延宕已久、戏码迭出的英国脱欧大戏终于迎来了终结的篇章,似乎预示着全球化也在走向尾声。与英国脱欧并行的,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和贸易摩擦的硝烟弥漫,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较量,各路政治强人的登台和民粹主义的烽起,意味着曾经一路高歌的全球化范式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变的关键节点。
这一厢,科技的日新月异让地球村变得更加紧密,人们的生活已经彼此密切嵌套,就像发生在英国的惨案不再跟中国人毫无关联一样;而另一厢,信息的孤岛却把世界割裂成一个又一个更加封闭的小世界。
这一厢,国际分工的深化让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被深深卷入全球贸易大链条的某个环节中,相互渗透和扩张的市场正在创造着地球上空前的财富;而另一厢,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越来越多的人被边缘化,沦为全球化的牺牲品。
这一厢,全球精英越来越超越本土,将意义和价值的生成转向新的疆界;而另一厢,在疆域桎梏下被隔离的底层越来越无法忍受精英们来自高空的俯瞰而转向个体乃至民粹主义。
也无怪乎,当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余音仍频频出现在各类学者、媒体,乃至政治权力拥有者语下时,畅销书作者、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已经改变了话语,把曾经引导世界未来方向的五字箴言——“世界是平的”——改成了“世界是深的”。
如果说三年前英国人在公投中选择脱欧让世人大跌眼镜,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已经真的做好了准备?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汇丰银行(HSBC)首席经济学家、英国下议院财政委员会专家顾问简世勋回溯历史,结合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在2019年出版的新书《世界不是平的》中提出了有关全球化的几个重要观点:
- 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个单行道,而是可逆的;也就是说,我们对全球化的展望一直过于乐观了。
- 全球化的进程虽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但一旦开始瓦解,其速度可以很快,并导致财富的急剧变化,正如历史上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短短几年间,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治体制(伊斯兰教)就改弦易辙(变成基督教)了。
- 移民、技术、金钱是三个可能导致全球化逆转的主要因素。
- 全球治理的落后已经无法应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反噬,那些一直在帮助管理全球化进程的国际机构正在丧失其可信度。
- 即便不会逆全球化,全球化的版本也不止一个。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的崛起,全新一批全球化的参与者有完全不同的历史背景、历史叙事和对全球化的认知,它们对全球化的方向和目标有不同的想法,全球化往哪里去,需要达成新的共识。
如果这些观点成立,那么除非采取必要有效行动,否则未来迎接我们的很可能是一个晦暗的、破碎的世界,恰如本书的英文名:Grave New World。
下文摘自《世界不是平的》部分篇章:
欧元区的问题
法国是构成单一货币体系的一部分,但是这种体系只会加剧成员国之间的不平等。自欧元形成以来,“五大”欧洲国家——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欧元区以外的英国——的经济命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单一货币制度出现之前的20年,西班牙和英国在“生活水平提升”的排行榜中高居榜首,意大利处于中游水平,而德国和法国则处于经济意义上的降级区。自单一货币制度诞生以来,德国和英国一直在争夺榜首位置,法国和西班牙一直处于中间位置,而意大利一直垫底。
德国和意大利财富的相对变化值得注意。1999年,欧元诞生的那一年,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约为德国人的90%。15年后,在意大利经济完全停滞了一段时期后,意大利人的生活水平仅为德国人的75%。
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差距。例如,威尔士人的生活水平仅略高于伦敦人的40%。2009年加入单一货币制度的斯洛伐克,其生活水平比较为富裕的西欧同类国家的40%还要低。然而,真正重要的是差距的扩大程度——以及扩大程度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欧元区的安排。欧洲的经济和金融架构师在构思单一市场和单一货币的时候,可能认为欧洲的经济体正在聚合,而事实却是,它们正在分化。简而言之,南北差距稳定地越拉越大。
在一个民族国家,政府很可能会尝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为较贫困地区的人提供帮助。即使这种尝试以失败告终,让人们看到政府采取了行动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在英国,北爱尔兰28%和威尔士24%的就业都集中在公共部门,而在富裕得多的东南地区,只有15%的劳动者以同样的方式就业。富人——还是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也会缴纳更多的所得税:根据英国财政研究所,收入排在前1%的人在2013-2014年缴纳了约30%的所得税,而在1979-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1%。虽然这一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化“赢家”税前收入的惊人增长,但这些额外收入随后被用于支持国内其他地方的就业或将一些人从所得税体系中剔除的程度表明,英国一直有对再分配的含蓄承诺。换句话说,有一种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负担分担安排。
在欧元区国家之间,负担分担的安排却并未达到同样的程度:可能是产生这种结果的制度要么不存在,要么缺乏民主合法性。德国的驾照在雅典行不通,而伦敦的驾照在斯旺西畅通无阻。法国社保金不归毕尔巴鄂管,而布赖顿的国民保险费在纽卡斯尔进行管理。
在欧元形成之前,这并不是一个多严重的问题:表现不理想的国家会对其较强的邻国进行货币贬值。这种贬值是一种隐性的负担分担安排。举例来说,如果意大利对德国货币贬值——里拉兑德国马克贬值——意大利出口商将变得更具竞争力,但德国出口商就会吃亏。另外,由于意大利从德国进口的商品的里拉价格上升了(德国从意大利进口的商品的德国马克价格也下降了),意大利消费者的处境便恶化了,相反,德国消费者的状况却变好了。与此同时,投资于意大利政府债券市场的德国人的处境也会变得更糟(因为他们的债券价值以德国马克计算的话将会缩水,而意大利政府尽管已经贬值,也必须支付高于均水平的利率来补偿其债权人,因为债权人承担了更加“糟糕”行为的风险。
然而,在欧元区内部没有类似的负担分担安排。的确,曾经会选择贬值的国家可以尝试压低国内工资和价格以实现大致相同的结果。然而,这个过程在政治上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1925年,丘吉尔做出决定,允许英国以战前平价重新加入金本位制,这使英国在面对工业竞争对手时背负着巨大的竞争劣势。凯恩斯对这一决定进行了有力回应:“丘吉尔先生的政策是将汇率水平提高10%。这一政策迟早会把每个人的工资都降低2先令。”“正如凯恩斯警告的那样,后果极为惨痛:1926年的一次大罢工;20世纪20年代剩余时间内持续的紧缩;1931年一次差辱性的贬值。
在一个高负债和超低通胀的世界——正是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许多南欧国家面临的状况——外汇“安全阀”的缺乏尤其不妙。超低的通货膨胀率往往与超低利率相关联。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处于单一货币制度下的国家仍然竞争乏力,那么它将别无选择,只能拉低价格和工资。然而,未偿还的名义债务数额将不会改变。雪上加霜的是,债务偿还成本也不会改变因为在利率为零或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借贷成本无法进一步下降。结果便是实际债务水平上升了。债务与国民收人的比率持续上升,财政紧缩必须越来越严,最终违约的风险不断上升政治民粹主义生根发芽。
民粹主义回潮
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下意识的反应。它一定程度上源自一种感觉,即在艰难时期实施的政策——有时是无意的——会对社会拜托你个成员造成不平等和不公平的影响。金融危机后救助银行可能有助于避免20世纪30年代的彻底崩溃,但是银行业中几乎无人从中受到惩罚:银行业——至少在美国——最终变得比危机之前更加集中(也就形成了寡头);在许多人看来,旨在让银行可控的监管措施很快就减弱了。在利率已经降至零的情况下,使用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是,因为这种政策使更多的钱流入已经富有的人的口袋里,它永远也不可能被视为刺激经济最公平的方式(特别是当家庭与企业更想偿还债务而不是打开钱包时)。要求债务人偿还债务而债权人免除自己的责任,可能可以避免麻烦的债务违约,从而减少更长期的金融崩溃的风险,但正如欧元区所发生的情况,它很可能引发债务国与债权国之间的信任崩溃,重演10世纪荒谬的狄更斯式道德说教。
民粹主义尤为可能在金融危机后站稳脚跟。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强有力的证据表明,金融危机——不是简单的经济衰退——已经刺激了政治民粹主义,明显表现在向极右主义的倾斜。其成果不仅被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崛起所扭曲,多年来,极右势力还在意大利和德国的选举中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同时至少还有比利时、丹麦、芬兰、西班牙和瑞士这些欧洲国家。最明显的便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民粹主义右翼政治及少数民粹主义左翼政治的回归。举个例子,选民对英国两大主流政党的支持比以往要低:在2015年的大选中,英国保守党和工党共赢得了673%的选票,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合计票数超过70%。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后,他们的合计票数超过了80%;值得注意的是,工党失去的份额(36.9%)比保守党2015年赢得的份额要高一些。在2015年大选中,最大的民粹主义赢家是苏格兰民族党,该党的主要目标是让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在其他地方,政党要么凭空出世,要么在政治舞台边缘追求候选资格,如西班牙的“我们可以”党、公民党和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的政党联盟“一起说是”,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和“金色黎明”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正统芬兰人党,匈牙利的“龙比克”党荷兰自由党,法国国民阵线。与此同时,2016年,凭借反穆斯林和反墨西哥的竞选纲领赢得共和党总统候选提名的唐纳德·特朗普排除万难最终入主白宫。而且,在民主党内部,伯尼·桑德斯( Bernie Sander)成了希拉里·克林顿有力的克争对手。他提议向富人征收重税以实现免费上大学,同时极力反对自由贸易,以此来吸引年轻选民。
实际上,金融危机解释了20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结构的内在悖论。由美国(在欧洲则是德国)领导的国家,是建立管理全球化的机构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一的基石。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随着跨境资本流动的大幅增加,事实证明这些机构作用不大。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危机揭示了全球化内部的不平等一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家之间,有越来越多的人退回到自己国家的“避难所”,这也意味着,人们逐渐拒绝全球化和人类共同的原则。政客很乐意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在2016年英国保守党大会上,英国新任首相特蕾莎·梅( Theresa May)指出:
如今,有太多身居权位的人表现得自己好像与国际精英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而不与大街上的普通人、他们雇用的人、他们在大街上擦肩而过的人同流。但如果你相信自己是一名世界公民,那你就根本不是任何地方的公民。你根本不明白公民身份意味着什么。
她对国际精英的批评也许是对的,但是她错在暗示只有精英才会视自己为世界公民。在一项调查中,来自18个国家的约51%的受访者都同意这一说法,“我认为自己更像是一个全球公民而非我自己国家的公民”。这些人难道都不知道公民身份的意义吗?
把精英与那些视自己为全球公民的人混为一谈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它只会鼓励“本土主义者”和排外的暗流。尽管如此,汉斯·摩根索的说法(引起了特蕾莎·梅的共鸣)——我们的国际代表与彼此相处时往往与他们自己应该代表的公民在一起时更自在——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一个严峻挑战,尤其是,如果他们坚持从高处睥睨自己的同胞。
不过如今,他们更多是从高山度假地而不是从喷气式飞机上俯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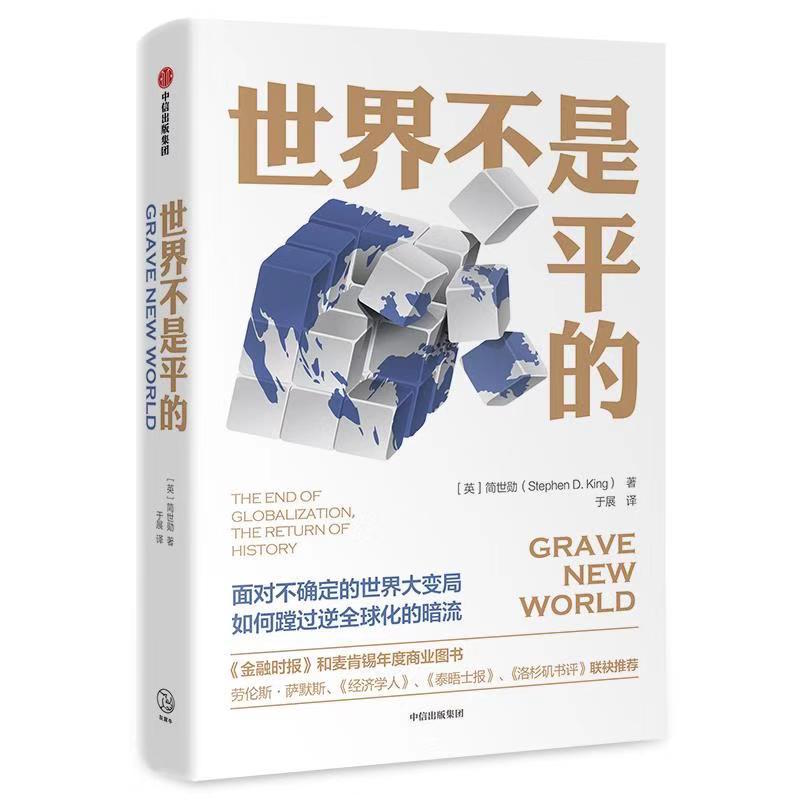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