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2001年,我和朋友在西门町吃冰,在路上被人问:“你想不想来拍电影?”隔了几天,我去见导演、试镜,就开始演《蓝色大门》。直到今天,让我进入影视行业的这些事我都记得很清楚。
那年我17岁,电影对我来说太新鲜了,只觉得很好玩。年纪那么小,对拍电影这件事很好奇,感觉自己的体力用不完,导演一喊“卡!”我就跑过去想看看机器是怎么样。2001年时,拍电影还是用胶片,底片拿出来之后,他们要在一个暗袋里过底片,把底片过到底片盒。那时候对焦都不是用红外线,是拉皮尺拉到演员眼睛这边,现在看来是非常古典的电影拍法。我整天在那边学习剧组的流程是什么、打光是什么、这些机器都是什么,进入到一个全新的职业世界里面。
《蓝色大门》参加东京影展的时候,应该是我第一次被电影的力量震撼到。我那时候还那么小,19岁,看到自己的脸被放到那么大在银幕上,然后看到身边世界各地的观众专注地看,他们会笑,会感动,我感受到自己是电影行业的一份子。这样一个瞬间的感动,让我觉得,那是可以让我一直做下去的事。
但我还是刚刚起步而已,进入这行之后我一边拍戏,一边学习、看大量的电影。后来有机会去拍香港的《千机变II花都大战》。刚到香港剧组时,我还听不懂粤语,香港电影工业的节奏很快,我一开始非常不习惯,很紧张,压力好大,就是在那边,我抽了人生中的第一支烟。
演戏要付出好多努力。我去香港拍戏没有用配音,从听不懂粤语到学会粤语。有几年我还接了一些日本的作品,也是人家邀请我过去,我觉得OK就去学日语、开始新工作。2015年跟孙艺珍演的《坏蛋必须死》需要讲韩语,正好那之前我在拍《再见,再也不见》,中间就隔了两个礼拜不到,只能在去济州岛拍戏之前,从韩文的发音、结构开始自己学,进组再来老师系统地教……这些技术方面的东西没有捷径可以走,学会可能不是太难,但是要用那个语言来表演又是另外一回事,台词也需要请教老师。到现在,看到韩文我还可以念出来,就是意思可能不太知道了。
在香港和日本拍戏的那阶段,应该是我工作安排最满的时候,那年至少拍了5个作品,而且演员不只是拍戏嘛,还要去宣传、拍杂志、拍广告。不是说3个月在拍戏,就表示只有3个月在工作,搞不好是连续8个月都不停工作。一部电影不是杀青就结束了,还要路演。《观音山》那次路演最长,将近一个月,大部分的省份都去到了,早上起来一直到晚上8点,一天跑5个影院。
现在来看这些经历,一切都没什么感觉了。当时就觉得好像在探险,这对我个人来说,不只是工作,是生命的体验,了解不同的文化、学语言、在那边交朋友……都是这个职业带给我的机会,很像游学。
2018年,我们拍《蓝色大门》取景的师大附中游泳池拆掉了。拆掉之前,导演易智言、桂纶镁和我回到师大附中,那天我们在泳池里面放了椅子跟银幕,在户外放了一次电影。我们三个人坐在最后面,在这个我们曾经拍电影的地方再看一次。那也是感受到电影好伟大的时刻,前面是观众,我们是经历过这部作品的人,我们记得当时的天气,当时的水温,还有18岁的自己第一次演电影时不知所措的感觉。这个职业总是会给我新的刺激,在演员这个身份里,我永远都在感受。

2
我演过一部叫《爱情无全顺》的电影,拍戏的时候,每天化妆要两个小时,把自己双眼皮贴起来,弄成不修边幅其貌不扬的样子,演一个叫吴全顺的理工宅男,表演时讲话的节奏也跟我本人非常不一样。这部电影现在可能没什么人讨论了,但在那时候的我看来就是在尝试“转型”,尽管现在看来是非常表面的。
常常会有人问我关于转型的问题。可以说,我从18岁拍完《蓝色大门》之后就想了,想尝试、想突破,可这不是说我拿起笔要画什么就能画出来。演员是被自己的能力和剧本所选择的,我没法决定自己想要怎样,就有那个能力做到。
我演的吴全顺,外形是有很大转变,看到的人可能心里都会笑一笑,觉得“He’s trying,他有想要努力转型。“可是大家认同的转型,并不是我在人设上做了多大的突破,演了一个让人多么大跌眼镜的角色,而是要认同我在新的戏路中拿出一部好的作品。
到现在还是有很多观众会叫我“大仁哥”,这种因为角色而出现的标签我觉得还好,说明它至少是个成功的角色,相对于“张士豪”时期,这可以算是有所转变。但在那之后,我还是演了很多“暖男”角色。其实我在接到它们的时候都是trying的状态,只是这两个可能是对我来说比较轻松的角色,对于它们所留下的标签,我还是开心的,所有能被记住的东西都很不错。
包括《后会无期》里江河那个角色,给一些观众留下印象,原来陈柏霖可以是这样。在我看来,江河也算是“trying”,不是真正转型。转型很难啊,真的要观众来说,也很难直接说出几个他们认为成功转型的演员。观众会觉得江河这个角色不错,但他没有成为人家见到我的时候第一个提到的角色。
即使在一个看起来没有什么大变化的状态里,付出的努力还是持续的。之前和迪士尼合作的《假如王子睡着了》,迪士尼希望我去演的那个角色身材线条特别分明,我虽然经常锻炼,但并没有追求那种肌肉的雕刻,事实证明,要做到那个要求真是很辛苦。去年演《鳄鱼和牙签鸟》需要讲法语台词,我又花了非常多的精力去学法语。
演绎每一个角色的过程中,都有它很难很辛苦的部分,对于trying还是being,都是之后下的判断,而我经历了那个当下,要说自己对哪个角色比较努力、比较看重,这好像不公平,演员去消化角色所应该拥有的本能跟才能,是职业的基本要求,它会持续在整个演艺生涯里。我将我所能消化的部分呈现到能力的极致,接下来就看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了。
怎么办?这个问题不应该丢给我,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不是说我这个人要怎么转型,演员所面临的这些问题,也是整个行业在思考的。
刚入行不久的时候,我对自己还有过期许,以为自己再过两三年就能拍到王家卫的电影了吧!每年都觉得应该很快很快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我有遇到过王导好多次,他每次看到我就讲一句话:“你怎么还是长得那么年轻。”我就只回答“对啊对啊”,我真的很期望去演他的片子,想跟他合作看看是怎么样的,但是没有合适我的机会。
每一部戏都有它自己的命运,我无法去控制整件事,和最后的结果,能做的只能是把我选择的东西做到最好。大家不就是在等待这一天吗?至少对我有期待就很不错,如果哪一天真的接到了一个令自己和观众都认可的转型作品,那大家一定会问下一个问题了:你接下来想要挑战什么样的角色?这个目标是没有终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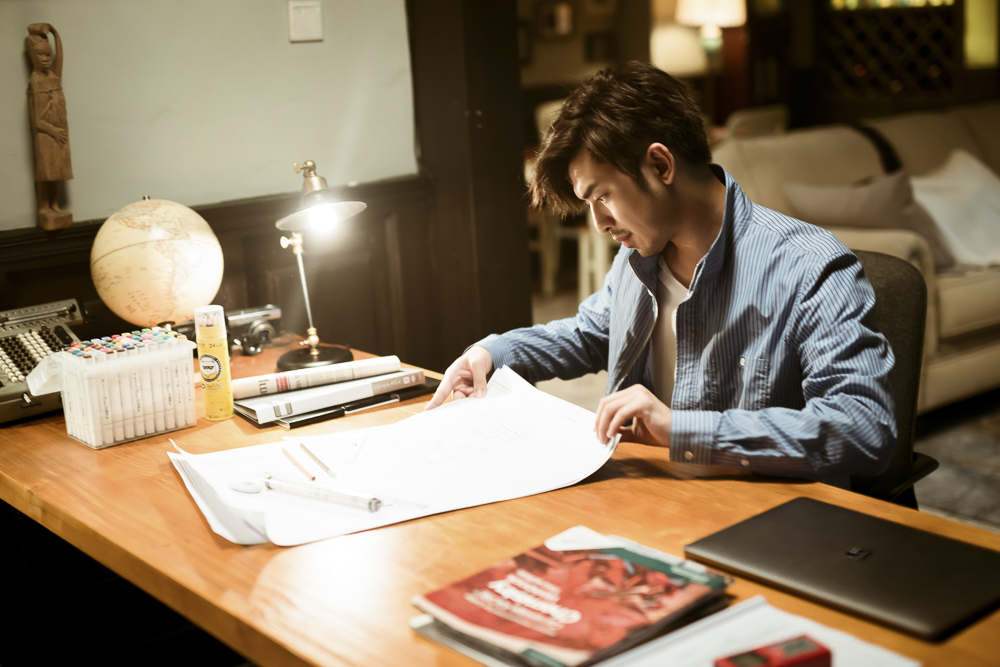
3
这些年娱乐圈也发生很多变化,我自己也在相应做调整和应对。比如,自己开公司算是我的一个尝试,当时的初衷是想要去做电影制作的工作。今年我没有接新的戏,只是带着自己创立的品牌参加了西宁的FIRST影展。我当然很想要制作好的电影,可能的话也想自己拍东西,现阶段我们还没有好的计划拿出来,所以并没有在这方面宣传太多。
三十岁之前我就是不停地在演戏,2016年去“我们相爱吧”是我第一次参加真人秀。刚接到这个邀请的时候,我感觉这是个我完全没有想象过的综艺形式,抱着玩一下也没关系的心态就去了。后来隔了一年,又去“花儿与少年”。真人秀很累啊,摄像机24小时都在拍。
可能有人会想,这种综艺类的曝光对演员来说不是好事情,但在好莱坞,这几年很红的演员Kevin Hart,还有Dwayne Johnson,他们都接了非常多的综艺,在综艺里,他们都有非常好的表现力让观众认同。他们拍的片子很多都是我们说的喜剧片、爆米花作品,但是观众也不会给他们下定义说他们就是怎样的艺人。
我自己也会看很多综艺,我觉得不管是参与或观看,都很好玩的。如果要把娱乐和演戏划分得非常清楚,那最近很火的“演员的诞生”属于什么呢?一群演员在探讨演戏,但是它又是一档综艺节目,就看观众要怎么解读了。
只是,这些节目会放大艺人比较私人的一部分,但我们不是一直都在“被”公开这些事情吗?与其去在意这些,不如把顾虑都放下。像“花少”就是完全没有台本,内容是自由度非常高的旅行,它的节目内容比我自己去旅游更丰富,行程的视野更广。
我都在娱乐圈十几年了,已经习惯不把工作和生活做很明确的界定。今年我都一整年没有接戏,给自己放了一个长假,大部分时间待在台北的家里和父母在一起,定期和朋友相约打球。不过这一年里我还是会到处走走,去上海和西宁参加了电影节、影展,这次来北京赴一个约,去见了很久不见的朋友易建联,看他的球赛,可能赶完通告晚上又去和朋友吃饭。
艺人的私生活不过如此,也就是在工作和私人安排中分配时间,我都是自得其乐的。我经常自己跑出去吃面、吃火锅,都不一定要包房。这和我展示在大家面前的性格也没有什么分别,像我出去吃饭遇到看过我作品的观众,跟我讲话、相处那几十分钟,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去年,有一次我去上海,看到一个修得很漂亮的球场,就叫了朋友来一起打球。结果好多人都过来看我,压力好大,那场球最后也没有打完。不过那个压力并不是私下打球被围观那种困扰,而是想到职业篮球选手在场上打球被那么多观众看,终于懂得他们上场的压力是什么样。我的朋友有各行各业的,大家面临不一样的问题,但一样的是,每种职业都有烦恼。
十几岁的时候我玩过乐团,玩乐团的时候就好想当摇滚乐手,觉得很帅。那时候是跟高中同学一起玩,有闲的时间就约到练团室去排练。后来遇到的一起玩音乐的朋友,现在都成了很厉害的音乐制作人,但我做演员了,音乐就变成忙碌时调剂的爱好。
以前我去别的城市拍戏,还会带着吉他。有一次,拍彭氏兄弟的《见鬼10》,我们剧组在泰国,我带了电吉他过去,那天我在酒店想玩一玩,就插上电源和音箱,一弹,整个酒店瞬间跳闸黑掉。可能是我带了四个效果器,电压适配有什么问题,那几秒钟我以为是闹鬼,吓死了。赶快给前台打电话,他们说没事没事,电路问题。后来几年,出国拍戏还是会带一个超级重的17寸苹果笔记本,再带一个小的MIDI,无聊的时候可以这样弹弹。
七八年前,我还和之前玩乐团的朋友去垦丁的春呐音乐节表演过,那时候我在拍台湾啤酒的广告,品牌方和音乐节有合作,他们知道我喜欢玩音乐,问我要不要去玩,我就和朋友练几首歌去表演看看。现在年纪大了,虽然自己的房间里有五把吉他,床边还一直都放着一把,我都不知道多久没有弹过它,可能零件都坏掉了。
我没觉得从西门町被拉去拍电影之后,人生就改变成什么样子了。当我知道艺人有什么新闻出去、看到的人反应会怎么样,反而就觉得无所谓了。我希望自己一直保持很纯粹、很自在的状态活着,保持清醒。


—— 完 ——
题图为《鳄鱼与牙签鸟》剧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