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过很多与南京有关的文字,觉得自己不会再写,不可能再写。直到找到一个新的角度——通过南京这扇窗户,把中国历史说一遍。”
——叶兆言
南京城里的柏林墙
文|叶兆言
南京人都习惯偷懒,不太会去想“南京”这两个字怎么来的,清军进入南京城,就仿佛历史简单重复,赶紧要做的一件事,先给南京这个城市改名换姓。于是在北京开会,满汉大臣招集到一起议论,拿主意说观点。大伙七嘴八舌,小心翼翼地揣摩圣上意思。其实这时候的顺治,还是个小皇帝,只有七八岁,根本不明白事,当家作主的是摄政王多尔衮。
很快,过了两个月,顺治二年的闰六月十八日,方案终于有了,清廷正式下令,将南京应天府改名为“江宁府”,原设的府尹改为知府。紧接着,多尔衮又给在前线督战的多铎下指示:
南京着改为江南省,应天府着改为江宁府,设知府不设府尹。掌印指挥、管屯指挥暂留,余指挥俱裁去。其卫所改为州县,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
好一个“俟天下大定,从容定夺”,胜利者的口气,说起话来就是不一样,就是牛。这指示有两层意思,其一,多尔衮说的南京,是指南直隶,也就是大南京的意思。这个大南京的范围,最初由明太祖朱元璋钦定,前面已经解释过,包含江苏安徽和上海,现在改名为江南省。其二,应天府才是地道的南京城,江宁也不算什么新名称,一千多年前,东吴亡国,南京就叫过“江宁”。当时是晋武帝南巡,慨叹“外江无事,宁静于此”,因此只是给南京恢复了这么个名字。
江宁这名字显然复古,出主意的肯定是汉人大臣,满人刚入关不久,哪会有这脑子。与元朝的蒙古人一样,满人根本不把南京这座城市可能会有的反叛放在心上。北方的汉人王朝特别忌讳南京的王气,因为所谓的金陵王气,很可能会让我们的国家处于分裂状态,因此隋朝统一中国,立刻毫不含糊地将南京这个城市给灭了,把六朝的痕迹烧得一干二净。满人跟蒙古人都是少数民族,他们知道广大的汉人地区,都可能生出一份反叛之心,在哪都差不多,都一样,犯不着要特别防范南京这一个城市。
满人很善于用兵,八旗铁骑指向哪,打到哪。自从入关以后,基本上逢战必胜。南京只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重要据点,在前期,它是进一步南下西征的中转站。天下大定之前,一方面,在级别上,南京的政治地位先要降下来,再也不允许称什么“京”,再也不是“留都”。对于发迹于东北的满人来说,北京才是他们不折不扣的南京。另一方面,改名江宁后的南京,仍然“为江南根本之地,绾毂十省”,仍然还是东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不可小觑。也就是说,清政府要凭借这个地方,控制南方。
满人在数量上是很少的,汉人可以不服气,不服气也没用,谁厉害谁狠,谁厉害谁就是精英,谁厉害谁就是狼。汉人只是羊群,清朝的天下事实上也是汉人帮着打下来,当时进入南京的清军,有很多都是投降的明军。大家都知道史可法没投降,英勇就义,然而太多数晚明的军事将领,都十分狼狈地投降了,都成为满人的爪牙。多铎给朝廷的奏报便称,先后投降的总兵有二十三人,监军有两人,副将有四十七人,骑兵和步兵二十三万八千人。
当兵的都投降了,老百姓还能怎么样,只能看热闹。南京的城市级别降低,降低就降低吧,这样的历史,过去也曾经历过。当时南京最大的汉官是洪承畴,洪是明朝重臣,降清以后,又得到了满人重用,官做得比在明朝时还大。洪承畴到南京来坐镇,主要是起到一个安抚作用,他是汉人,又是前朝的大官,有他在场面上支撑,南京人的亡国情绪会少了许多。
要控制和管理南京这座城市,也不是什么难事。根据记载,当年在南京的清军,真正属于八旗军的数量,少得让人不敢相信。实际兵力仅仅为“左翼四旗满州、蒙古二千名,弓匠五十六名,铁匠五十六名”。这个数字并不是想当然,还是有来头的,在《钦定大清会典则例》里有确切记录。
此外,维护南京安全的还有绿营兵力四千人,原来是明朝江南提督曹存性的部下,降清后被编入了绿营。这个比例很有意思,计算起来,绿营的人数比八旗军多了将近一倍,可是这些“南兵”基本上就是做做样子,完全没什么战斗力,管管南京城里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还可以,指望他们缅怀旧主,能够揭竿而起,起义造反,根本不可行。
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反抗,起码在南京的外围,在东南沿海,反清复明的战斗还在进行,还在继续。南京人心里显然也还不服气,可是满人不跟你们讲道理,他们来到这个城市,作威作福,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最先开始感受到这份委屈,是生活在南京的贵族,在过去,这个城市属于他们,吃香喝辣为所欲为,偏偏人家满州鞑子是提着一把屠刀来管理南京,才不会把这个城市中的什么贵族和世家放在眼里。
一大批原明朝的勋贵高官,被削爵免职,被抄没家产。中山王徐达的后裔魏国公徐文爵,被除去封号。徐文爵有个弟弟徐青君更惨,被“籍没田产,遂无立锥”,最后不得不“与佣、丐为伍,乃为人代杖”。勋戚贵族如此,一般士绅的境况,显然会更糟糕。形胜当年百战收,子孙容易失神州,不亡国不知亡国恨,真亡了国,再抱恨也来不及了。可怜一片秦淮月,曾照降幡出石头,有点文化的文人,只能靠书写诗歌来言志抒怀。
1645年的5月,明朝的南京官员们出城投降,迎接清军。这个场面很戏剧性,清军大队人马开了过来,耀武扬威进城。清军和平进入了南京,立刻将城市的东北部划为八旗军营地,原来的老百姓呢,对不起,该去哪去哪,统统驱逐:
分通济门起,以大中桥北河为界,东为兵房,西为民舍,通济、洪武、朝阳、太平、神策、金川凡六门,居大清兵。
军令如山,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南京城立刻大乱,原来住在这里的南京原住民,不得不“日夜搬移,提男抱女,哀号满路”,众多居民不得不移家城西和城南,造成“西南民房一椽,日值一金”。官兵军爷免不了要趁乱抢劫,趁机捞一把,清军统帅多铎为严肃军纪,“斩兵抢物者八人”,效果如何,也只有天知道。老百姓都害怕兵荒马乱,都担心家破人亡,没想到这个灾难说来就来:
百姓俱狼狈走,稍迟则刀棍交下,立毙。什物悉为兵有,百姓止走空身而已。
南京城东北部,就这么眼睁睁地成了八旗军的地盘,满人反客为主,鹊巢于是鸠占。很快,到顺治六年,为确保满汉分居,互不干涉影响,干脆在南京城东部修筑“满城”,专供旗人居住。自南京城有史以来,这状况是第一次出现,竟然出现了“城中城”,在城市内部又加修了一道城墙。仿佛过生日切蛋糕,活生生地切了一刀,硬是生造出了一个满城,与旧城以一道高高的新城墙为界限:
起太平门,沿旧皇城墙基,至通济门止
不熟悉南京城市格局的读者,对这道区分满汉的古代柏林墙,不会有什么感觉,也绕不太明白。清朝当局曾先后两次修建南京城中的满城,具体方位是以原明皇宫为基础,将皇宫的东墙和南墙拆掉,利用南京城的东南城垣。满城西侧,从太平门内皇宫角竺桥至通济门,沿用旧宫城西墙,添造城垣,南接通济门东侧。满城的西侧城墙上开设两道城门,以便与汉人居住的区域相互往来。北侧城墙是将原明皇宫北墙进一步延伸,整个满城“长九百三十丈,连女墙高二丈五尺五寸,周围三千四百 十二丈五尺”,是清代直省各驻防城中面积最大的。
满城中修筑了箭亭和校场等军事设施,当然还有八旗营房,满汉分居是清朝的一大特色,国内其他城市中也有满城,大多按八旗方位进行布局,红黄蓝白,各有各的位置。南京城内的这个满城如何布局,在清代方志以及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后人因此也很难弄明白。清道光年间,江宁将军祥厚曾奏称:
奴才闻得有人在朝阳门迤南并正阳门之东、西倒塌裹披城墙土坡上种地……查验得镶黄、正白、正蓝等三旗界之裹披城墙均于早年坍塌,砖块无存。
根据此段文字,可以认定到了清道光年间,南京城里这道柏林墙已名存实亡,很多地方已经坍塌。同时也可以认定,位于朝阳门,也就是后来改名的中山门以南,正阳门也就是后来的光华门两侧城墙,属于镶黄正白正蓝三旗的辖境。这与八旗方位中通常镶黄旗位于东北,正白旗位于正东偏北,正蓝旗位于东南的规定相吻合,说明清代南京满城的内部格局,非常可能也是遵照了传统的八旗方位。
这道区分满汉的柏林墙,足以造成一个城市的两种不同文化。南京城里的满城,就好像一个巨大兵营,行政上不受地方府县管理,江宁将军是南京八旗驻防的最高长官,其职责为“镇守险要,绥和军民,均齐政刑,修举武备”。军事事务是驻防将军的首要职掌,不过驻防旗人的日常生活,譬如婚丧嫁娶,譬如养赡救济,必须也得过问,别人想管都管不了。
满城也因此自成体系,成为南京享有特权的城中之城,《钦定八旗通志》上便有明确记载:
江宁驻防旗员给园地三十晌至十晌不等
换算一下,每个旗员可分得六十亩至一百八十亩土地,这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人人都大地主。八旗官兵的主要收入,按说是清廷发给的粮饷,将军每年俸银为一百八十两,俸米九十石,佐领俸银一百零五两,俸米五十石五斗,骁骑校俸银六十两,米三十石。自雍正朝起,对将军和副都统等高级官员,另增给养廉银,数额是正常薪俸的数倍甚至十几倍。大家都知道满人马上得天下,不擅耕种,有了土地也只能收地租,这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当时旗田地租年收入总数为三千九百九十两,根据《佚名奏报江宁驻防八旗每年盐菜及地租项下用银数目事》记载,乾隆年间的具体分配情况为:
江宁将军一员,每年银八百三十两;江宁副都统二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二十两;左翼协领四员,每员每年银二百两;左翼佐领二十四员,每员每年银八十两。
由此可见,当时旗人在南京的日子十分快活,可以充分享受打下江山的种种好处。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当然应该是老子和老子的后人来享受。清代设立理事同知一职,专门负责审理旗人与南京原住民的诉讼。理事同知在官制上为地方属员,不隶属于八旗驻防。自康熙朝起,清廷将理事同知定为旗缺,只有旗人才能出任此职。因此,虽然名为地方官员,其职责只是保护驻防南京的旗人权益,在处理各种纠纷时往往袒护旗人。
在南京的江南贡院,存有一块《韩绍文等立颂德碑》,为雍正年间的理事同知赫胜额歌功颂德,说他“仪型虽往,恩德犹存”,“自莅任以来,旗民安堵,强梁敛迹,宵小潜踪”,说他“片言折狱,秉正持平,哀矜勿违,小大以情”,说他“无偏无袒,至公至明”。“安堵”是安居乐业的意思,强梁和宵小都是属于坏蛋,明白事理的人都知道,秉正持平是对断案的最基本要求,却还要专门拿出来歌颂,足见当时秉公执法,不偏袒旗人,实属非常难得。
在八旗制度下,朝廷会按月发给粮饷,驻防兵丁不允许从事农工商等产业,过着不劳而获的快乐生活。南京城中也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满汉矛盾,譬如满汉不通婚,禁止旗女嫁与汉人,旗人男子则可以娶汉人民女为妻。又譬如旗人有很好的福利待遇,拥有政治和司法方面的特权,不受地方法规约束,旗人的不法行径便在所难免。特权很容易产生腐败,更容易造成罪恶,江宁驻防官兵“日就纵驰,至不堪言,更且习气大坏,多有窝盗包娼、行窃诈民,甚之重利盘债、骂官闹衙,无不任为”,而“该管之官反行百计袒护”,地方官府虽受其扰,亦无可奈何,无计可施。
当时在南京,出现过一种让市民哭笑不得的盗匪,俗称“旗盗”。一度十分猖獗,没办法收拾。不是旗人直接参与了偷盗,而是一些投靠旗人的本地刁民,在为非作歹干坏事:
昼则倚势行凶,夜则纠众打劫。地方官追捕急迫,彼即仍窜归旗,无从究诘。
所谓投靠旗人,又叫“投充”,其实就是投入到旗人名下,打着旗人招牌,狐假虎威伤天害理。顺治和康熙年间,八旗官兵买卖人口之风,曾经非常厉害,一般老百姓自然不愿意卖身为奴,可是到了后来,风气开始转变,汉人百姓竟然会主动投入旗下为奴。投充者既有孤身前来,亦有干脆携家带口,包括自家的田地投靠。一旦投入旗下,挂名旗奴,其田地即可免除官府赋役。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南京人不惜投充为奴,更有奸恶之徒,借投充之机,仰仗旗人的特权威势,在地方上横行无忌:
投充名色不一,率皆无赖游手之人,身一入旗,夺人之田,攘人之稼。其被攘夺者愤不甘心,亦投旗下。争讼无已,刁风滋甚。
根据嘉庆年间的《新修江宁府志》记载,江南地区原住民投充旗奴所带来的骚扰,最严重的地方就是南京。所谓“南民投充,惟江宁为多”。这是让傲慢的南京人感到很不光彩的一段历史,因为当时的投充,“非尽艰窘而然也”,并不是迫不得已,并不是走投无路,不得不这么做,而是“半属作奸恶棍,半属逋罪强徒,急欲逞凶,遂尔走险”,结果就是“一经收录,大肆猖狂,或伙赴市廛以陵商,或横行村镇以诈懦。有司惮其恶而不敢制,小民畏其威而不敢言”。
没有人说得清楚,隔绝南京市民与旗人的柏林墙,什么时候被拆除。跟北方的万里长城一样,南京城里这道满城城墙,更多的只是一种摆设,并没有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它提供的是一种心理上安慰。因为年久失修,更重要还是因为没什么实用性,很多地段都坍塌了,坍塌也就随它坍塌。一段接着一段毁坏,坏了也没人去修缮,满城的旗人不会去修,南京的原住民也不会去修,跌落在地上的旧墙砖,正好被贪小便宜的人拿回家派上用场。
从清朝中期,到太平天国,到晚清,到民国,到国民政府,到汪伪时期,都会有一些南京老百姓浑水摸鱼,偷偷地将旧城砖挪为家用。甚至官家也参与过盗拆明城墙这些事,民国初年,大清没了,南京城内“手不任执殳,肩不能荷锄”的旗民,由于生计问题,一度在地方政府默许下,靠拆旧城砖卖钱度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黄埔军校也迁到昔日的满城,蒋委员长曾作过批示,同意军校拆些城墙砖建校舍,因为有关人士反对,遂告停止。
横贯在南京城内的这道柏林墙,最后是不是就这样茫然无存,不得而知。遗忘总是很容易,今天大多数南京人的记忆中,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这么一道城墙。晚清时期的鲁迅曾经在南京读中学,当时南京人心目中,显然还留有一道柏林墙。再过不了几年,就辛亥革命了,汉人和满人的对立情绪,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鲁迅先生喜欢骑马,在满城区域里骑马,会招到清兵呵斥,不止呵斥,还会向学生娃子扔石头。鲁迅他们也不甘示弱,也会用石头进行还击,结果当然是谁伤害不到谁,大家都只是扔着玩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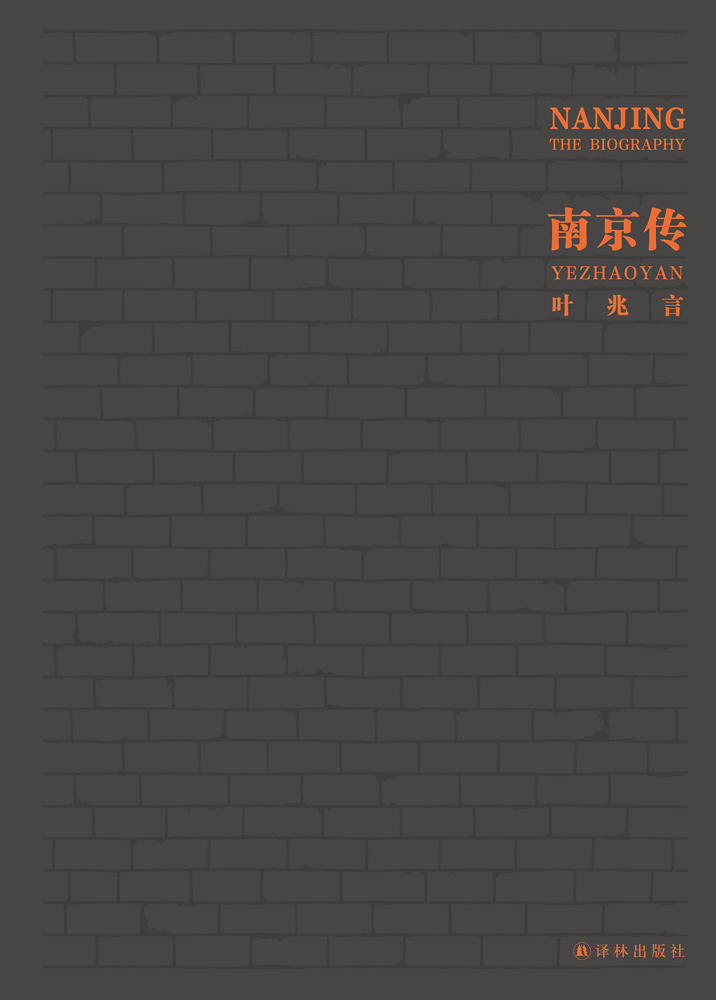

—— 完 ——
本文图片由出版机构提供。
叶兆言,1957年出生,南京人。1980年代初期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作品有八卷本《叶兆言中篇小说系列》,三卷本《叶兆言短篇小说编年》,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等。《南京传》为叶兆言最新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