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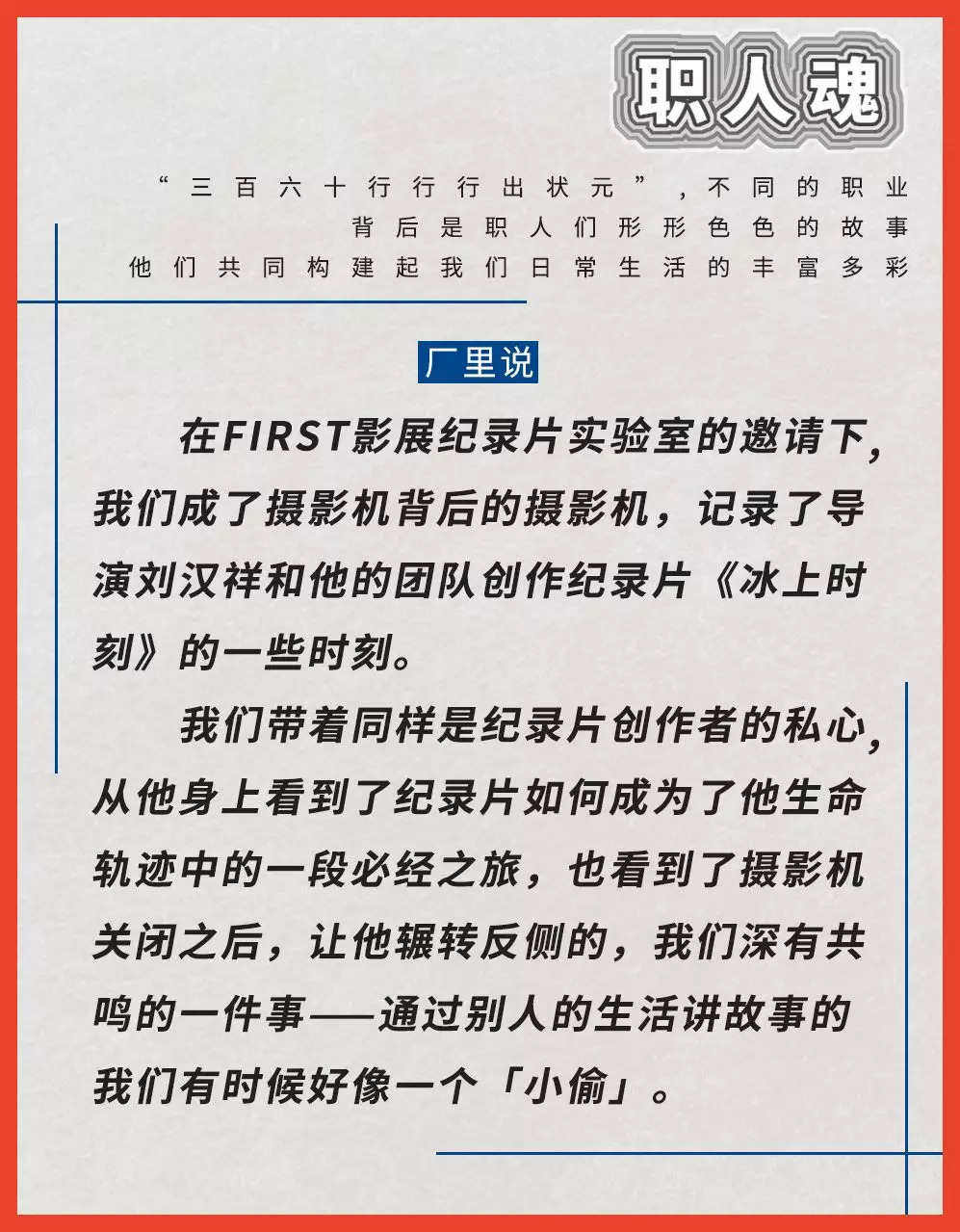


1.
刘汉祥觉得“冰上时刻”这个名字有很多含义。“冰上”当然跟冰球有关系,这是一部记录学冰球的孩子的影片。而更多的韵味应该在“时刻”二字。当他坐在那些冰球队家长的车里面,跟着他们在北京穿行,时刻带来了一种时间感:孩子在冰上;家长在日常生活中,在等待。
他尝试去表述一个简单的感官体验:人其实是在不同的维度里生活的,虽然对于时间的计算方法是相同的,但是感觉始终千差万别。
这种哲学层面的追溯,更像是创作者的思维习惯,而非一个绝对明确的主题。具化到拍摄中,刘汉祥想让儿童冰球队的视觉语言看上去尽量单纯。理想状态下,这个纪录片呈现出来的东西很简单,但是能带给观看者很多的思考。

儿童纪录片导演刘汉祥与冰球小选手

对于刘汉祥来说,其中一个思考,将是城乡儿童的教育差别。学习冰球的孩子大多来自一线城市的中产以上家庭,这项运动也可以被看作是阶级身份的某种象征。
他们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开始接受训练,在冰上排着队,等待跨过一个一个很小的障碍物,而与此同时,那些乡村的儿童却要跨过更大的宿命的艰难——这种夹杂着同情和自怜的判断是真实的吗?
儿童冰球队的故事发生在城市中,在室内体育馆的穹顶之下,但它极有可能同样残酷,因为童年原本就很残酷。

《少年少年》剧照
再回到在冰上排着队的等待跨过一个一个小障碍物的孩子,那时候一个家长带刘汉祥去冰场看训练,这一幕让他完全出乎意料:教练让小孩挨着跳过去,大部分在跳过去后一定会摔倒,但必须很快爬起来,因为不爬起来就会影响后面的人。跳跃,摔倒,爬起,继续排队。从这个圈,刘汉祥觉得看到了城市儿童的成长。

2.
作为FIRST影展纪录片实验室的项目,《冰上时刻》是刘汉祥的又一部儿童题材纪录片。箭厂出于对题材还有导演拍摄目的的兴趣,以及作为合作方,跟FIRST影展一路跟踪了下来。
从2009年开始,刘汉祥一直做儿童题材的片子,因为“对别的任何都不感兴趣”。很多人把坚持做了多少年当成是一种情怀,刘汉祥否定这种判断。在他眼里没有情怀,也没有坚持,只是巧合。但仔细想想,这种巧合的发生可能还是源于自己,源于一直尊重内心的选择。
拍摄儿童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纪录片,导演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契约关系在这里将全部失效,成人世界的规则很难适用,因为孩子有他们的一套原则。

“在这个世界中,孩子其实是处于弱势。他的周围都是比他高很多的大人,因此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很强的。在跟他们接触的时候,不能拿成人那一套客套去对待,因为他们比我们要敏锐得多。但这恰恰是真正动人的东西。”
2014年,一辆改装的红色大篷车来到了四川雅安地震灾区,建立了一个流动露天影院,这是《夏日流动影院》。刘汉祥最初以志愿者的身份去随行记录,后来他把拍摄的权利交到了雅安小朋友手中——给了他们30台相机去记录自己的故事。
其中有一个11岁的小女孩,父亲一直在外面打工,她像小大人一样照顾两个弟弟,做饭,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刘汉祥在拍摄时就和女孩建立了一种难以言说的友谊,拍摄结束后,女孩给刘汉祥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讲述妈妈去世后自己的改变与成长。

《夏日流动影院》剧照
这种拍摄过程中建立的信任可遇不可求,被刘汉祥看作是额外的奖励。在他的概念里,成长存在一种巨大的失落感,而孩子身上的天真对成年人是有治愈性的。尤其是当他回到钢筋水泥的世界里,他没有告诉过山里的孩子,他也期待听到他们的消息。
刘汉祥认真回复了那封信,告诉女孩一些自己的关于“失去”的童年经验。通信意外地维持了很久,后来,情绪的东西反而少了,女孩开始问刘汉祥数学题。
“我的数学也不好,就各种找辅导资料和上网查解题步骤,感觉自己上学时也没这么认真。”刘汉祥笑着说。

3.
16年冬天,刘汉祥的妻子怀孕了。女儿的到来让他在拍摄儿童纪录片的时候更多投射到自身。未来她会在北京生活吗?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在做每一个片子时,他都去找作品主题和自己的关系。
如果缺乏关系,就很难有信心和耐心继续。在儿童冰球队的故事里,他保持着创作者的敏感,同时又多了一份与家长们的共情。

过去他常常去拍摄乡村里的孩子,感受到被对方需要,但当拍摄城市里的孩子时,他们“根本不需要”。这种失落感也让他再度调整自己的客观性。“也许人家本来都不需要你,只是你需要他们而已。”他苦笑着总结。
即使是那些对镜头展现出喜爱的孩子,其实也并不知道这些影像将成为什么,或以什么方式呈现。当你在拍摄的时候,往往是拍摄之外的事情令他对你产生了信任,他就会觉得这个事情有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过程并非是绝对平等和真诚的,反而有点像“偷窃了别人的东西”。刘汉祥有些惆怅地说,窥视着他人生活的纪录片工作者们,应该被叫做小偷家族吧。

在那些拍摄过的孩子的生命历程中,刘汉祥会渐渐变得遥远;而他们对刘汉祥来说,就像在异乡遇到的小树苗,他甚至谈不上为他们浇灌过什么,他大概只是在旁边坐了一会儿,看了看天。
女儿出生前的冬天,他知道自己终于种下了自己的小树苗。北京正在下大雪,他写了一首诗,大概的意向是,你来吧,虽然我没有做好准备,但我把这个世界打扫得很干净,我的桌子上会放一杯铁观音,一支玫瑰花,我给你一个坐标,你来就可以了。




厂长语录
“我要做盗圣”
来源:箭厂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