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书情书》里有这样一个说法:一本书是文字世界的房子,变成铅字的文字就是从这栋房子里向外寻求对话的机会。
从《书情书》我们不难发现,德国学者布克哈特·施皮南(Burkhard Spinnen)对书籍的分类是有趣的——新书和旧书、大书和小书、昂贵的书和便宜的书。新书像是一个密封的罐头,没有生机也没有气味,甚至可能因为太新而让人心生畏惧;旧书则布满了历史的印记,它身上传递的信息是,它并不是一次性的消费品,它的价值在于流传中的一再被阅读。大书与小书也是不同的,厚重的大书如同不动产,是专属于富人和贵族的,有些书以身形厚重为荣,比如画册和摄影集,还有一些小书是轻巧而便携的——1900年问世的平装本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平装本也并不是书籍的终极形态,人们相信文字传播的下一步是使得媒介变得更小更轻,比如电子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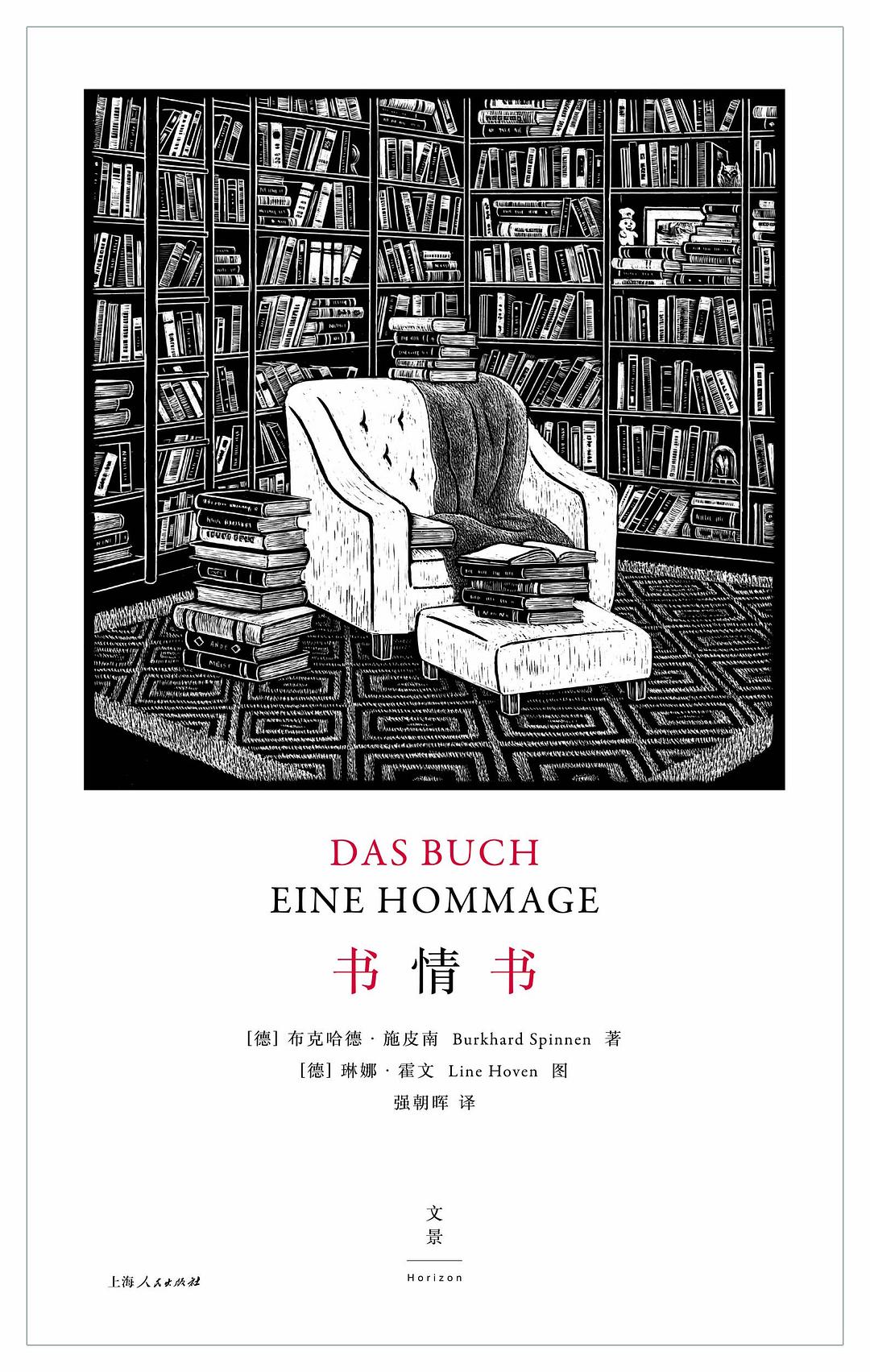
[德]布克哈德·施皮南 著 强朝晖 译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年2月
施皮南对于教科书也做出了描绘和评价。他写道,教科书是许多人一生中的第一本书,也是唯一一本书;与此同时教科书也是洗脑神器,它教会人阅读,同时也可能透过刚刚开启的心智之门,将乌七八糟的文字塞进人的头脑。“有些文字的作用不是启蒙,而是恰恰相反。一个人连字还认不全,便被一些充满成见的文字禁锢住了思想,或被各种甜腻腻的诗文迷住的心神。”更有意思的,作者还写到了被偷窃的书、被遗落的书、被查禁和焚毁的书,它们都反映着人类对于文明的态度,“说到底,人类对待书籍的态度标志着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将书当成工具或废料的人,要么是傻瓜,要么是恶人。
《书情书》中的个人阅读史也在呼唤着读者的共鸣。作者写下自己童年时刚刚踏入公共图书馆时的心情,也与读者分享了他是如何喜爱在跳蚤市场游荡、与某本书不期而遇的,同样他也怀念在二手旧书店与那些气质独特的老板聊天的机会。他珍视这些与书相遇的瞬间,因为他明白,就像一个书架只能摆放一定数量的书籍一样,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容纳的书籍数量也是有限的。4月正是读书月,界面文化经出版社授权,从《书情书》中摘录了相关章节,与读者共飨。
跳蚤市场
在过去几年里,我的购书方式和习惯渐渐变得理性务实了起来。这样的发现,让我禁不住有些惶恐。想来有类似经历的人,恐怕不单是我一个。因为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是采用邮购的方式购买书籍。这些人在发出订单前,通常都已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这样一来,一切都变得简单而快捷。 但同时,一家家小型书店却也因此走向了凋敝。这些书店的强项之一,恰恰是帮助那些事先说不出书名的人,找到自己需要的书。他们当中有的人是想给侄女选个合适的礼物,有的人是想在去伊维萨岛度假前,挑本书带到路上读。

“游荡式购书”(这是我自己独创的概念)的庇护所,是跳蚤市场。在这里,人们通常无法通过书名或作家名去查找书籍,以专题分类或按作者姓氏的字母顺序排列的书架也难得一见,更不会有当季畅销书之类的荐书榜。这里,只有一堆堆塞满了各色书籍的木箱或纸箱,你必须俯身躬背,甚至蹲下身子,才能看清箱子里到底有哪些货色。
在我的生命中曾有几个年头,我几乎每个周末都会跑去跳蚤市场,然后径直奔向一个个书摊。曾有几千本书被我捧在手中,仔细掂量,有数百本最终被我买下。在淘来这些宝贝时,我的心情时而是惊喜,时而是半心半意,甚或是漫不经心,信手拈来。有些书和我的藏书在风格上很搭,可以顺顺当当摆上书架;还有一些书,我却只能在原有的收藏之外为其另立门户。就像一个长年购买乐透彩票的人一样,我也曾中过几次彩头。具体地讲,就是用不多的钱,买到了昂贵稀有的珍本书籍,比如说卡夫卡和罗伯特·瓦尔泽的初版书。只可惜这些书多数都被我转手卖掉,好用赚来的钱继续供养我的藏书癖。
淘书很容易上瘾,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如此。受这一癖好之累,我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一个穷光蛋;可是,要说它会让我为此害病,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肯承认。当然,淘书的确是个力气活,这是无可否认的事。每逢跳蚤市场开张的日子,我都会一大早爬起床,咖啡顾不上喝,饭也不吃一口, 因为我整个人早已兴奋难耐,浑身上下都充满了元气。几个小时之后,我两手变得脏兮兮的,腰也疼得直不起来。这时候,一堆书已被我收入囊中,其中有些书,我以往甚至从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比如说,司法记者斯灵的书就是我在跳蚤市场初次遇到的,副刊作家瓦尔特·吉奥莱恩也是一样。到了晚上,我疲惫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手边放着一摞新入手的书和一瓶啤酒。那一刻,我常常会感到幸福无比。
我也常常自问:究竟是我选择了这些书,还是它们选择了我?这时我总是想:对这些书来说,它们毕竟要经历数十载的辗转迂回,才能在这个周六的上午,在克雷费尔德或是另外某个地方,与我的人生轨迹相交汇。这是纯粹的偶然?抑或更多是一种缘分?就像两个素昧平生的人,经过一路周折才终于遇到对方,并从此携手共度余生。
好吧,我知道,这多半只是一种美好的幻觉。假如我当时遇到的是另外一些书,我的选择自然也与现在不同。但是,每个热衷于寻找和发现的淘书人,他们的生活其实都离不开幻觉。他们与淘来的书之间,并不是顾客和商品的关系。对游荡于跳蚤市场的淘书者而言,其目标并不在于具体的需求和满足,就像在网上购书那样。说到底,真正吸引他们的,是那些幸运的瞬间,还有那些不可预期却让人受益无穷的偶遇。

公共图书馆
笼统地讲,在很长时间里,除教会或大学名下,图书馆一直是王公贵族的私人宝库,里面存放着金银财宝外的另一类宝藏,它是人类知识与精神的珍宝。很多时候,这些书籍对它们的主人而言,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拥有,而非使用。不消说,在那些年代里,的确诞生了许多美好的事物:教堂、宫殿、油画、雕塑、音乐、文学等。不过我们依然应当庆幸,那个时代终于成为了过去,至少在世界大多数地区如此。
随着王侯统治的结束,许多私人藏书变成了公共图书馆。这是启蒙运动的一大功绩,是社会迈向民主化的重要一步。只有具备了知识,人们才有能力表达观点并提出异议知识即力量。
那一年,当9岁的我刚刚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市立图书馆办下借书证的时候,我对这一切还浑然不知,也没有太大兴趣。当时,图书馆大楼就在今天的位置。它地处老城中幽静一隅,与购物街相隔只有两百米,旁边是一个小公园,四周是一片十九世纪建造的民宅。大楼本身是新建的,从网页上的资料看,当时建好还不到三年。当然,那时候我对这些同样一无所知,也同样不感兴趣。
话说回来,1966年或1967年冬天时的我,或许根本就没有把这座大楼和图书馆对上号。在一个9岁的孩子眼中,那只是一栋装着书的房子而已,里面的一切也都很平常。一进门,旁边是一排窄小的柜子,可以用来存放书包。再往里几步,就是少儿阅览室。大厅宽敞明亮,透过高大的落地窗, 可以望见阴凉安静的内院。一排排书码放在书架上,被窗外射入的日光映照着。门口摆着一张长桌,是办理借阅手续的地方。我感兴趣的,便只有这些了。不,还有一点!我一直很想知道,到底有什么法子,能让我把12-14岁年龄段的书借到手。要知道,我的出生日期就写在借书证上,而办理借阅登记的阿姨又总是一脸凶相。我实在想不出招数,只好乖乖地等,等待自己长大到12岁。为了让时间过得快一点,我几乎读完了书架上所有9=11岁的读物。
门兴格拉德巴赫市立图书馆青少年部,是我今生遇到的第一家图书馆。在第一次圣餐礼上收到亲友相赠的厚厚一摞书之前,我家从来没有过一本书。在我的亲戚朋友当中,也没有哪个人家里有书架或书柜。可是,为什么当我第一次走进图书馆,便立刻感觉那是属于我的“地盘”呢?或许是新奇所致,倒也说不定。但不管怎样,只一眼我便爱上了它。
首先,当然是因为那里的书多得数不清,如果不是我想借的书恰好被借走,图书馆里的书永远都是应有尽有。另外,我还喜欢里面的气息和氛围,每一处都和校园迥然两样:没有人乱跑或喧哗,也没有人故意用胳膊肘冲撞我,或用言语讥讽我,让我不得不一次次确认,自己是个样样不如他人的笨蛋。我爱图书馆里的秩序,也爱管理员的铁面无私,虽然正是这一点害得我为了读到下一个年龄段的书,苦苦等了好几年。就连无聊繁琐的借书手续也让我欢喜,就算为此排队又有何妨?还有那事先规定的借阅期限,是它将我的生命按照阅读时间,分割成了一个个美妙的段落。

但是,对这家我深爱的图书馆来说,我却最终变成了一个“坏人”。按规定,我必须等年满16周岁,才能转入成人部去借书。可我不想等那么久。就在我13或14岁的这一年,我怂恿父亲去办了张借书证,然后拿着这张卡片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成人阅览室,那里的面积要比少儿部大出好几倍。我翻看索引找出我想读的书,然后努力模仿大人的笔迹,把书名写在一张纸条上。接下来,我必须打着父亲的旗号,用他的证件才能借出这些书。每次做这些事的时候,我都手抖得像是做贼,以为这一次定会被戳穿,然后乖乖束手就擒。可是从没有人识破我的诡计,就连纸条上的字迹也没人会多看一眼。如今,我要对门兴格拉德巴赫的图书管理员们说声谢谢,因为是他们的粗心抑或是智慧,才让我有幸在不到16岁的年纪,便读到了大量“少儿不宜”的文学作品。
不久前我听说,“我的”第一家图书馆已经被列入文物保护项目。官方对此的解释是,“它以建筑之形式见证了西德‘二战’后为社会变革所付出的努力,其公开透明之机制,使 一个民主开放社会所崇尚的价值得以尽现。”
每一字每一句,我都发自内心地赞同。
书店
书店的样子看上去很像是图书馆,可它并不是。对书籍来说,书店的角色更像是一处驿站或临时寓所,而旅行的最终目的地是读者或其他某个地方的书架。和图书馆一样,这里的书籍也被分门别类,整理得井井有条。但是,这种秩序是一种机场和火车站式的秩序,其主要乃至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让转机和换乘变得更快捷。绝不能让任何一本书在书店滞留太久,以致于变成旧书。在这里,所有的安排都是为了加速周转。店家总是根据季节和时令,并参照媒体宣传和热销榜单,对书籍的码放不停地做出调整:两摞书眨眼间就被互换了位置,一排书架如闪电般被腾空,又塞满了新书。
对热爱文字的人们来说,书店是论坛、酒馆和集市。在这里,每个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去搜罗信息,了解最新的热门话题,在聆听先哲的教诲之余,再翻翻当下流行的鸡汤文章。而且,人们还可以把货品拿到手里,用各种方式去掂量。比如说,拉开书中的折页,欣赏下里面的插图,再挑两段文字试读。记性好的人,还可以默记几条有用的公式或诗句,而不用担心因为偷窃被警察找麻烦。
话说早年间,街上经常还可以见到模样不像图书馆的书店。这些书店通常都是由店主亲自去挑选图书,再亲自经营和打理。走进这样一家书店,仿佛强行闯入了店主的私人阅读世界,那感觉难免会令人有些不适。这是因为,面对正在专心读书或整理藏书的老板或老板娘,人们总是担心自己会打扰他们。从这里买走一本书,就像是给一个精心打造的宇宙添了一个缺角。在这个宇宙中,市场规则和热销榜不再受到重视,甚至被彻底抛到了一边。假如你不顾这些,执意要做出亵渎它的决定,那么不管你愿意与否,你都会在接过老板递过来的包装好的书的同时,得到一句他对这本书的点评,而且是免费的。
但是,这类书店如今变得越来越稀少,甚至正在走向绝迹。这实在是令人惋惜。其实,早在我刚刚开始买书时,这些书店已经不多见。在今天的许多大城市,这样的书店更是无处可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时,还出现了一类面向特殊读者群的专业书店。这些读者包括女人和孩子、同性恋者、秘教徒或其他宗教门派的信徒。在这些书店里,站在柜台后面的,也不是满脑子生意经的商人,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有信仰的商人。可即使是这类书店,也早已变成了稀罕物。
大约在二十多年前,我曾有幸结识了一位年轻的老派书商。当时,我在北威州的一座小城市,为我新出版的小说集开办了一场读书会。活动结束后,这位年纪比我还要小几岁的书商,请我为他签了三十本签名书。当我问他是不是对销售过于乐观时,他神色庄重、不带一丝嘲讽地回答说:“来我这儿的人买什么书,向来都是由我做主。”
我刚刚在网上查了下,这家书店依然开着,店主的胡子比当时长了很多,可颜色还像当年一样红。我在此衷心祝他好运。
旧书店
旧书店是时间退场的书店。这里没有应季生意,也没有摞成山的短命畅销书。旧书店里全部(或几乎是全部)的书,都已经被卖过一次,有些甚至是几次。在书的前页或末页上,标着各种货币单位的价格,有些货币甚至早就不再流通。没有人再为这些书卖力宣传,书的封套设计也早就和市场与时尚脱了钩。就像书店一样,旧书店也是书籍的中转站,只是在这里,等待不再是一件令人焦急的事情,反过来,这似乎已经变成了其存在本身更美好,也更可敬的一部分。
和书店相似的还有,在光顾这里的人当中,有的是直奔目标而来,也有的人更愿意听听别人的建议,或干脆是想来碰运气。但有一种买主可谓旧书店所独有,这就是狂热的淘书迷。这些人在来的时候,多半都揣着一张长长的清单,上面罗列着自己梦想的目标。为了让梦想成真,他不知疲倦地在书海中徜徉,想象着书架上有一本书一直在默默地等待着自己(而且只他一人)。这种想象令他迷醉,身体如通电般注满了能量。这种寻宝的快乐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有可能被超越:当他意外地淘到一本从来不曾耳闻的书,而且这本书从此后就变成了他所有藏书中最心爱的宝物。
一个人可以喜欢,甚至爱上一家书店,但旧书店却不同。它要么让人反感,要么令人沉溺于其中、难以自拔。我最刺激的一次淘书经历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维也纳。未来某一天,这个城市或许将成为整个中欧最后一个还有旧书店的城市。这些旧书店仿佛是一座座墓穴,里面埋葬着尚未死去的书籍,它们经年累月地守候着,等待被某个读者赎身以获得重生。

在维也纳,我遇到了一位旧书商。打那之后,他就成了我眼中整个职业门类的化身。当他注意到我对哪些书感兴趣时,立刻兴致勃勃地讲起,上世纪三十年代,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曾在现场听过卡尔·克劳斯的讲座。在这间散发着霉味的小店里,我就这样被这个男人引领着,踏上了一场文学回顾之旅。同时在他的诱导下,买下了几本价格昂贵的初版书。在我犹豫的片刻,他甚至还解释说,他其实根本不想把这些书出手,因为那里面蕴藏着他太多的回忆。于是,就在这个午后,我把整个旅行的钱花得不剩分文。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旧书商就住在店铺深处一个狭窄的隔间里。我曾透过门缝偷偷向里张望。屋里的景象十分凌乱,在一张行军床模样的床铺边上,摞着一堆堆小山似的书。旁边的小桌上,紧挨咖啡壶和茶杯也堆满了书。整间店铺本身,都被书塞得满满当当,让人几乎转不开身。每个书架前的地上都堆着书,我必须先把它们移开,才能看清书架上的书。要是地上太挤,没法挪动书堆的话,我只能弯下腰,像猜谜般努力去辨认一个个书名。在被压弯的书架搁板上,书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没有一丝缝隙。每次从上面抽出一本,都让我心惊胆战,生怕整个书架会在那一刻轰然倒塌。
以前我总以为,灰尘是没有味道的。那一次我才知道:灰尘是有味的,而且味道浓烈,甚至令人心生恐惧。
文摘选自布克哈德·施皮南《书情书》,由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刊出,小标题有改动。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