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起曈(斯坦福大学本科生)
编辑:张潇冉
想像之中的公平?
一年前,我曾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过一篇读者来信,全文的口径与教育部提倡素质教育的改革方向大致吻合,但在社交网络上,这封信受到了一边倒的批评——
“就现阶段而言,素质教育是只有在发达地区才能进行的。”
如果没有应试教育,“很可能会更加地变成只有富人的孩子才能接受更好的教育,也就是社会阶层更加固化和两极分化。 ”
甚至有人表示,

“要是硬推素质教育,中国就要有起义了。”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科举制度自6世纪开始实施以来,逐渐稳定成为了寒门子弟跃向上层的唯一方法,为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严格等级秩序提供了阶级流动的机会。在久而久之的熏陶下,对中国人而言,教育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学习知识,不如说是为了改变命运——通过自身的努力克服家庭出身的不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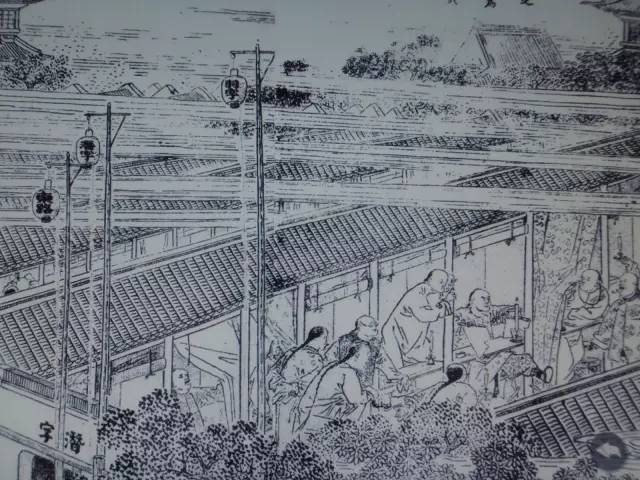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语境中的教考体制就这样日积月累,演化成了一种工具,为普罗大众提供了对公平的憧憬。
然而很难说这种憧憬在多大程度上符合现实。各个省份的招生名额在高考前已经预先划定,这也意味着不同地域的考生起初就无法站在同一起跑线竞争。
2004年前,除北京、上海外,全国大多数省份均采用同样的试题,因而一所大学在全国各地的招生分数线会不尽相同,这无异于是对高考公平最直接的冲击。

2015年北大自主招生简章(图片来源:北大招生网)
或许是因此,2004年后,14省开始自主命题,使得各省的高考试卷无法直接比较。但此举并未真正从根源解决问题——2015年,公立的北京大学的高考计划录取率在北京为0.27%,在上海为0.05%,在江苏为0.01%。
程序的受害者?
上述种种问题都体现在考生和家长无法看到的宏观层面——在美国,如果大学愿意招收一个学生,该生就可以选择前往这所学校就读,而在中国,录取过程需要政府部门的计划。但是,一旦计划出现偏差,制度的纠缠真正影响到的往往是微观的个体。
一心梦想踏入清华大学的江西考生王希在今年的高考中取得685分,成为了自己家乡的“状元”,这一分数也恰好达到了清华制定的录取分数线。但满心欢喜的他最终等来的却是失望——省考试院认可的清华分数线是686分,因而直接将他的档案投给了另一所大学。
最终清华无法提取该考生的档案,也就不能完成录取流程,考试院坚持认为自己无可指摘,毫无违反教育部的规定,而王希只能与清华失之交臂。
录取计划甚至不仅划定决定了各省的招生人数,甚至还细化了每个省不同专业的限额——换言之,2015年任何河北考生都无法报考北大法语专业,任何河南考生都无法报考北大俄语专业,而这一切只因某个计划的制定者大笔一挥,将法语和俄语专业的名额分别随机划给了这两个相邻省份。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高考承载了不仅延续了科举式的公平想像,更继承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衣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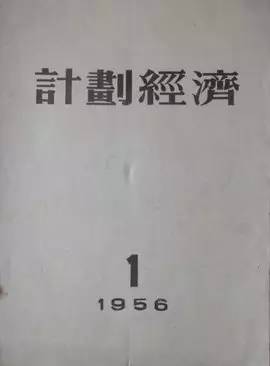
1950年代的出版物《计划经济》(图片来源:百度百科)
是制度,还是思维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政府仅在1934年要求各大学文科各系平均人数不得超过理科各系。
除此之外,各校享有高度招生自由,全国也逐渐形成了类似欧美国家的单独申请报考模式——与如今的美国大学申请情况类似,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同时报考多所学校,因此,同样与如今美国大学招生的情况类似,不同级别的学校新生报到率也相差甚远。
可以想见,这一模式在1949年后必然不会久留。当时的共产国家普遍信奉普列布拉津斯基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市场调节效率低下,发展缓慢。将这一理论推而广之,欧美式的招生制度成为了缺乏国家控制的典型反例,必须加以根除。
1952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收新生的规定》,决定在当年启动首次全国统一高考,各校招生名额和录取要求全部由政府核准。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高考被彻底废除,中国的大学也几乎全部荒废,但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迈入市场化经济改革时,高考选拔中的计划成分依然被保留了下来,而且这三十余年来,随着社会的惯性而不断加深。
我高一在密苏里的一所私立高中交流交换学习时,接待家庭看到了中国社交网络上考试结束后全年级学生集体撕书“狂欢”的照片,表情写满了不解和担忧,但作为一个中国学生,对自己的课程几乎没有选择权,所学大部分内容的唯一意义仅在于考试需要,因而,高考之后,教科书似乎也立刻失去了意义。
近日,湖南省南华大学甚至决定用抽签“抓阄”的方式决定学生的专业取向,在这种情况下,公式化地机械备战高考,考完后就撕毁教科书,似乎顺理成章。
本文为《我在斯坦福的课堂上,回看中国高考制度》系列文章第三篇。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