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跟世界上任何国家可能都不一样:爱沙尼亚的历史是“唱”出来的。
无论是被德国、丹麦、瑞典还是被苏联占领,爱沙尼亚长久以来一直都依靠着音乐,在外国势力的统治下艰难保持着部分民族意识。
这个国家从1869年起就举办大型歌会了,到现在已经成了一项特别的传统。每每看着大约2、3万人的合唱团,以及超过10万的观众,这样的场面就让人感慨——要知道,爱沙尼亚的人口也就130万左右啊。


但近年来,随着爱沙尼亚开始拥抱世界,这个国家的音乐有了不一样的意味,而这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爱沙尼亚的音乐失去了它的本质了吗?如果真的如此,我们是应该感到遗憾还是为之欢欣?
在苏联时期,爱沙尼亚的歌会包含了不少苏联国家的宣传元素,但它们本身还是为国民们提供了一个庆祝自己语言与传统的机会。
在苏联统治下的第一年,1947年的歌会上,作曲家Gustav Ernesaks将一首老诗“Mu Isamaa On Minu Arm”(我的国,我的爱)改编成了歌曲。爱沙尼亚人民在接下来几年的歌会上都表演了这首歌,借此来挑衅苏联政权;很快,此歌在某种意义上就成了爱沙尼亚的非官方国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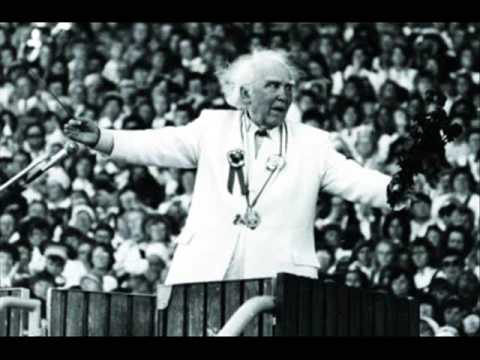
其他的爱沙尼亚音乐就没有表现出那么明显的民族主义:比如Veljo Tormis等作曲家,创作了一首关于列宁谈自由问题的歌曲。这里面藏着双重意味,一方面表达爱沙尼亚人民对自主决策的渴望,另一方面指出苏联没有遵守他们开国者立下的原则——在那时,所有的东西都要先经过审查。
在1980年代后期,音乐成为了爱沙尼亚脱离苏联的重要手段。在“歌唱革命”运动中,大批民众就在聚众高歌的伪装下组织起来为争取独立而奋斗。1988年6月,10万爱沙尼亚人就连续5晚聚在一起,高唱抗议歌曲直到天明。

当时的人权活动家Heinz Valk写道:“在节日上高歌《我的国,我的爱》是我们国家最荣耀的表达自我的方式。而一个通过歌声和微笑来进行革命的国家值得成为所有国家的榜样。”这场运动在1991年爱沙尼亚通过非暴力手段取得独立之时达到顶峰。

这种每5年举办一次的歌会在现在依旧吸引着大批观众,同时也继续培养着爱沙尼亚人民的国家意识。
“你可以想象在一场棒球赛上3万人齐声高歌,”在2007年与丈夫一同拍摄纪录片《歌唱革命》的美国制片人Maureen Tusty表示,“但歌会上唱歌的都是专业的合唱团。你会为他们的声音和音乐的力量而倾倒,那是一种内心的洗礼,你能够从内而外地感受到那种力量。”

然而如今,爱沙尼亚的许多音乐跟这种音乐遗产已经没有太大关系了。
“我不认为我们真的受到了多少传统民间音乐的影响。”爱沙尼亚流行摇滚乐队Ewert and the Two Dragons的32岁主唱Ewert Sundja这样说道。他表示,乐队的最新专辑摒弃了爱沙尼亚的音乐元素,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国际风味。
爱沙尼亚脱苏取得独立的时候,Sundja才8岁,因此他的成长过程中主要是用黑胶唱片听英美的音乐。像史提夫·汪达(美国黑人歌手)、雷·查尔斯·鲁滨逊(美国灵魂音乐家)、弗兰克·辛纳屈、皇后乐队和披头士乐队对他的影响远大于国内音乐,而这主要是因为“爱沙尼亚没有那么多酷炫的乐队”。而如今,爱沙尼亚电台里放得最多的也都还是外国歌曲。
Sundja的乐队创作的歌曲都是英语歌词的,他们的风格也更像是梦龙乐队(Imagine Dragons,美国独立摇滚乐队)和Bon Iver(美国乡村民谣歌手)的风格综合体。

在苏联占领爱沙尼亚的期间,西方流行音乐常常是被禁止的,而那些不想被苏联限制艺术表达的音乐家们一般都转入了地下创作。
而随着国家的独立,流行音乐、朋克和摇滚音乐家都有了更多的自由,然而基础设施的不足还是限制了他们的创作与表演。在1990年代,欧洲流行音乐攻陷了爱沙尼亚的电台(Sundja称其为“噩梦”),直到互联网的普及,才让人们能够接触到更多流派的音乐。

如今,爱沙尼亚国内的音乐尚处于发育状态。5年前,国内音乐家走出国门去表演都还极为罕见,即使去也只是去邻近的芬兰和拉脱维亚。
但现在政府开始对音乐产业投资,为那些有潜力的音乐家提供资金支持走出国门,和国外艺术家们展开合作。爱沙尼亚的大学也开始提供有关文化管理和音乐市场方面的课程。而国内也自2009年起开始举办“塔林音乐周”——今年吸引了来自26个国家的204名艺人,当然,一半的表演者还是来自爱沙尼亚国内艺术家。

音乐周的创始人Helen Sildna表示,小国家需要培养自己的创意人才,“艺术家就是你的创意品牌,他们可以是国家的文化大使。”
Sildna以摇滚乐队Ewert and the Two Dragons举例,这支乐队刚刚跟美国Sire唱片公司签下了合约。而签下他们的人,之前也曾签下过麦当娜等巨星——这或许就是爱沙尼亚音乐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

但融入全球音乐发展,同时也意味着有失去爱沙尼亚独特的民族元素和政治色彩的风险。
这并不代表着爱沙尼亚的传统音乐就这么遗失了,毕竟爱沙尼亚作曲家阿沃·帕特(Arvo Pärt)等人的古典音乐在当下依然很吃香。但有一件事是可以确定的:“歌唱革命”发生近30年后,爱沙尼亚本土音乐的构成正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个国家的音乐创作已经融合了许多不同的流派风格了。

许多在后苏联时代出生的爱沙尼亚年轻人会觉得,那些曾经在歌会上风靡一时的音乐与歌词都已经老掉牙,并很难再让人产生共鸣了。电子音乐DJ和古典音乐家Sander Mölder的童年是在歌会的合唱团里度过的,他表示,爱沙尼亚音乐整体上来说,就像这个国家一样,“非常年轻而且很脆弱”。
然而制片人Andres Lõo认为,让年轻音乐人继续从民间音乐中寻找“独特性”的做法已经过时了:“为什么在我们有了新的音乐之后,还要继续听那些过时的音乐?”
但这个问题同样也给音乐人带来了困扰:如果说从传统民间音乐中继续汲取灵感已经是陈词滥调了,那还有什么能让音乐创作保持民族性呢?

在“歌唱革命”来临之时,29岁的民间音乐家与学者Maarja Nuut只有5岁,但她还清楚记得当时的场景。她的父母都参加了爱沙尼亚的地下反叛组织,父亲被苏联的克格勃杀害。但Nuut表示,她的同龄人跟她不一样,大部分人对这些事件基本都没什么情感上的牵绊。
而现在Nuut的音乐创作结合了古老的爱沙尼亚民谣和现代的电子音乐元素,比如loop pedal,一种可以记录下一段声音然后不断地循环与添加的音乐器件。
Nuut表示,在给从未听过爱沙尼亚音乐的外国人演奏时,音乐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但她同时也认为不必太过追求给自己贴上“民族性”的标签。“当然,如果你能把自己想表达的话,跟这个国家的独特音色或气氛结合起来,那就是最完美的。”
(译者:李雨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想要获取更多有意思的内容,请移步界面网站首页(http://www.jiemian.com/),并在微博上和我们互动,调戏萌萌哒歪楼菌→【歪楼-Viral】(请猛戳这里)。
你也可以关注乐趣频道的微信公众号【歪楼】:esay1414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