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健翔,源计划工作室创始合伙人,主持建筑师
对城市的观察,对城市的批判性分析,一直融在我们的建筑思考当中,让我明白思考比工具更重要,仅仅掌握了工具的建筑师,可能本身也只是一个工具,而会思考的建筑师才能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
新与旧
耳濡目染的粤语文化圈,与随着时代发展进入的新的元素,注入我成长中的思想源泉。
我是土生土长的广东本地人,从小受到爷爷的影响很大,爷爷是传统的文化人,他以前开书店,对地方文化怀有饱满的情怀。从小爷爷带着我到处跑,看了很多乡下地方,虽然印象不深,但记忆里留下了老城墙的影子,以及关于那些地方的故事,所以我心里对这种物态层面的文化史也埋下了一份兴趣的萌芽。
我们这一代人受到粤语文化的影响很深。广府人基本上都说粤语,大家倾向于把所有不说粤语的人都当作北方人。这样自给自足的文化很有趣,这里有山有水,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又远离政治中心,没有过多的国企、单位,改革开放很早,私营企业比较多,所以在广州的生活比较自由、松散。
但同时,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作为贸易城市,广州自清朝开始便有通商港口,贸易最火热的时段,很多人才被吸引到南方。近在咫尺的香港与广州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状态也有很大反差,通过一些亲戚朋友从香港带回来的商品和提到的见闻,我得到一些比较真切的感受。珠三角接收了很多的外来文化,其中大部分都是通过香港传播直射过来的,这些新的元素进入广州,与旧的文化相融,汇集在一个时间段里。来自港台的英文音乐传进来,本土音乐夹杂着摇滚音乐,这些变化体现在建筑上,便开始萌发出新的东西。

家乡江门骑楼街 摄于1995
不同的文化融入广州,赋予这座城市很强的包容性,过去的交往流通留下了很多痕迹,文化的融合和嫁接形成了广府的独特味道。
对我来说,自由成长于粤语文化圈,感受到各种新旧、东西的文化碰撞,也因此过于安逸粤语文化区的生活,连报高考志愿时也没考虑过超出此范围的选项,大学去了华南理工大学。进入大学后面对一个新的集体,虽然同学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广东,但从中融合了众多不同的地域文化,比如潮汕的同学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广东味。
这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陌生化
从选择陌生的建筑专业,到决定进入陌生文化寻找自己的理想,我一直在把自己推向陌生化的空间。
作为工科的建筑专业对我来说很陌生,我心中对艺术和设计带有朦胧的喜爱,在完全不了解建筑具体是什么的情况下,机缘巧合选择了建筑专业。但是从进入建筑行业开始,我就从没有想过要放弃。
在学校面对陌生的专业,我的愿望是要做一个好学生,既希望能够得到老师们的认可,取得好的专业成绩,同时又不完全认同和接受这种以高分换取认可的方式,所以我的状态并不让自己确信。
作为学生,我们会跟老师进行讨论,但是每一个学生的对话方式是有差异的。有的成绩很好的同学比较了解学校和老师的要求,也有同学比较自我,喜欢发起跟老师的争论。相对而言,我性格比较内向,跟老师的对话比较平和,但我自身还是自己的矛盾和挣扎;我没有挑战现有体制,也希望能得到体制认可,但内心上我希望尝试不同的东西,渴望自己专业学习的内容有一定的突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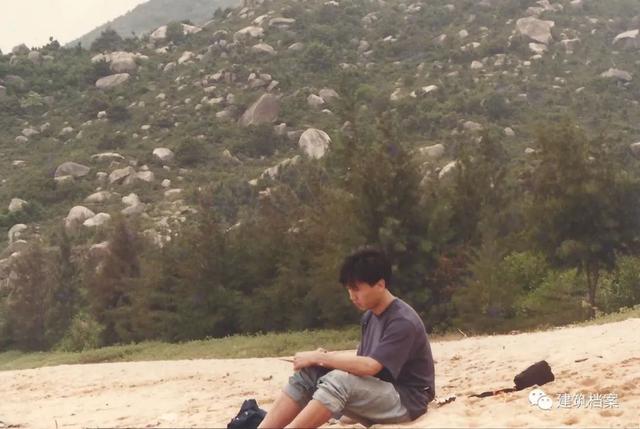
高中阶段户外写生 摄于1988
因为专业的关系,在学校里开始接触到国外的杂志,从这些杂志上我看到很多不同信息,了解了一些不同方式,有些东西对自己的冲击力很大,自然我会好奇这些形式是怎么来的。经过自己的琢磨,我能明显感觉到一些跟我们在学校中不一样思考和设计方法。但在那个年代很难有系统的学习和讨论,只能自己瞎摸索。
当时的各种理论、思潮对我充满了吸引力,好奇所致,我花了不少时间去阅读和思考,我尝试去阅读所谓后现代、解构这些理论,我还曾经试着在学生刊物上发表理论性的文章。这种蓬勃的理想主义状态很真实,促使我思考现在的状态与我理想的状态。

大学时期 摄于1993
毕业之时,我面临留在广州的大型设计院和回到家乡的小设计院两个选择,考虑到在本地文化可能得到的更多机会,我回到家乡的设计院工作,在这两年左右的体制内工作过程中,我渐渐发现自己很难长久在这种体制下工作,当时几乎所有项目都是原始的地产项目,内心感觉建筑不能这样做,但又无法道出个知乎所以。
之前在学校的那种对于理想状态的追寻似乎复苏了,让我更加坚决地寻求离开这种状态。
对我来说,出国是一个很好的转换机会,以便梳理自身的思考以及对建筑的谜团,并让自己接触更多不同的知识和思考方式,我萌生了出国的想法。
家人难以理解我的想法和决定。他们对完全陌生的状况充满忧虑,希望我留在从小扎根的家乡,继续从事一份稳定的设计院的工作。然而,当时的我抱着纯粹的理想,尽管不知道出国之后会遇到什么、能做什么,我还是决定把自己扔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尝试。
最终家人支持了我的想法。在父母为数不多的对外联系中,曾有好友早年从国内到香港和国外的,也发展得很好。通过和他们的交流父母也理解这种选择中潜在的机会,同时他们能感觉到我的坚决,因而一定程度上相信或许我真能找到自己的路。
独立思考
“你为什么选择做这件事?”是我处于不同于国内文化时,遇到的第一个难题。通过对自己思维模式的调整,我逐渐明晰了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知道的我们那个年代学建筑的人好像都向往美国,出国的同学也基本去了美国。我的英文不好,也无法取得美国学校奖学金,不可能拿到美国签证,所以在选择国家的时候,我出现了短暂的纠结。
跟我关系比较好的一位华南教授,提醒我可以试试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一个国际人居研究中心,有联合国资助,学费很低,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几经周折后我申请去了欧洲。出国那年我25岁。

罗马梵蒂冈圣彼得广场 摄于2002
去国外之后,很多经历都是在意料之外,包括教育方式、建筑方式和文化差异。由于签证原因我刚去学校就面临毕业论文的开题答辩。我需要确定自己的老师和研究方向,学生的专业背景不同,课程很混杂,有规划的,也有建筑的。我选择的方向是设计,在课上讨论的话题跟我在国内的学习模式完全不一样,那对我来说是第一次遇到的巨大的文化冲击。
在国内或者说广州,人们生活或工作的状态很务实,一是要挣钱,二是建筑师要用自己的建筑去解决问题,解决需求。然而,西方严谨的建筑教育完全不同,他们的教育体系特别关注理性的思辨,注重理性的思考。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这种根本性的问题在我们的教育里面是没有的。被问到的时候,我完全答不上来,加上语言的障碍,几个老师扑面而来的批评让我整个人大脑一片空白。从本科学习开始,我自认设计还是挺不错的,从未面对过这样对设计论题完全空白的状况。
这是一个涉及到人的问题,说白一点,就像西方的哲学问题。“你为什么活着?”“你为什么做建筑?”这是相同的问题。他们对我提出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难题,不仅是他们对我的拷问,也是我拷问自己的开始。当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发现需要把之前所有的知识都先扔到一边,清空自己的思维再去重新思考。

人在欧洲
现代社会让人过于急躁,急躁之中会错失很多宝贵的东西。我觉得年轻时历经磨难的过程会变成一个人日后的财富,因为它在帮你积淀思考的能力。很多表面上无用的东西,可能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类似我们所习惯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我要利用它来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之类的问题都是功利心态的体现。来到欧洲,进入到了另外一种文化,开始尝试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回看自己的文化,会看得更清晰、更透彻。
重新思考也好,融入一种新的文化也好,是一个很难的过程,因为所有的课程编排跟我之前接触的都不一样,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知识架构。我面临着把自己原本的东西放下,这是很痛苦的过程,相当于从零开始,但是一旦真正进入到跟以前不一样的状态,反而给我一种新的自信。
在国内的学校,我们掌握的技能只是工具,而学会思考才是真正的核心能力,通过思考建立起自身的一套逻辑思维,学会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来找到自己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开始真正驾驭一些对空间的思考,对城市的思考。
这一年时间内,我完成了我的论文,并且得到了设计论文的最高分数。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真正找到了自己设计方法的基础和努力的方向。
新的原点
2003年从欧洲回国后,我在想凭借自己经验和知识应该以何种方式参与到城市开发建设中的问题。那时候国内、至少在广州还没有独立建筑师这一说,我开始的想法比较单纯,几个同学在开展商业合作方式,跟他们合作,各自在商务和设计有所分工,后来发现这个想法不太可行。
在摸索中,我开始接触一些可能的项目,刚开始做的时候,小规模项目的机会少,都是地产项目或者很大的项目,面对这种情况,我需要给自己一个定位,“我要去做什么?”

源计划麦仓工作室 摄于2013
回国工作初期做了几个项目,积累了一定的实操经验,给我最深刻体验的是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项目。这个项目我从竞赛前联络到跟同行组成一个设计联合体参加竞赛得了第一名,然后一直跟进到项目建完,时间不长,但这个过程中让我比较清晰地经历了一个项目的过程。
与出国前相比,我对于自己的专业方向明确了很多,但在欧洲待了四年半,我已经很习惯国外的生活节奏,以至于刚回国那段时间花了很长时间去适应国内的文化环境。在沟通问题上,在欧洲的经验是大家提前很长时间通过邮件把计划安排好,一个月后的事情可以很清楚,具体到哪一天要做什么。而在国内总要通过电话、聊天,让大家有充足的变化余地,任何事情都是在博弈,感觉非常消耗精力。朋友会觉得我的行动缓慢,连走个路都跟不上社会的节奏。在这种慌乱急躁的调整状态中,我花了至少两年的时间才恢复过来,重新适应了国内的生活。
2007年,我们正式成立了独立的工作实体。当时的理念是建立在对设计的追求上,希望通过设计(在可控范围内)改变社会和文化,很明确的一点是庞然大物类的建筑不是我们想要的,也不是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做的东西。
我们想法很简单,试着自己独立做项目,哪怕是很小的项目,只要可控可实现就值得去做。我们没有给自己留什么后路,从大的公司合作里面全撤出来了,就这样一步一步,秉持着自己的原本的理想走到了现在。

与合伙人蒋滢在设计项目中合影 摄于2019
回过头来想,自己独立执业,意味着我又回到一个陌生的起点,就如同之前的很多次,我都是带着自己的想法靠近未知之源,回到零点的位置。到国外,就先把原来的知识放下;在国外学习、工作多年以后,回来又重新整理出一套新的体系,才能重新开启,这样又是一个原始的状态。
我们会面临慌乱和痛感,还有各种压力持续涌来,但是我能明确感觉到这样的状态是一个对的状态。我很希望持续地保持着那种未知而可达的状态,这是最好的状态。
本文图片由源计划工作室提供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