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粮食计划署近日发布报告称,新冠疫情沉重打击了世界各地的经济,加剧了食品危机并带来饥饿风险,没有任何地方未受影响,27个国家濒于危境。据新华社8月11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制止餐饮浪费行为作出重要指示。本文摘自微信公号食通社(foodthinkchina)作者孙天舒撰写的《饥饿》书评(编辑:春晖、天乐),略有删减,已获授权。
“有人会说‘谈论饥饿有什么意义?这于事无补还很无聊’。于是,我决定要写一本关于饥饿的书。”《饥饿》的作者,阿根廷记者马丁•卡帕罗斯(Martín Caparrós)如是说。
1.“没到场的人请举手”
饥饿问题变得不痛不痒的一个原因是,在种种关于饥饿的讨论中,我们很难听到8.15亿人饥饿者的声音。真正深受饥饿之苦的人根本没有到场,因为他们饿得发不出声或者疲于糊口没空为自己振臂一呼。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报告来自宽敞洁净的研究机构办公室,采集自田野的事实也会被整理成干净的数字和图表。这是一个原告不能出席的庭审。脱离了挨饿者进行的关于饥饿的讨论,就像是说“没到场的人请举手”。
饥饿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在什么地方肆虐?什么造成了饥饿?为了从缺席的人那里得到答案,卡帕罗斯走访了七个国家:从处于干旱的萨赫勒地区的尼日尔,到经济排名世界第十、营养不良人口数量却位居世界第一的印度,从资本和机器日日夜夜洗刷农业的美国,到“生产了3亿人的食物却没法养活400万公民”的大豆之国阿根廷……

他深入到饥饿发生的现场——在茅屋下、垃圾山上、油炸食品店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中,与见证者交谈。有人在热水里徒劳地煮着几颗豆子,有人刚刚茫然地裹起奄奄一息的孩子的身体,有人从垃圾山上捡来快餐店丢掉的冷冻炸鸡,欢呼雀跃。来自7个国家的几十个故事,每一个都关乎和你我一样真实的人类及他们所经历的旷日持久的饥饿。一顿顿的食不果腹积累成隐忍、沉默而痛苦的常态。这些琐碎但真实的对话将“饥饿”从宏观的数字剥离出来。
卡帕罗斯并不满足遵循“结构性饥饿”的框架——他认为“结构性饥饿”的概念把饥饿的原因分解为气候、资源、人口、产能等多个板块,却不去触及饥饿的真实意义。他说:“不存在‘饥饿’。存在的是人吃不饱饭这件事。我们很难理解在那种情况下要如何生存下去,因此我决定前往不同的地方,探访饥饿的人,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生活并记录下来”。短暂的饥饿是一种令人不安的生理感受,长期的饥饿是一种困顿低迷生存状态,一种无法反抗的宿命:“最极端的贫困,是那种夺走了你的想象力和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勇气的贫困。”
你生病了,你感到虚弱、嗜睡、失去工作的兴趣,却依然要挣扎着照顾自己。对一些人来说,他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这样的状态,只不过,他们没有变得更好的可能性了。
这是我们所谈论的“饥饿”。8.15亿人的日常。
教科书或官方报告中关于饥饿的数字,真的将这个问题呈现清晰了吗?
2.饥饿:从来不只是粮食不足
饥饿是如何形成的?很容易想到的是因为食物供给的不充足。例如,由于自然和社会禀赋的匮乏,粮食收成不能满足人口消费。FAO在今年3月发布的《全球粮食危机报告》也将“气候变化”和“战乱”对农业生产的强干扰列为造成粮食危机的最主要原因。但事实上,目前世界粮食产量足够喂饱100亿人。这可能听起来很可笑:我们的食物生产其实是过剩的。
为什么过剩的食物未能喂饱有限的人口?首先是食物浪费:FAO在2013年的报告《食物浪费足迹》中指出,“全球每年有13亿吨食物被浪费,这相当于我们已经生产出的粮食的三分之一。”一类浪费发生在生产环节,即收获和贮存过程中的浪费;一类浪费发生在消费环节——购买完成后,被过量购买的食物在家里腐烂,最终被扔掉。FAO在2012年的报告中指出,欧洲和美国的消费者每年浪费100公斤食品。世界上最富有的二十个国家居民每年浪费的食物总量为2.2亿吨,相当于整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粮食总产量。“一切人丢弃一些人需要的东西,一些人缺乏另一些人过剩的东西。”卡帕罗斯的笔下,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巨大的垃圾山上,上千人为找到被丢弃的香肠、薯条、狗粮、罐头你推我搡。“这个城市在2011年每天丢掉的粮食有200-250吨。"
其次,并不是所有的食物都是给人吃的。世界粮食生产的很大一部分流向了生产畜牧业饲料和生物能源。在美国,畜牧业消费了70%的谷物。而生物燃料对粮食的消耗更加密集:填满一个乙醇-85型油箱需要170公斤玉米制成的乙醇,这足够一个赞比亚人吃一年。卡帕罗斯在书中指出,人类社会每年需要用乙醇填满将近9亿个同等规模的油箱;如果将美国汽车消耗的农业生物质燃料换算成粮食分发给世界上所有饥饿的人,他们每人每天可以拿到一斤玉米。
在此,生物燃料是否在成本和温室气体排放控制方面有显著优势暂且不谈。但上述数字告诉我们两点:
一,虽然目前有8亿人吃不上饭,但解决他们的生存问题似乎并不是我们的头等关切;
二,如果我们依然将生产饲料和生物能源放在解决饥饿问题之前,那么即使我们通过升级农业技术、开垦新的农地、加大农业投资,使粮食产量如联合国所呼吁的那样在2050年翻倍,我们依然无法解决饥饿问题。
如果我们想解决饥饿问题,毫无疑问我们是有能力解决的。但是,我们真的愿意解决饥饿问题吗?
有充足的食物供给却无法充分地满足食物需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称之为“权利失败”(failure of entitlement)。个人可以通过生产、贸易或两者的结合来实现商品的拥有,这是人对于商品的“交换权利”;而饥饿意味着人既无法生产足够的食物,也无法通过交换获得足够的食物,即“交换权利下降”。阿玛蒂亚·森认为,权利关系的变化与分配的失衡才是导致饥饿发生的真实原因。但他没有解释的是在食物总量充足的情况下饥荒究发生的原因。
通过还原食物价值链各个环节上的参与者,卡帕罗斯试图回答这个问题,并认为其中的一大缘由是食物的金融化——目前食物系统的目的是盈利,而非把人喂饱。在这个系统里,食物被剥夺了“为人类进食所用”的本质,而变成高度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他指出,那些在大宗粮食交易市场上声称市场是最好的调节工具的人,实际上在人为的制造市场的“不正常”,并且从市价每分每秒的变化中获取收益。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考夫曼(Frederick Kaufman)在《食品泡沫:华尔街是如何让数百万人陷入饥饿然后脱身的》里面也提到:“食品更加商业化了,变成了一种投资,和石油、金银或者其他有指数的商品一样。投资越多,食物就会越贵,那些付不起钱的人只能挨饿。”
这组数据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这个问题:2003年,用于食品商品的投资额是130亿美元,2008年则是3170亿美元,增长了25倍。芝加哥交易所小麦的交易量是世界小麦年产量的50倍,世界上的每一粒小麦都在这里被反复交易了50次。粮食作为一种生活必需品本应有很低的市场弹性,但事实上,2008年一吨小麦的价格是2005年的三倍。
同时,全球化推动了国际贸易,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地由粮食贸易订单联动,粮食生产的主动权逐渐被发达国家把持;粮食涌向资本密集的地方,而非按需达到穷人的手里,粮食也越来越多的成为政治干预的工具。贸易的逐利性和粮食价格的虚高扰乱了阿玛蒂亚·森定义的“食物获取权”。购买力有限的人买不起口粮了,小农户也因市场信息的极度不对称而被迫承担巨大的生产风险。2008年,埃及的面包价格上涨了5倍,之后,便是“阿拉伯之春”。
卡帕罗斯说,饥饿不是一个农业技术问题。饥饿是一个权力和政治的问题。
饥荒和粮食过剩并存,这不仅仅是一个农业问题。
3.饥饿的隐喻
《饥饿》是一本让人读起来不舒服的书——卡帕罗斯的叙述在沉郁和高亢的节奏间快速切换,带着一种社会活动家不眠不休的激情和愤怒。比如,他讽刺我们太习惯于将“饥饿”归类为各式各样的主义,仿佛发明了“结构性饥饿”这个词就完成了理解饥饿的使命;比如,他批判大多数宣扬以人道主义解决饥饿的行为无非是利用着全球机制,而从不质疑秩序和权利;比如他无时无刻不在提醒你,还有人在挨饿,还有人在死去,而我们作为失败的食物系统中的一员,虽然对此几乎一无所知,却依然助纣为虐,难逃其咎。
在印度,卡帕罗斯去问一个村庄里的寡妇:忍饥挨饿不会让你感到痛苦吗?
他立刻为自己的问题感到羞愧:“我羞愧地感觉自己像坨屎。一只老猴子在房顶上叫着,我觉得他的意思是要我别再说话了。”
这让我有些释然:看来自己不是惟一一个在阅读过程中对书中的饥饿感到愤怒、无力又羞愧的人。这本书提醒我,如果真的关注贫困、饥饿和相关话题,那么产生以上三种激烈的情绪大概是一个常态。
我无法在几千字里概括这本书,概括卡帕罗斯所叙述的饥饿。因为那些对话、反思、情绪化的宣泄、怯懦、愤怒难以被凝练和压缩,也无法在图表和报告中展现——而“饥饿”,正是切肤之痛本身。
饥饿不仅仅是饥饿,它是一个关于人性、利益、权力的隐喻。“饥饿是一种分隔的比喻:一道他们与我们、拥有者与没有者之间、因为一些人有和一些人没有之间的断然的屏障。生态理论和气候变化给人们造成一种人人平等承担责任的感觉,而饥饿却正相反,饥饿是最具阶级性的威胁。我们很多人都清楚这不是我们的问题,那么,这为什么成了我们的问题?”
《饥饿》这本书会让我们重视和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明明知道这些事在发生着,却还能若无其事地生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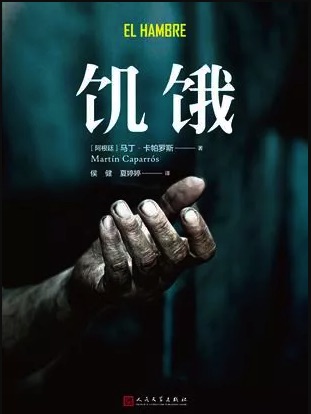
作者: [阿根廷] 马丁·卡帕罗斯/ Martín Caparrós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译者: 侯健/ 夏婷婷
出版年: 2017-6
定价: 58.00
ISBN: 9787020126682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