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互联网指北 张凤姑
编辑|蒲凡
宝财哥是个影视人物,出自《我爱我家》第23集、24集《双鬼拍门》,设定是一位包工头卷款逃跑、自己讨薪无门,只得寻亲访友凑够盘缠的农民工。在这部长达120集的国产情景喜剧巅峰之作中,他的戏份充其量只能算“友情客串”。
可他出场即传说。他能抛出犀利的观点,认为老局长傅明的家庭条件在90年代顶多算个“贫下中农”,也能无缝回归传统,套用老家的规矩明确指出凤姑妹妹实际上应该管自己叫“娘舅”,他也关注时事,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入室抢劫”,在那个年代最高量刑至死刑——哪怕他仍然说不出一句完整的普通话,仍然习惯性地将“我们”说成“额们”。

更何况宝财哥还长得像“电影明星谢园”,精瘦、黝黑、休闲西服搭配篮球背心,太容易让人怀疑梁左当年在写这个本子的时候,是不是只记住了“艺术来源于生活”,忘了“艺术高于生活”。
以至于越是时光荏苒,宝财哥就越让人笑不出来。就像“我不下岗谁下岗”愣是披着喜剧的外衣,在1999年除夕夜让无数国企职工在电视机前酸了鼻子,在那个年代进城的人,应该不会觉得宝财哥有多好笑,毕竟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生活糟粕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展示在陌生人面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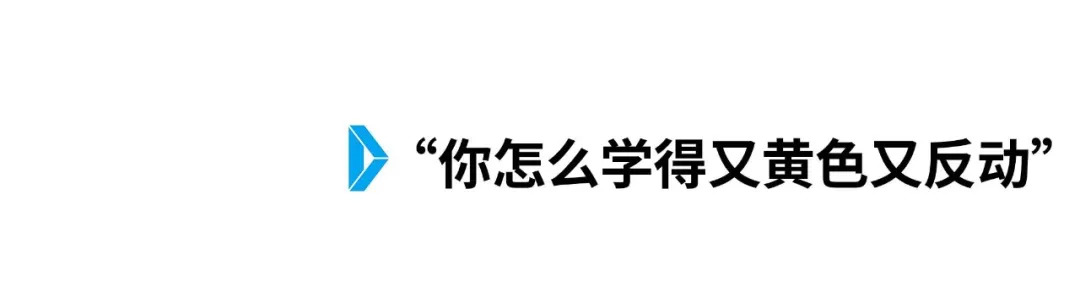
宝财哥的思维模式在现在看来是匪夷所思的。
比如当他拍着胸脯地笃定“凭他和凤姑妹妹的关系”,凤姑妹妹一定会接济他足够的盘缠以撑过难关,导致未婚妻春花疯狂吃醋,说出“舅舅搂着外甥女儿,舒服一会儿是一会儿”以嘲讽的时候,他第一反应并不是“我不是、我没有、别瞎说”这样的否认三连,而是给春花戴了个高帽:
“你怎么进城不到半年,学得又反动又黄色?”

但在90年代初,这恰恰是普通人最正常的反应。或者更准确地说,在当时,“讨论时政要事”是一件非常时髦的事——有些类似于现在的自媒体大V们张口“亚文化”、闭嘴“人间观察”——能够在闲聊的时候砸挂几句当下时事,对方一定会高看你一眼:
“嗬!您可真有想法!”
这个风潮也几乎是当时语言类文学作品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比如同样在《我爱我家》里,亲家母和傅明老人尬聊的首选话题就是:“那柬埔寨要大选了吧,您说咱努克能当选吗?”
一个从小生活在胡同里,连字都认不太清楚、靠唱大鼓为生的老太太,亲切地将国外政要西哈努克亲王称为“咱努克”,太有前两年周杰伦粉丝团突袭微博超话的既视感了。
您老也懂这个?

1991年春晚相声《着急》里的姜昆也深受其害。由于他的街访大妈意外地会去关注“季节变动导致副食品价格涨价”,并乐于将这个信息分享给身边能聊上的每一个人,他早早地选择大量囤货柴米油盐,最后惨遭做空:
自己家里的粮油多到吃不完,一口气撑到了副食品又因为季节变动降价,造福了全体邻居。

《英雄母亲的一天》对这个风潮的表现就更花心思了。侯耀文说自己是个导演,赵丽蓉则听成了“倒爷”。
你可以将这个包袱理解成相声里经典的“聋子打岔”,也就是当下流行的“谐音梗”最具有本土特征的形态。但一个讲故事只知道讲“猪八戒和阎罗王打起来了”、怎么也讲不好“司马光砸缸”的老太太,却知道“倒爷”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魔幻的事。
要知道倒爷可是一门高门槛高风险的职业,非《鬼吹灯》里王胖子那样,心思活泛、消息灵通的年轻人所不能胜任。

所以哪怕外表再邋遢,能脱口而出这样富有鲜明“时政色彩”的判词,当时的观众也肯定会高看宝财哥一眼,并毫不吝惜地送上溢美之词:
这家伙,在老家绝对有一号。
说不定还会被树立成典型。那是从生活方式到经济基础全面转变的特殊历史进程,直到1982年之后农民才能够自由地进城务工、长时间地在城市生活。
在那之前(包括之后的几年里),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仍然是件新鲜事。赖在老傅家的季春生同志,就曾经表示自己在水泥管子里“蜗居”的时候,经常半夜被联防队员查起来,然后就遣返回原籍。如果这个尺度沿用至今,那些吃着挂逼面的三和大神们,大概率无一幸免。
即使走出来,也有着非常直接的政策引导,即所谓的“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傅明老人家里的小保姆小张,就是“有编制有备案”的家庭服务员,通过职业介绍所介绍,在傅明老人的单位做过登记,工资需要实报实销组织审批。
总之别看1982年距离宝财哥来找凤姑妹妹已经过去十年——划时代的变革从来不是“十年”这个时间跨度所能承载的,自然也不能帮助“城乡交流”上升到“频繁”的程度,更不足以让春花从容应对进城半年以来带来的文化冲击。

只是话又说回来,这样的十年时间也无法帮助宝财哥真正地融入“城里”,他可能还记着城里人批判着《甜蜜蜜》是“靡靡之音”,却不知道孩子们已经流行看“麦克老狼”,流行到家长都不管的地步。
中国老百姓享受信息大爆炸的历史并不长,哪怕标准降低到能够随心所欲看电视,都已经是1990年之后的事,以1990年11月2日颁布“有线电视管理暂行条例”为节点。
在这之前天线是比电缆更常见的信号传输方式,当时人们即时有电视也往往只能收到个位数的电视台,不方便到即使是所谓的城里人也普遍需要《电视报》作为必要补充来获得更好的观看体验,广告语“《中国电视报》,生活真需要”可一点都没有夸张。
别看现在不少人心心念念传统媒体时代的辉煌,正儿八经的传统媒体时代的残酷,同样远远被低估的。经济、地域、教育程度这些现在看起来非常形而上的因素,在当时实打实地影响着人们的视野,带来了一条条难以逾越的文化沟壑。
以至于努力大胆如宝财,也只能假装“进城”而已。就像街溜子永远不会把“华子”塞进公文包,公文包上的LOGO永远比材质重要,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也只是能够远远地眺望到时代的背影,何况当时的宝财哥呢。
所以现在想想,梁左没安排他碰见官二代贾志新,大概就是最大的善意。要不按照人物性格,宝财哥早就被有理有据地呛回去了:
“您没看过报纸还是没听过广播?还黄色歌曲靡靡之音?早没人提这茬了。”


不过有件事,宝财哥和贾志新肯定会达成共识:
虽然傅明老人是首都的局级干部,是40多岁大姑娘都愿意倒贴的“高干本人”,按照另一位高干子弟孟朝阳估算“养头大象都富裕”,但总体对比起来也顶多算个“温饱水平”。
贾志新就在和平收留季春生的时候,精准地定义过自己家与北京街溜子互帮互助的性质,“穷帮穷”。宝财哥的评价更不客气。春花儿发出“这家人好有钱咧”的时候,宝财哥一边犀利地指出“我看你是没有见过真正的有钱人”,一边用实例抨击贾府的生活品质,“茶不好,凑合着喝”。
那可是老局长的茶。

当然这其实挺诡异的:宝财哥倒可以理解成在春花儿面前吹牛,以维护自己“一家之主”的尊严,从小胡同里长大、小时候还下乡学农过的贾志新怎么能这么不知足呢?
原因可以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
那年头,人们都向往着南方。
1986年,深圳举办了国内第一届大型健美比赛,中国老百姓第一次见到女性也穿着“大裤衩子”就出来比赛。在当时带来的文化冲击,远不亚于二十年后人们偷偷地在博客里传播木子美的《性爱日记》。

1990年深交所成立,在极短的时间里为中国第一代股民暴发户,也在两年之后用一场上蹿下跳、无法用传统“牛市”、“熊市”还形容的“猴市”,教会了大家什么叫做“资本市场的残酷”——同年TVB神剧《大时代》上映,在一代中国股民强烈的共鸣中成为了“圣经”般的存在。
贾志新不愿意经常和别人谈起他爸爸的局长身份,而是更愿意在谈生意的时候让别人称呼他为“贾经理”,如果接起电话的那一头是生意伙伴,他还会习惯性地切换成广东口音,也不知道跟哪儿学的,大概是电视台制作的《每天学粤语》。
中国的孩子们不再唱“吹起小喇叭,嗒嘀嗒嘀嗒”。相比起她妈妈走穴的时候就能遇到的“阿欢阿巩阿庆”,贾圆圆已经彻底被港台明星征服,会在笔记本上手抄《其实你不懂我的心》,会逃课去参加《霸王别姬》的首映礼,只为一睹张国荣风采——这还没说胜似她“活祖宗”的四大天王呢。

那时候,商家有奖销售会把“香港七日游”设置为一等奖,放在“夏利牌汽车”前面。贾圆圆她妈和平女士,就曾经中过那么一回,然后很快轰动了整个大院,学校、居委会、剧团都拉着她要赞助。
至于原因,生得不太晚的中国人大多都能说上那么两句。改开、特区、南巡、单列计划、市场经济、价格闯关、集体下海,这些富有时代使命感的词语大多都在那时候迎来故事的高潮,或印在教材里,或被写成了歌词,或占用新闻联播至少5分钟的口播。
现在历史书上对那段时期的狂热情绪有个很精确的定语,叫“孔雀东南飞”。人才、资本、资源、注意力都在向东南沿海转移,最终在珠江两岸完成孔雀开屏,带来了灿烂的成果。
也不知道算不算幸运,那个年代,沿海和内地、国外和沿海真的有不容辩驳的“差距”。稳定的“差距”带来的直观结果是:人们一方面会形成“外国的月亮比国内圆”这种不争气的心态,要求国民从教育到两性关系矫枉过正式的进行全方位反思;另一方面,各种论调背后骨子里的“要强”、“追赶”内核,又能巧妙地把这种心态转化为正能量,无比真诚地将“差距”看做是“希望”:
最好的,一定还没来;最神奇的,一定还没看着;最有钱的,一定还有想不到的。
值得一提的是,不知道算不算巧合,“京派文化”的衰落也发生在这个全民等待着南方的捷报频传的过程中,宝财哥三次元的真身谢园就吃了教训。
他和葛优、梁天在1994年成立了一个“北京好来西影视策划公司”——葛优在当时已经是国内顶流,梁天则大胆地中途退出了《我爱我家》的拍摄——结果除了一部让他拿到百花奖的《天生胆小》,其他的浪花基本都没听着响。
这到哪儿说理去?

最后聊聊宝财哥的婚姻观。
首先宝财哥肯定不是渣男。他敢于冲破中国乡间“先成家后立业”的传统观念,带着春花儿一起在城里闯荡,只为了个更好的生活条件——这就比现在大部分凤凰男有志气很多,没钱,谈什么优质基因的传承?
宝财哥肯定也高尚不到哪儿去。当他们的性质已经彻底转变为“入室抢劫”,在严打年代够判得上死刑的时候,他和春花儿就发生了严重的、人生观层面上的分歧——春花儿说“咱们自首,有妹子陪着你,你还怕什么”,宝财哥犹豫了一下还是甩开了她的手“我可不想死”——三观不合,他俩能过到一块儿去么。
淳朴中带着小自私、自私中又备受良心煎熬,二十多年过去了你仍然能够在快手、抖音上主打家庭伦理、农村婚姻的短剧中,看到这个内核——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农民婚姻关系,背后复杂的成因足够聊上好几篇知网论文了。

不过宝财哥让我最在意的台词,其实是另外一句。他在撇弃自己和凤姑妹妹的关系时,曾经进行过一次非常严肃的声明:“额们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这简直太90年代了。
90年代初,严打仍在继续,流氓罪仍然存在并可以最高量刑到死刑,但发展到了第二阶段:随着社会风气、舆论环境、生活方式的不断复杂化,流氓罪开始由于“名义过于宽泛”而开始出现大量“矫枉过正”的现象——和很多人谈恋爱算不算流氓?和同性谈恋爱算不算流氓?在大街上接吻算不算流氓?和身边女性接触过于亲密算不算流氓?
直到现在,网络上还流传着一个“80年代木子美”的传说,据说一名王姓女子因为和多人发生性关系而被判处死刑,并且在临刑前留下了一句旷世名言:
性自由是我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我的这种行为现在也许是超前的,但20年以后人们就不会这样看了。
这句话的源头在哪儿,是否是真的,目前已尚不可靠。我国的公检法机关也确实在1991年开始对“流氓罪”进行联合商议,向寻衅滋事罪、聚众斗殴罪、侮辱妇女罪、聚众斗殴罪等有着更加严格的细分罪行靠拢。
但那些年承认男女关系的存在,的确是一件需要有勇气的事,也是值得上纲上线的事。这种思潮甚至形成了一种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恋爱纠纷解决方案”:
我要向你的领导/单位反映反映,维护男女关系也是全社会的事儿——单位劝完妇联劝、妇联劝完居委会劝、然后就是全家老小齐上阵——现在仍然有迹可循,只不过当时是打电话、写信以及上家门口堵领导,现在是写长微博、公众号,通过热搜来举起舆论公器。

当然这也是宝财哥最幸运的地方。在那个年代,他居然有机会和未婚妻,在婚前这么彻底地交流着自己的婚姻观。又因为不太有文化,歪打正着地规避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骨子里的“两性耻感”。再加上“包工头跑了”,爱管闲事儿的单位也不复存在。
你说,为啥明明细琢磨起来都对不上号,总会觉得自己身边就有这么一号人?历史会记住宝财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