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早期的宗教教育和哲学教育来自于泰戈尔的诗。
1984年,我接触的泰戈尔是郑振铎和冰心翻译的,格言体,译文很优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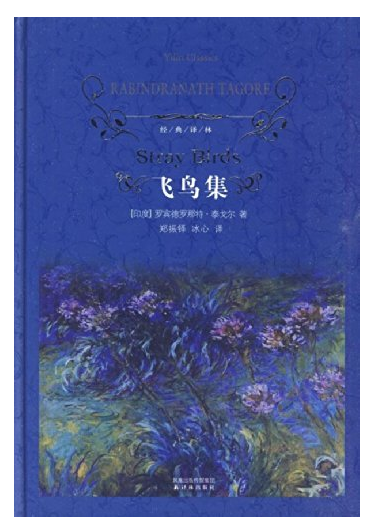
那时,我让别人念,我抄成盲文,因为盲文点是凸出的,所以显得每一页都很厚。《飞鸟集》薄薄的一小本,抄成盲文就是很厚很厚的一大本,成了像圣经一样的巨大经典。 《飞鸟集》,《吉檀迦利》,《渡》;我觉得名字都很美,出一本买一本。我现在还有当年抄的盲文。
在这之前,80年代初,我爱买精选集,像《外国情诗一百首》,《外国名诗500首》,泰戈尔是我第一个系统接纳他的诗人。我印象比较深的,像《飞鸟集》第一句,“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的窗前唱歌,又飞去了。秋天的黄叶,它们没有什么可唱,只叹息一声,飞落在那里。”还有《生如夏花之绚烂》里有一句“有一次,我们梦见大家都是不相识的。我们醒了,却知道我们原是相亲相爱的。” 《新月集》挺美妙,是给小孩写的。还有一本诗集叫《情人的礼物》,有种泛神论。 读《情人的礼物》非常感动。泰戈尔的诗里更多的是印度教、波斯人的大自然的东西,诗里老有虚拟的女子形象,可能是某个神。后来读诗几乎没有那种感动,只有理性。读泰戈尔的诗就像听音乐,有一种骨子里的激动。
泰戈尔对我的诗歌音乐都有启蒙。他的诗里面音乐性很强。
我记得收音机里有文学节目,有时候也会播放他的诗歌朗诵,配上印度的音乐。印度文明本身就很神奇,泰戈尔的诗有种强大的印度文明的气场,异国的远方的气味弥漫在封闭的生活里。泰戈尔的诗里充满到处旅行、漂泊、在路上、山川、河流,少年时代可能就有那种内心的种子,喜欢这样来来去去到处走,心智上也能接受——那时候如果看布罗茨基就接受不了,没有复杂的心智。
泰戈尔挺适合十三四岁左右的少年时期。青春期的情感刚刚发芽,他的诗能把宗教情绪、生理情感和性别意识都融合在一起。泰戈尔的东西很多是泛神论的,有种宗教的情绪。他老提到神,你就会想这个神是个什么神,是个女神呐,还是像耶和华那种爱发脾气的父亲神啊?泰戈尔用诗歌的方式把宗教情绪消解了、融合了给我。
那时候我用盲文写日记。80年代写诗喜欢非常励志、押韵的那种。看泰戈尔以后有所改观,模拟他的语气写一些东西。比如出现一个虚拟的她,发现一个哲理……多年后看这些东西挺可笑的。
2
我13岁的时候也看《圣经》。那时候有个香港的圣经电台,是短波,中波也能搜到。我爱听那电台,因为里面的歌曲也很好,偶尔会有吉他弹唱。我用盲文给人家写信说要一本《圣经》,后来人家给我回信,被学校扣住了,成为一个事件。因为信件要通过门房老师,他看见了,啊了不得,像出现敌人一样。我是团员,团委开会,老师批判我,因为香港那时候还是境外。那封信最后也没让我看到。
那时候我希望有宗教上的启示,其实也不在乎是《圣经》还是佛经,但都很难有机会。
盲文版的《圣经》,三十多本,摞起来有一米六,从地面到我脖子那么高。

盲文版圣经,CFP
《圣经》对我影响很大,不是从基督教,而是从文学这个维度。
《圣经》总也看不完,对我来说它是个无限大的世界,什么时候都可以拿起来看一看。它不单纯是一本书,而像一个很大的世界,有很多入口。刚开始我喜欢翻《圣经》找故事看,潜移默化也会受语言的影响。圣经的语言相对来说比较庄严,单一,甚至有点单调。少年时期喜欢花哨的语言,比喻多的,有各种象征,修辞复杂的。圣经比较直接。
我后来读《神曲》,读舍斯托夫的书,读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战栗》……会在很多书里重新找到一个小门进入《圣经》,然后出来。这本书像枝叶繁茂、纵横交错的大榕树,枝杈多,又生小树,一棵一棵蔓延开。
今年去耶路撒冷,再一次感觉到《圣经》,是真正从一个城市进入《圣经》。在《最后的晚餐》那个地方,过去在《圣经》里读到的耶稣受难的圣母教堂,排着队,大家趴在地上摸耶稣降生的马槽底下的石头,还真是感觉不一样,它是固体的、石头版的《圣经》。当然我也不是个基督徒,有一阵快是基督徒了,后来看佛经又转了个弯。
基督教里有种情绪,很悲悯,后来我听了很多好的音乐都跟《圣经》有关。有段时间我很喜欢莫扎特的《安魂曲》,就是那种感觉,从《圣经》里派生出的向死而生。
3
14岁左右,我开始看《红楼梦》。盲文是删节本的,云雨之事都删掉了,还是茅盾删的,那时候特别恨矛盾,太无聊了,这事儿干的,删这干嘛呢?不是盲文的全本有,但我不好意思找人念,十三四岁找人念个《红楼梦》?也不知道哪儿会出一个让人心跳的东西,所以只能读删节本。有饥渴感也挺好,会想想,那段删掉的是什么东西呢?我每天彻夜读《红楼梦》,盲文是摸着读的不需要开灯,躺在床上抱着一大本书从晚上能摸到早上。
十四岁左右,《红楼梦》那种古汉语也是能读懂的。知道古汉语可以讲故事,就对古汉语产生了亲切感。借着《红楼梦》,会看很多其他的书。有一段香菱跟着林黛玉学诗,林黛玉举很多例子,王维的诗,陆游的诗怎么怎么好,写到“良辰美景奈何天”是艳词,挺好奇《西厢记》有多艳,就会找来看看。《红楼梦》是古代文明的一扇容易进入的门吧。
16岁的时候,我特别爱买世界名著。到书店的时候,人家说拜伦的《唐璜》好,我就买。两大本,诗歌体,译者是穆旦,才六块多钱。那时我还不知道穆旦,就觉得哇,译得好。听说是查良铮(穆旦原名)文革时候一边刷厕所一边翻译的,真是最好的翻译诗。好的段落我都抄下来,现在被我像文物一样放在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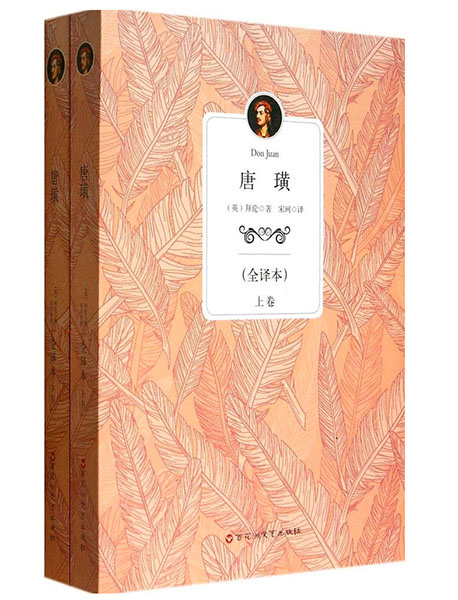
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拜伦不像泰戈尔,他是讽刺的、嘲讽的、嬉笑怒骂的。我那时看不懂当中的典故和西方知识,比如说,唐璜跑到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被抓到皇宫里,那段写苏丹的皇宫写得非常好。但我不知道伊斯坦布尔在哪儿。去年我去伊斯坦布尔,走到一间一间的嫔妃宫女的房子,想起唐璜怎么被贩卖到皇宫里,辉煌的皇宫,很香艳很浓郁的感觉。好多书回忆起来再次相遇的时候,就把你的整个时间连成一片了。
我可能十四五岁就打开了心智,到了大学就没啥意思了。
80年代,我根本没想弹琴唱歌,音乐不在意识范围内,都是写作读书。80年代文学更受重视,有影响,周围人都这样,搞音乐干嘛啊?不务正业嘛。90年代,文学退潮了。人们开始唱卡拉OK,开始跳交谊舞,舞厅特别火。我那时候忙着找女朋友,生活寂寞才读点书。无聊的时候读萨特、加缪,也没读太懂,寥寥吧。我转行做音乐了,生活重心转移了。人可能还是脱离不了整个时代的氛围,尤其是年轻的时候。
4
1994年,在沈阳一个体育馆,门票50块钱,我看了一场崔健的演出。那是我看的第一场摇滚乐现场。
崔健音乐中的强悍和力量冲击着我,《一块红布》啊,《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我都买磁带回去听。我感受到力量,来自于中国的力量。我还扒过崔健的《出走》,吉他和声很好,根音下行,吉他递进式的很好听。《一块红布》在街边我也经常唱。 当时我也听Nirvana,但是冲击没有那么大,毕竟我不了解他唱什么。崔健的歌词很中国化,我看他的现场,底下人很激动,台上人也很激动,我那时候理解,可能这就是摇滚乐。摇滚乐不能离开现场,不可能光从磁带或者CD上,现场是最直接地传达摇滚乐。崔健的舞台到现在来说不能说最好,也是最好的之一,不出前三。他的稳定性最好,这么多年来,灯光、调音,整个乐队艾迪 ,刘元,跟他好几十年,不解散不换乐手,所以他的舞台感是最好的。我后来经常在音乐节上看他的现场,他的才华是均衡的整体的,不是那种偏激性的天才。他投入很多,音乐作品好,唱功也好,乐手水平也高,整体舞台传递得很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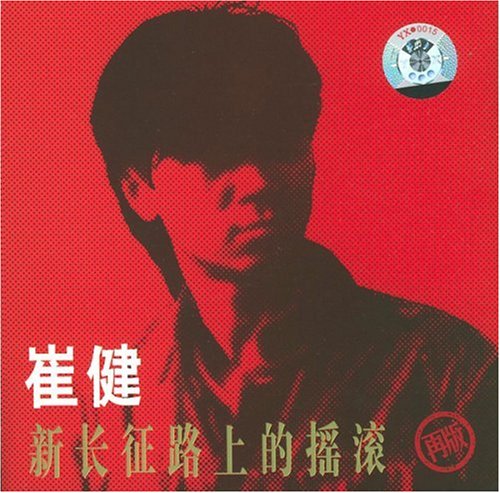
但崔健倒不是我去北京的原因,我还是为了谋生,为了生活。我去北京卖唱是因为没有别的生存能力,生活逼着我进入音乐,并不是某个音乐作品引导我。
要卖唱,就得学习唱歌,学习唱歌就要扒带子。扒带子最早是从齐秦那些歌开始,《外面的世界》、《昨天的太阳》,《大约在冬季》……吉他和声走向很好,从高向低,根音上行下行, 那时候大陆歌曲的和声编得都很简单,齐秦就很洒脱,有转调的,分解和弦,吉他因素特别多,很有启蒙性——当然卖唱也用得着。
到了北京,很多人卖打口带,接触到打口带了,我开始扒国外的。扒起来挺麻烦,得听好多天。但要弹好了就觉得,这个编得真好听啊,和声转得跟我们那个1451,5323,1323完全不一样啊,多扒点歌就觉得整个西方摇滚乐的和声编得好,才有创作欲望进入到音乐里去。最早的是Beatles。Beatles的音乐吉他和声又简单又好听,我觉得beatles是个永远能创造出那么多好旋律的乐队。我在Beatles那里学到了西方现代音乐的旋律和声音的默契配合。列侬有首歌叫《love》,也是我最早扒的,歌词也简单:“love is real ,real is love” ,现在有时候还唱呢。那时候我英语就初二的水平,这个歌词好,太好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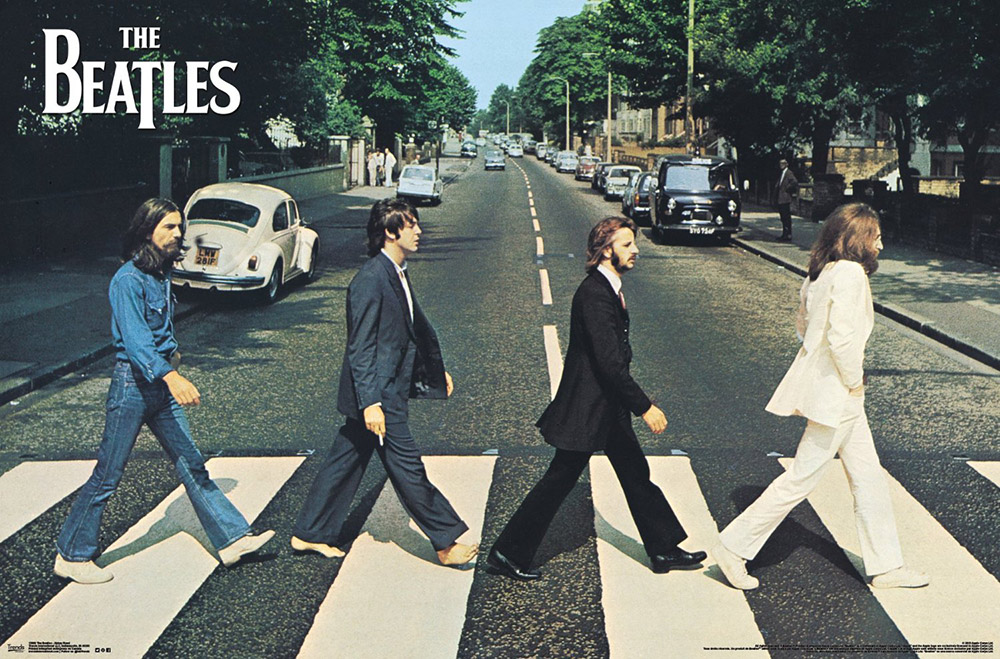
有一阵我喜欢听“感恩之死”,Grateful Dead,一个很迷幻的乐队。那是1995-1996年左右,我在北京。那会儿喜欢迷幻这词儿。相比Pinkfloyd,我更喜欢感恩之死。他们的迷幻不是通过效果器、灯光,更多是通过原声乐器制造出迷幻。就是吉他加一点失真或者合唱、效果器,然后贝斯、鼓。平克很多歌是通过音色、效果器、合成器制造出一种迷幻,感恩之死相对来说是朴素的迷幻主义,有限制有局限的。他们的专辑特别多,估计加现场一百多张不止,有一阵我买了很多他们的打口带。

Grateful Dead 2015年在芝加哥的演出,CFP
但这些不像《圣经》、泰戈尔对我的影响那么大,因为自己已经写歌,走上了这条道路。在这条路上遇到了一些旅行的同伴。后来我遇见了小河,他给我矫正了一些方向。比如怎么在舞台上唱歌,弹吉他,怎么能够写歌写得更私人化,不是为了集体,为了抒情和意义写歌,而是更私人化,写出内心的好和不好。
5
前两天我还在看泰戈尔英汉双语的《飞鸟集》。有时太累了不愿意看新书,就看过去的。隔了好多年又重逢了,你会想起它当年对你的影响和启示。
现在,我觉得都是延续,没有什么急转弯的影响。我谈到的,不能说是国外,应该说是世界性的,因为是陌生的,那些才有矫正意义。
三十岁以后,我开始听德彪西,巴赫和莫扎特。我的手机里下载了一百多首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还有平均律。我还喜欢弦乐四重奏,无论是莫扎特的还是柴可夫斯基的都喜欢。我觉得形式非常完美,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一个非常完美的音乐结构。很早期我也听古典,但听不懂,比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欢乐颂》,是叶公好龙,命运交响曲就听第一乐章,欢乐颂前头都听不懂,到最后才出现大合唱,古典音乐需要心智,也需要好的音响吧。拿个收音机听交响乐怎么听也没有那种宏大立体声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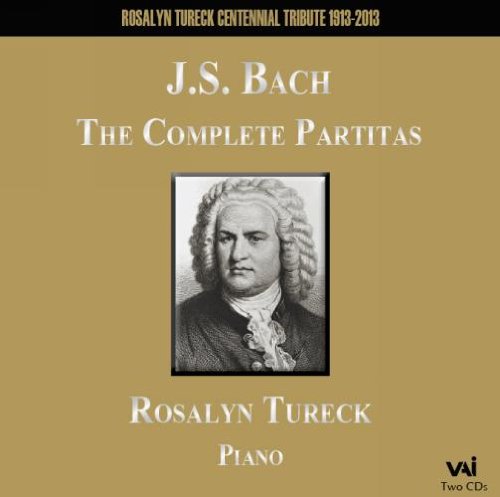
图雷克演奏的巴赫
古典乐给我带来了宁静,更多的是听音乐内在的情绪,比如莫扎特的音乐,特别欢乐,像孩子气的不断在变化,喜悦,听了心里太欢喜了,和巴赫是两个极端,巴赫是缓慢宁静的音乐。现在可能更多的是从心智上介入这些音乐,让自己安静,喜悦也是让自己心里宁静一些。
最近我在读《飘》。昨天看到斯佳丽战争中逃到她的家乡,白手建设她的家,挺激励人的,有力量,有美国的冒险精神,也有自私的光辉。的确是本好看的书。现在我的阅读就这样,想去哪儿先看看那一带的书,加深对那边的了解。我今天要从大理飞北京,明天飞美国。去看看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
——————
题图摄影:中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