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看来,椰壳碗内的青蛙“心胸狭隘、迂腐守旧、深居简出和自我满足”,而他自己想要的则是椰壳碗外没有规训边界、充满好奇和冒险的人生。本文探寻安德森的情感和学术世界,在他糅合着爱与愤怒的丰沛情感中发现了一个活得真挚而元气淋漓的人,从而解释了与他这个情感世界如毛细血管一样连接着的学术世界的问题意识从何而来,走向何处。
《安德森的两个世界》
文 | 张帆(《读书》2020年9月新刊)
《椰壳碗外的人生》是政治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学术自传。该书展示了一个全面立体的学者形象:一个四海为家、情深义重的漫游者,一个疾恶如仇、飞蛾扑火般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超越边界、追求卓越的思想者,和一个老派保守、内心光明的长者。在书中谈论不同对象时,他的用语化为两极:一类是表现亲密关系的,如:家、爱、情感依恋。另一类是表现对立关系的,如:仇恨、愤怒、恼火、煎熬、讽刺、藩篱、无趣。两类泾渭分明的词语体系象征了安德森学术人生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情感世界,这里有他坚守的学术传统,有他在漫游途中为自己营造的家,也有他的家人、恋人和朋友。他在情感世界里感到温暖、自在。另一个是学术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安德森是对手、异类和被驱逐者。他随时严阵以待,准备揭下对手的假面,还原世界的本来面目,挣脱一个个束缚人的思想,然后悄然离去。
安德森的学术人生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其两个世界之间的密切联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情感依附”。跟随安德森营造两个世界的历程,追寻他漫游其间的足迹和情感变化,可以窥见情感与学术之间,以及学者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
01

安德森认识世界的方式从一出生就与常人不同。世界地理是他“移动的青春”里一个接一个的驿站。母亲曾告诉安德森,他会说的第一个词是越南语,而不是英语。因为他一九三六年在昆明出生后,照顾他的保姆是一位逃婚到中国的越南年轻女佣。五岁时他全家取道美国回爱尔兰,不意在旧金山和科罗拉多上了三年小学,一九四五年回到爱尔兰。不久,又去英国读寄宿学校和伊顿公学。后来,安德森又到美国求学和工作,到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做田野调查。安德森一生漂泊,“在任何地方都无法久居到安定下来”。他的词典里没有“故乡”这个词。《想象的共同体》中提道:新贵族们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行政单元想象成祖国,如同宗教朝圣者一般行进在如螺旋上升的任职通道上。“官员最不想要的就是返乡,因为他并未拥有一个具有内在价值的故乡。”这句话几乎是安德森的自我写照,他也没有“具有内在价值的故乡”。然而,孤独的漫游者终究要回到故乡。安德森一生都在更广大的世界和更悠久的传统中寻找属于他的家,一步一步地在漫游的旅程中营造了他的家。他的故乡像一座城堡,里面住着他的家人、恋人和朋友,传承着让他长久依恋的古典教育和老派的生活方式。
安德森与印度尼西亚的“恋情”建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在印尼进行田野工作期间,“印度尼西亚是我的初恋。印尼语是我的第二语言。有时候,我还会陷入印度尼西亚语的梦境”。梦中的印尼语正是安德森爱上印尼的原因之一。在移动的青春里,“我曾因我的英国口音被美国人嘲笑,在爱尔兰曾因我的美国口音被人嘲笑,在英格兰曾因我的爱尔兰口音被人嘲笑”。幼年因为语言而被边缘化的记忆让他“后来容易通过语言喜欢上印尼、暹罗和菲律宾”。
语言之于安德森,与其说是交流的工具,毋宁说是一种情感方式。学习语言就意味着学习新的情感方式。“学习一门语言是学习与我们不同语言的民族的思维和感觉方式,也是学习构成他们的思想和情感的历史和文化基础,以此学习与他们感同身受。”这种体悟萌发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和家庭教育。“我是被爱尔兰父亲、英格兰母亲和越南保姆养育长大的。法语是一种秘密的家庭语言。”母亲为他聘请的拉丁语家庭教师韦伯斯特夫人“让我爱上了拉丁语,让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我有语言天赋”。
在伊顿公学读书期间,安德森接受的是古典学教育。“伊顿的课程非常守旧。核心元素是语言——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以及后来冷战期间的一点俄语。”伊顿的学生们必须接受严肃的写作训练,“用拉丁语创作诗歌,将英语诗歌翻译成拉丁语。用不同的语言熟记并公开朗诵很多诗歌”。少年时的语言和文学训练,成为安德森成年之后寻找故乡的精神密码。“我背诵我喜欢的诗歌,并且经常默诵它们。以这种方式背诵,诗歌深深地驻扎在我的意识之中,与其说是意义,毋宁说是声音、抑扬顿挫、韵律。”二○○七年,退休之后的安德森在圣彼得堡的一次培训班上背诵了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出人意料地,学生们热烈响应,与他一起背诵起来。结束时,他乡遇知音的安德森已然“泪眼蒙眬”。

苏哈托上台之后,语言在安德森的写作中还扮演了斗争武器的角色。安德森向两位旅居柏林的印尼作家学习冷嘲热讽的混合语言风格。这二人写作了很多关于苏哈托集团丑闻的讽刺文章,“文章混合了标准印尼语、雅加达俚语、爪哇方言,利用爪哇皮影戏故事、中印功夫漫画、粪便学和无所顾忌的荤笑话,让他的朋友们笑掉了大牙,让敌人愤怒得发抖却又无能为力”。这也正是安德森的风格。“关于如何用印尼文写出有魅力的文章,我从他们二位那里学到了很多。我们一致同意,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我们将用性术语记述关于政治的一切,用政治术语记述关于性的一切。”成果之一是安德森短暂担任过印尼一家周刊的讽刺专栏作家,直到刊物被军方取缔。
除了温暖和依恋,安德森也常常是愤怒的。愤怒的情感总是与其政治立场的转变相伴随,这些愤怒的种子都融入了他后来的学术研究中,生根发芽。
一九五六年,安德森在剑桥大学校园见到印度和锡兰学生因为举行演说,抗议英法入侵苏伊士运河而遭到校园恶霸攻击。“我未加思索便试图介入去帮助他们,不料我的眼镜却被人从脸上抓了下来,打碎在烂泥之中。我一生中从未如此生气过。生平第一次遭遇了英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还是在剑桥,安德森经常光顾一家艺术电影院。那时,每场放映结束后,观众都必须立正站好,伴随着国歌观看幼年伊丽莎白女王骑在马背上的图像。叛逆的安德森不堪忍受这种煎熬,“在因为《东京物语》泪眼婆娑或者因为《战舰波将金号》热血沸腾的时候,去忍受这种专制的拥君废话就是折磨”。于是,每次国歌声一响,他就往出口跑,因此而被盛怒的爱国者们殴打也在所不惜。“由此,我成为一名幼稚但坚定的共和主义者。”

在印尼也是如此。“在那里,我的情感和政治倾向首次在我的工作中发挥了作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四年,安德森在印尼做田野调查,“碰到恃强凌弱的美国官员时感到很恼火”,以至于当苏加诺发出反美吼声“去你的援助”时,“我内心欢呼雀跃”。那一刻,出生在中国、在美国和英国受教育的爱尔兰人安德森,发现自己成了某种“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这一跨度之大令人瞠目结舌,直到多年以后,他的立场才发生改变。
02
一九九八年,六十二岁的安德森获得美国亚洲研究会颁发的“卓越终身成就奖”。他在致辞中提出了关于情感世界与学术世界关系的“情感依附”理论:“把区域研究专家与其他学科的学者区别开来的是我们对自身所研究的地方和人民的情感依附。”说完他把两个十多岁的印度尼西亚养子本尼和尤迪推到讲台上,站在他的身边,以表明他的意思。观众掌声雷动。那一刻,“我简直幸福得想哭”,安德森写道。
情感依附理论的核心是一个学者深爱着他研究的地方和人民。情感是否真诚取决于他的情感世界和学术世界的关系,取决于他是否把情感融入了他的学术实践之中。实证主义、逻辑自洽、价值中立、符合规范是学术本身的规则,但这远不是学术活动的全貌。在安德森这里,其学术旨趣和治学方式都与他的情感世界息息相关。进一步,他的情感世界形塑了他与对手打交道的方式,不管是陷入后殖民主义的扭曲关系中时,还是面临独裁政权的驱逐而陷入人身危险时,他的情感世界都一直陪伴着他在学术世界里征战四方。
安德森说:“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时光以一种直接的、感性的方式把我与民众联系了起来。”一九六一年,安德森来到雅加达开始两年四个月的田野工作。虽然爱尔兰人的身份帮助安德森顺利进入了田野,但是并没有完全消解后殖民时代权力关系的扭曲。在田野工作中,“我发现自己频频被称作‘老爷’—一个荷兰殖民者曾坚持要求的称呼”。苦思多日,他告诉朋友们:“我和看起来像我的人应当被称作‘白化病的’(bulai或bulé),而不是白色的。”这个词原本是用来表示水牛、奶牛和大象等动物粉灰色肤色的。“渐渐地,它传到了报纸和杂志上,成为印度尼西亚日常用语的一部分。”后来竟然有白人同事因为这个词向安德森抱怨印度尼西亚的种族主义,安德森听完都快乐疯了。安德森用一个单词跨越了克利福德·格尔茨所谓的美国学者与印尼人之间的“道德与政治的鸿沟”。这再次证明,语言是他的情感方式,他由此入手“与民众联系起来”,同时送别殖民时代的遗迹。

一九七二年,安德森写完了他的首部比较研究的作品《爪哇文化中的权力观念》。之后,他仍想知道,“即使在自认为完全现代的文化里,是否存在关于权力的旧式思考的土壤”,多年之后,当得知美国总统里根在他妻子致电算命先生前从不做重要决定时,安德森异常兴奋。他的兴奋之情源于对美国民族主义的神话“美国例外论”的一贯反感。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把早期美国与西班牙美洲的混杂的新式民族主义进行比较,并把美国的案例放在这一章的最后而不是开头。对此,时年七十三岁的安德森在书中顽皮地说:“我喜欢期待这样的比较所激起的愤怒。”
《想象的共同体》一书最典型地体现了安德森的两个世界的交融。情感世界的诸元素都能够在其学术著作中找到各自的身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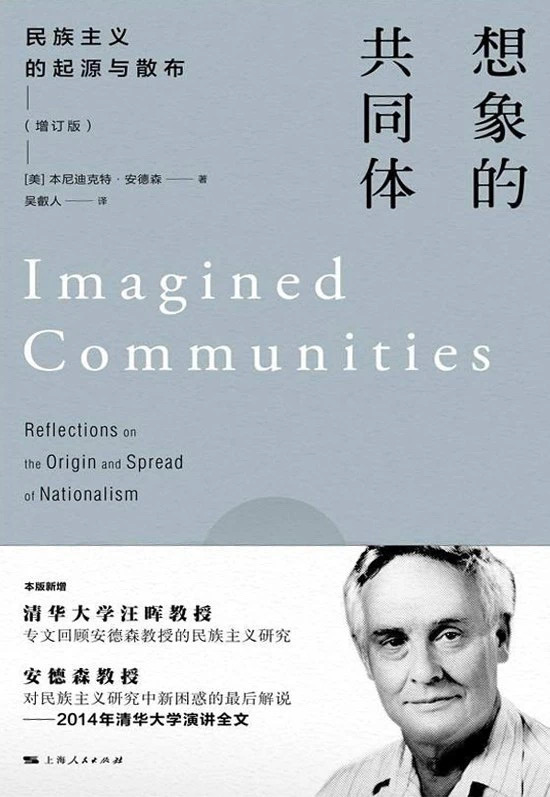
安德森对自己比较视野的演化路径有着非常自觉的认识。少年时期,“从地理上讲,我是在为一种四海为家的、比较性的人生观做准备”。后来,在“同类中最好的”康奈尔大学东南亚专业学习,那里的图书资源、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和学术训练让比较思维深入骨髓,与东南亚同学的交往不断地让“偏见接受考验”。一九六三年现场聆听印度尼西亚国父苏加诺的演讲也是他比较视野的震撼式启蒙。苏加诺称希特勒是“绝顶聪明”的民族主义者,这让安德森“晕头转向”,“它让我从此不再可能把欧洲视为理所当然”。这些都在以聚焦相似性为比较策略的《想象的共同体》中得到了体现。
安德森也谈到了一九七二年之后到写作《想象的共同体》之前的十年间自己兴趣和观点的变化,并列举了引起这些变化的三大影响。首先,通过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和《新左翼评论》,安德森才“变得更加国际化,不再只是一个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其次,东南亚专业的学生习惯于进行“之前未曾想象过的崭新比较”,这让他领悟到,真正有益的比较是那些出人意料的比较。第三个影响来自密友、人类学家詹姆斯·西格尔,因为他的提醒,“我开始思考如何把我之前所接受的古典、西欧以及印度尼西亚文学训练运用于政治研究中想象与现实之关系的新式分析”。自此,语言和文学对于安德森来说,从一种情感方式延伸为学术研究的方法,《想象的共同体》中的很多引文和典故都出自英国的诗歌、随笔、历史和传说,即为明证。少年时的语言和文学训练,不仅是安德森寻找故乡的精神密码,也逐渐成为他的治学方式。所有这些影响都清晰地显示出,安德森在不断地超越自我,不论在政治立场方面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比较和超越是相互推进的。比较的要点之一是翻越语言之墙、超越“天经地义”的局限。“你无法再认为你的阶级立场、你的教育甚至你的性别是理所当然。”
最终,对情感的敏感让他找到了解答民族主义谜题的突破口,这是安德森情感世界与学术世界关系的最佳例证。之前学界将民族主义单纯地作为一个观念系统或者一种意识形态来看待。安德森对此表示质疑:这种看待民族主义的方式无法解释其巨大的情感力量,以及它让人心甘情愿为它牺牲的能力。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说:“如果我们把民族主义当作像亲属关系或宗教这类的概念来处理,而不要把它理解为像‘自由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事情应该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此外,他还一偿夙愿,用学术的方式吐露了在剑桥大学时遭遇“英国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愤怒:“若干年之后,当我通过写作《想象的共同体》来为英国读者讲述民族主义的时候,我以挖苦、讽刺、含沙射影的方式道出了依然历历在目的一些愤怒。”
安德森的比较研究之路是一条超越边界、超越自我的路。他在这条路上反抗、揭穿那些荒唐、反智、损害创造性思考的东西,如东方主义、文化霸权、美国例外论、欧洲中心主义、官方民族主义等,斗志昂扬,不知疲倦。凡此种种,都仰赖于他的情感世界为其学术世界提供的问题意识、研究视角和论辩对手。
一九六五年印尼总统府卫队发动军事政变未遂之后,大屠杀爆发。逃离是一般学者面临危险环境时的正常反应,可安德森并不这么认为。平定了叛乱的苏哈托宣布杀戮应该由共产党人负责。然而安德森和同事经过研究,撰文主张“未遂政变”的原因可以追溯至印度尼西亚军方的内部冲突,而不是如苏哈托及其支持者坚持的那样,是共产党。两个月后,文章“泄露了出去,让苏哈托的人和美国国务院怒不可遏”。安德森因此被禁止入境,直到苏哈托独裁政权倒台他才重返故园。为了他的“初恋”,安德森超越了恐惧,在一般学者唯恐避之不及的历史境遇中展露了飞蛾扑火般的性格。此后,安德森又两次重操旧业,为泰国和东帝汶发言。一九七六年,为了抗议泰国政府对进步组织和左翼政治家的暗杀,安德森为写给《纽约时报》的抗议信征集签名,绝大多数泰国研究专家都拒绝签名。“我敢肯定大多数专家都对谋杀感到震惊,但他们担心倘若自己开口,就无法再获准回到他们所热爱的暹罗。”不出数年,苏哈托吞并东帝汶,“我非常‘幸运’早已被禁止进入印度尼西亚,因此对我而言,为东帝汶人写作和游说并不困难”。情感世界帮助他在学术世界中做出了选择。从前的怒目少年至此已经蜕变成了无所畏惧、肩负道德勇气的学者。在危机四伏的国际政治情境中,安德森选择了讲出事实,用行动抗议暴政。
03
安德森的学术旨趣是从人生经验中自然生长出来的,一生都在迎着真问题砥砺前行。他的两个世界相互交融,彼此成就。安德森在两个世界中都找到了内心的平静。而在现代社会,学者身上的两个世界常常是断裂而不是相互融合的。这也就能够说明他对一些事情的批评。安德森非常警惕“民族主义和全球化限制我们的观点和把问题简单化的倾向”。他反对图书馆把一切都数字化,也反对研究生培养逐渐“职业化”,认为“这些学生是在被训练,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被教育,目的是让他们在‘学术工作市场’具有竞争力”。学术不是谋生之道和进身之阶。安德森说:“怀疑的、自我批评的立场正是学者们今天最需要培养的。鄙视政治家、官僚、公司经理、记者和大众媒体名人是很容易的,但要在思想上远离我们根植于其间、视为当然的学术结构却远没有那么容易。”要远离一个结构,就要重建一个结构。对安德森而言,让人得以“保持距离观察它们,而不是被它们形塑”的新的学术结构,就是像毛细血管一样连接在一起的两个世界。
本书的英文书名是A Life Beyond Boundaries,可译为“超越边界的人生”。贯穿情感世界和学术世界的正是安德森对众多边界的超越。这一连串超越可分为三类:首先是被动的超越,包括语言、故乡,也包括田野地点从印尼转到泰国和菲律宾;其次是比较方法的超越,如对学科藩篱、民族主义和各路中心主义的超越;第三,以学术担当和道德勇气对真实世界中霸权和危险的超越。究其根本,安德森对待情感与学术的方式,是他对自我最深刻的发现,也是对数字时代学术风格的超越。
安德森不断提醒我们,被民族主义和世界政治所裹挟的,不是戏剧,而是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人生。真实世界是有情感的,研究者与真实世界之间的情感关系也同样真实。情感世界和学术世界的关系驱动着学者气质的形成,带领他认识不同的历史、文化与社会,使之理性而温暖、专精而勇敢、智慧而有趣。安德森把他的学术生命向两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敞开,一边迷恋,一边奋战,直至最后一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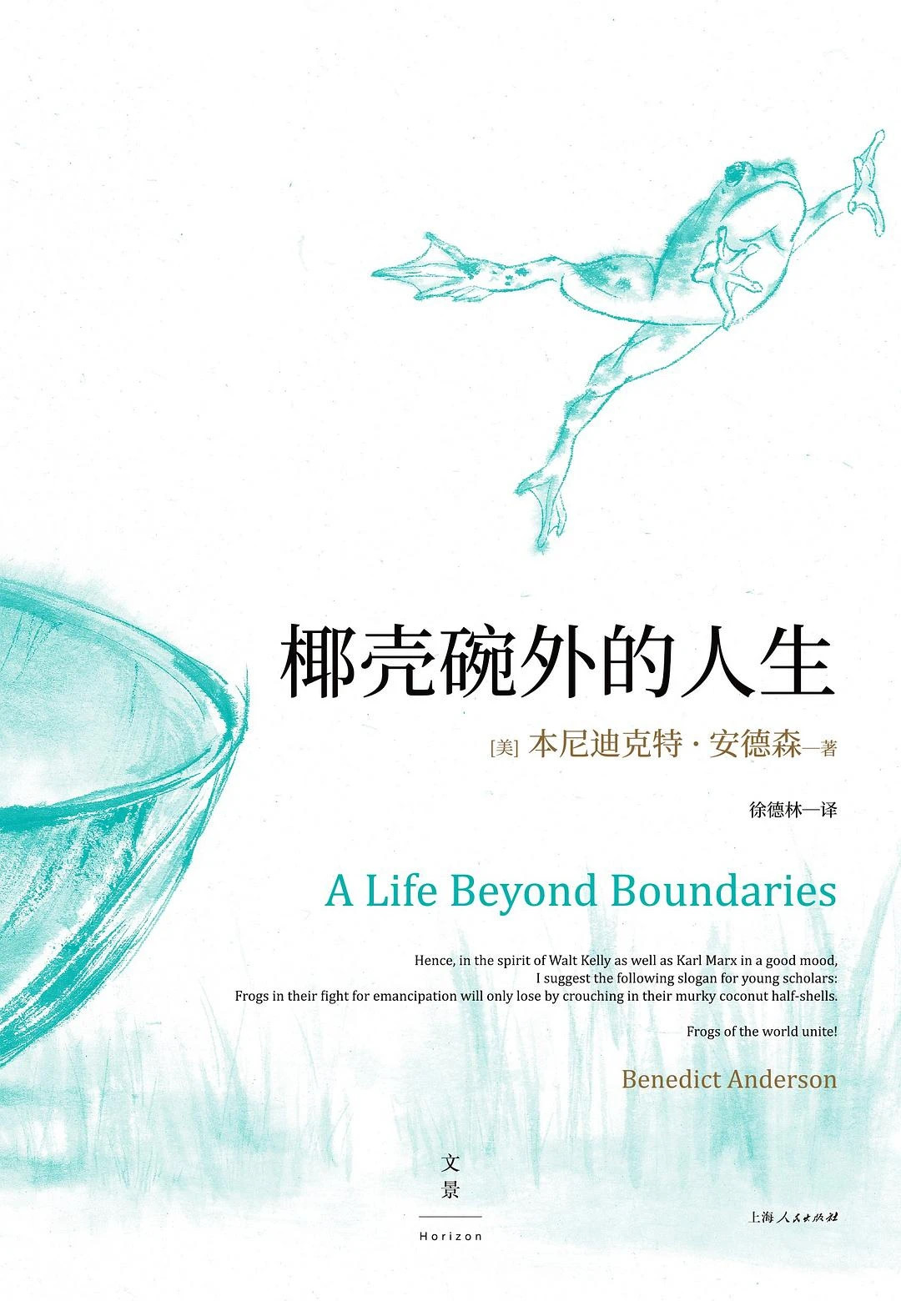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