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在日前于南京举办的非虚构文学工作坊中,我们听到了关于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种种回音,也观察到了一个奇异的现象:以书写纪实中国系列著名的作家何伟并不在场,他的名字却被频繁提及。人们将何伟的《江城》《寻路中国》与其他中国题材的非虚构写作进行比较,也会以何伟的视角出发,重新看待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发展。然而,他的写作本身并未得到很好的分析,如果说其写作给予了中国非虚构写作以启示,那么这些启示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如果说他更新了人们看待中国的方式,又具体是怎样的更新呢?
一、外来者与体制内
何伟作为外来者当然有许多不便,就像他在接受跳岛FM采访时所说的,他承认自己作为记者很多时候置身事外,想要建立起更紧密的关系,就必须让自己进入单位或所谓“体制内”——最初来到中国时,这个“单位”是涪陵师专,现在变成了四川大学。
何伟对单位的体认是层次丰富的,在他看来,单位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决定着人们谋生方式、升迁道路、社会保险、政治面貌,也规范着人们的身份认同甚至婚恋预期。二十多年后,何伟再次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开设写作课,疫情期间他同样需要参与微信群体温接龙,这也是单位关系的例证之一。
单位内外的对比在《江城》里尤为明显,《江城》前半部分主要围绕师专和英文系展开——他所接触到的人,系领导、教师和学生都是隶属于单位的;后半部分何伟进入涪陵,与单位之外的人打交道,在公园、茶馆、面馆间游荡,认识了自由摄影师、面馆老板、面馆里的顾客(包括中巴司机、小商小贩等)等等——令人意外的是,他反而和这些“社会上的人”建立起了更加亲密深厚的关系。何伟认识到,这些社会上的人需要用自己的头脑、运气加努力挣钱,同时也可以有相对“更自由”的发展,因为“没人告诉他要上几个小时的班,面馆应该卖些什么”,不管是老板还是顾客,他们为的只是过上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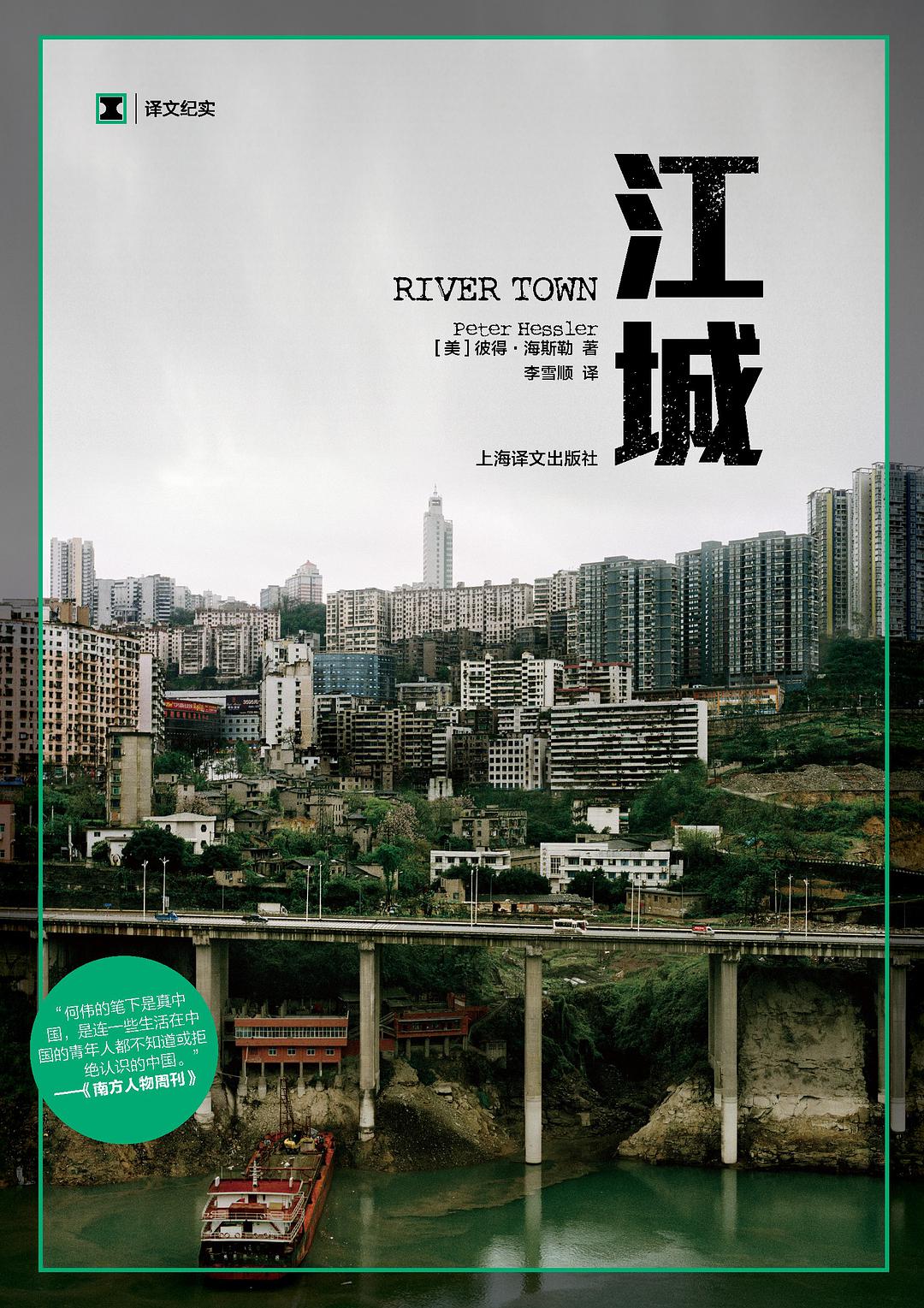
[美]彼得·海斯勒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
至于何伟本人,两年里在师专的体系中工作,虽然孤立和“监督”始终存在,但他也逐渐打开了一些局面——他曾参加学校和系里的酒局,代表师专在长跑运动会赢得荣誉,这帮助他更好地理解了单位的运转规则:借着在酒局里和同事拼酒,他弄明白了系里的酒量排行榜,也因为酒量大过旁人而获得了尊重。在运动会结束后,他赢得了印有“涪陵”字样的运动装奖励,上了本地电视新闻,不料却刺激了本地人的爱国主义情绪。
随着对语言和文化的日渐熟悉,他对单位中的人际交往规则也更加了解,他明白“好干部”和“坏干部”的区分(坏干部通常作为拒绝申请的理由,是过错推诿的对象),可以熟练巧妙地绕过限制、避免麻烦(“到那个学期,我们越来越难以忍受那些没头没闹的政治限制,一般而言,我都尽量避免跟干部打交道,幸运的是,这不难做到。若非万不得已,我肯定不去外办。我也尽可能少跟管理人员说话。”)作为教师,他也成为了师专的一部分——当他身处师专之外,在乌江边的农家看到写作业的孩子时,他想到的是,自己已经成为了当地教育体系的一分子,而这是有价值的:
“我教的不仅仅是文学课,其中还有一个毫无争议的事实,在几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在这里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些孩子们的教育体系——当中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标语口号不会永远永远持续,但那些受过教育的孩子们却会从中持续受益……”
因为“外国人面孔+男性”的身份,何伟能够接触和采访到的人群,与他的妻子、同样从事非虚构写作的张彤禾是不同的。同样以中国工厂为题材,《寻路中国》与《打工女孩》两部作品清晰地显示出了这种区别:张彤禾可以作为女工的朋友回乡探亲,村民家人也会以对待普通来客的方式对待她,比如给她一桶洗脚水招呼她洗脚;而何伟接触的人群更多是官员和厂长。
一方面,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何伟得以“高屋建瓴”地领略某个地区整体的发展,因为他可以进入经济开发区官员的办公室,与主任交谈,了解该地产业构成、人口增长、总用电量等等;在写作过程中,他多次援引官员告诉他的数据,比如工业用电量占到了丽水市总用电量的百分之七十——虽然他也会怀疑这些数字是否真实: “对于数字的使用,自有他们的一种套路——极其漫不经心之间,会背出令人咂舌的各种数字来。”另一方面,何伟也通过这种层面的接触里看到了工厂厂长与官员之间由互惠互利构成的“关系”(“关系”和“单位”一样,是何伟重点对待的汉语词汇,关系包括送礼物和回馈、打招呼和应许)。这种“关系”是有逻辑的,而这种逻辑是如此地容易理解:官员得到了礼物,工厂就能够得到优惠待遇。
当然,在《寻路中国》里,何伟的工厂故事也写到了普通工人。那位富有计谋又脾气泼辣的陶姓女孩令人印象深刻;以这个人物入手,何伟也写到了她的父亲和姐姐,他们一家来自安徽太和,家中依靠玉米小麦种植生活,但也就到此为止了——虽然他已经意识到,丽水的女性代表着经济开发区的新阶段。
在《江城》一书中也是如此。何伟体认中国女性的总体困境,提及新的经济秩序带给她们的期待和要求经常互相矛盾,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容易陷入孤独和无望当中,女性寻求经济的自立可能会招致社会的批评和其他方面的挫败;他也写到了相当多样的女性群体,包括农妇、女学生、女教师、发廊小姐和面馆老板娘,而她们的性格和命运始终是模糊的,有着一层神秘的隔膜。显而易见的是,对于工厂里的男性,他确实更方便拉近视角,他记录下了陶氏姐妹的监工老田热爱买彩票的细节,了解调色师傅小龙喜爱阅读的励志书,因为他确实可以进入他们的宿舍,看到写在墙上的彩票号码以及翻开的书页。
二、快速变化背景下的阶级与金钱
如果读过何伟的作品便不难发现,变化是贯穿于他的中国观察的最重要主题,从《江城》到《寻路中国》,他逐渐将“快速变化”写作为中国社会的本质特征:
“在很大程度上,我所看见的那些城市其实就是一个个大的建筑工地。……无论在中国什么地方,人们总在建筑;城市在发展,整体在变化……围住中国的就不是万里长城,而是一堆堆的脚手架。”
“那样一种转型变化的感觉——接二连三、冷酷无情、势不可挡——正是中国的本质特征。”(《回到涪陵》)
他再一次回到涪陵时,旧城区已经完全拆除了。在《寻路中国》里,快速变化不仅影响到了空间布局和产业结构这类决定城市面貌的大事,也影响到了中国人的心理应对机制,许多人都有一套“先做后想”的逻辑,而“先做后想”可以带来成功;在《江城》里,何伟总结了他对于中国人思维套路的观察——看起来似乎复杂的群体,实际上在思维层面却整齐划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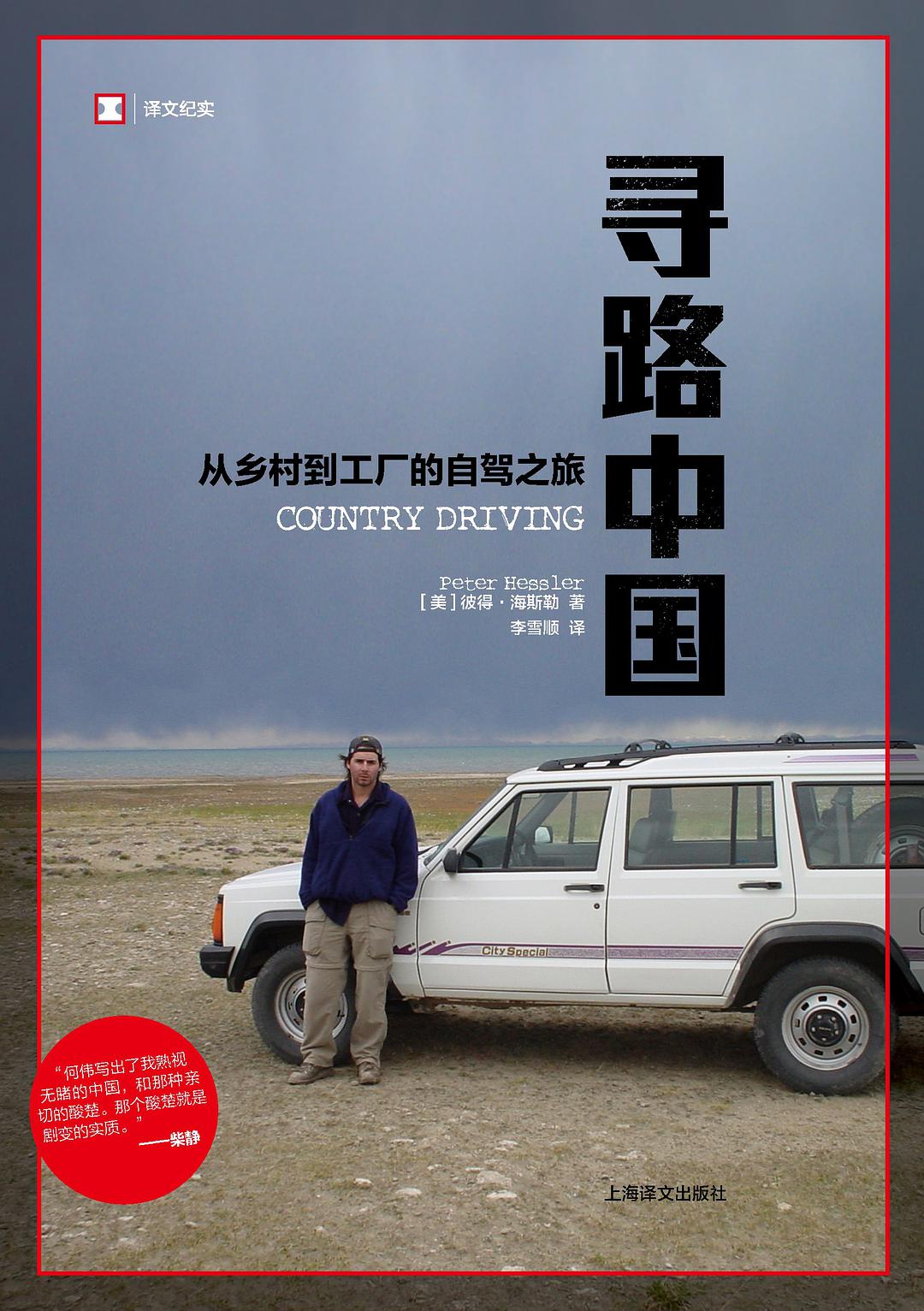
[美] 彼得·海斯勒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
仅仅将中国描绘为快速变化的、被脚手架包围的大工地,更像是一个外来者笼统片面的印象,从《江城》开始,何伟捕捉到的切入中国现实的重点之一,是人们对阶级和金钱的态度。中国人对钱的态度是直率的:当地人喜欢谈论钱,人们在谈到物品时完全可以问询价格,他被问询工资多少,也问别人有多少收入,谈钱就像“吃了吗”一样,是一种问候的方式。富有深意的是,在谈论金钱之时,阶级问题隐含其中——一群小孩子们比较压岁钱,他发现拿到压岁钱最少的小孩,来自一个养鸡的家庭。
师专的学生多数来自偏远的农村家庭,何伟也逐渐明白了来自农村家庭意味着什么。在课堂上阅读英文文学,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件比水田里耕地更容易的事,而与此对应的是,学生们也教会了何伟,在美国教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教授有多么值得怀疑,因为那些处境阔绰的教授们不可能比一位农民的女儿更理解她的处境。何伟讽刺地写道,“而我总觉得,那些满怀激情地大谈革命和阶级斗争的人更应该没有终身教职,如果你要听如何从文学的角度去诠释马克思主义,也应该到由学生亲自打扫教室卫生的大学里去听一听。”中国的农民不仅指从事农耕职业的人,农民是与城市居民截然不同的人,他们可能“成为偏见和屈尊的牺牲品”,就连“土”也可以作为一个贬义词。
《江城》里有一节名为《钱》,何伟大写中国式的对金钱的执着,金钱的作用不仅在于供养生活,也代表着在有限的资源中获得更多的机会。重点永远在于有限,而不是更多;比起从积极方面讲述金钱能买来什么,何伟更关心的是消极方面来讲金钱可以弥补些什么,比如应付罚款(超生、换工作等)。中国人对金钱的热望并不是出于贪婪,而更像是一种在相对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能过上更好生活的企图,有时候这变成了要摆脱贫困现状的“折腾”,而这些折腾通常都是缺少思考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就像《寻路中国》里的魏子淇先后尝试安利和旅游业一样。为了与这样的生活方式进行对比,何伟提到了美国式的乡村生活,与中国人牢牢抓住、精打细算相比,他认为美国农民基本是“没本事”和“好运气”的结合体。
值得琢磨的是,何伟对金钱和阶级的审视态度,在时隔二十几年重归中国之后,仍然在延续。他在四川大学教学时会给学生发问卷,想知道他们如何认知自己家庭的社会阶层;在接受采访时他回答说,从前的学生个子不高,现在的学生比他还要高,因为从前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户,而现在的学生出身城市中产较多——这印证了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流动性吗?学校类型和学生代际都已发生了变化——涪陵师专和四川大学在规模和等级上差距不小,他现在教的学生,算起来已经是当年学生的子辈了。
三、陈词滥调和含糊其辞
何伟在中国将镜头对准日常生活,也对人们平常使用的语言处处留心,并在学习和转述这些语言时,捕捉到了它们有趣又含混的面貌。这既包括例如“封建”“集体主义”“官僚主义”等具体词汇,也可延伸至课堂的课文用语、随处可见的口号和标语。以集体主义来说,他看到学生们经常会写我们中国人多么具有集体意识,而美国人通常讲究个人主义,但在涪陵的生活中,他看到的集体主义只限于家庭或小团体中,在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里,人们很少表现出认同感。就像扎堆买票时,集体主义体现为人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把票买到手,此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将他们凝聚起来,而正因如此,每个个体都拼尽全力地实现个人目标。在事不关己的情况下,人们更多选择围观而不是参与(何伟引用了鲁迅以强调中国人有围观倾向的观点),而这种围观而又漠然的态度会延伸至对更大社会事务的疏离。
何伟在书中引用乔治·奥威尔的话“语词和意义分了家”,描述他观察到的教学现象:学生们使用一堆政治术语,却并没有人指出术语的意义,语言和意义分家并不重要,只要他们学会“正确地”使用这些术语就可以了。詹姆斯·伍德在评价乔治·奥威尔时强调,奥威尔在描绘封闭的世界——英国生活以及概括它们的规律时有着出众的天赋,因为他同时看到了这个世界的真实性(它们被一种现有的生活文化制造出来),又看到了它的虚幻性(它们依赖自己特有的法则生存),于是将英国生活写作为一个既真实又充满虚构的地方。
有意思的是,这一点观察也适用于何伟,尤其是何伟对于日常语言的观察。他在中国见到的人们用语言构建出来的生活,既有真实的一面,也有虚构的一面——真实在于这些用语毕竟有着自己的历史和传统,也确实塑造了人们认识身边和自我的方式,“单位”和“关系”都是这样的例子;而虚构的一面在于,有的词语已经成了陈词滥调,大家都在使用,但谁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意思,像是“封建”被年轻人用来形容一切觉得老旧过时的事物,这种语言的使用变成了一种惯性,失去了指涉现实或辨明真相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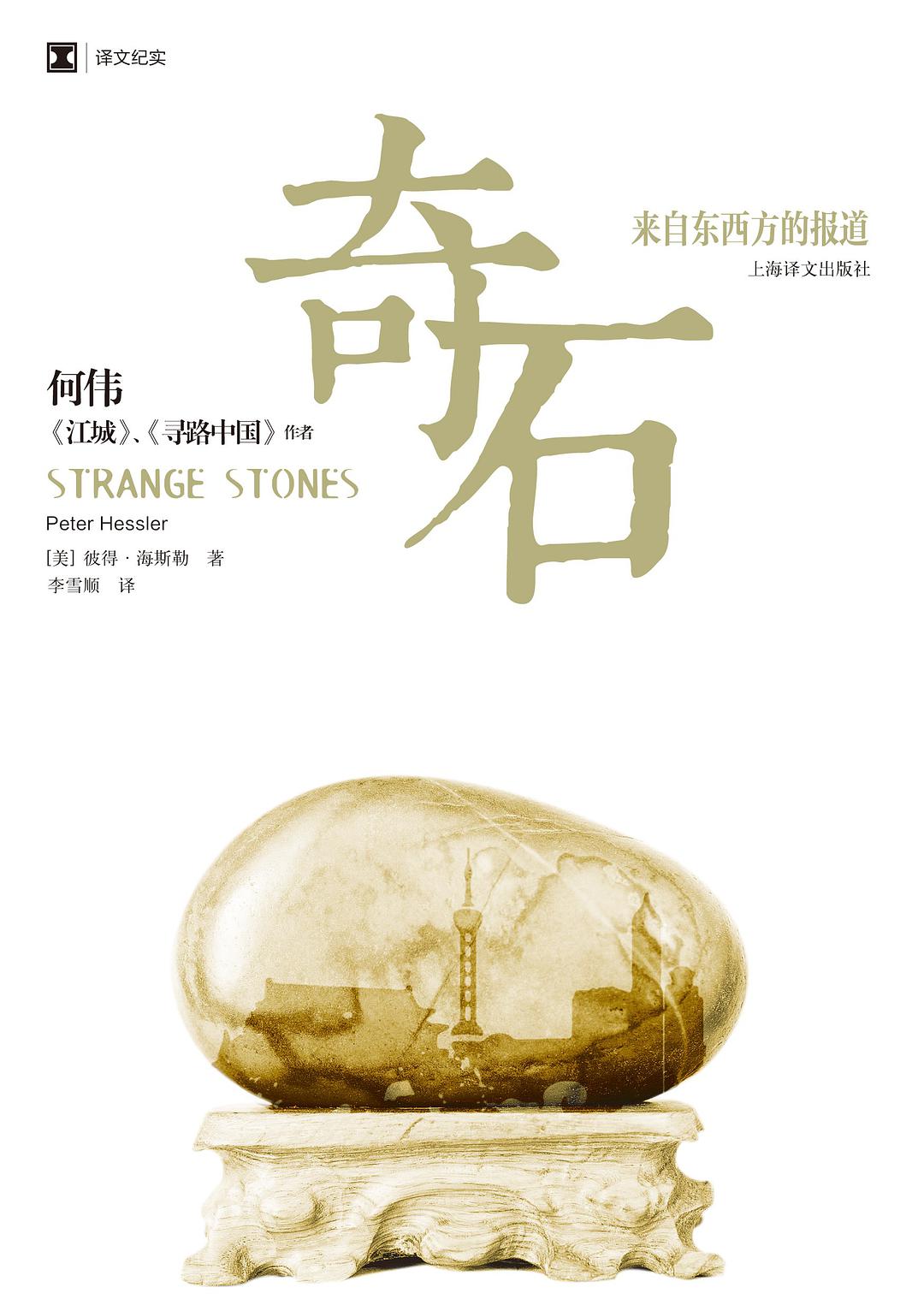
[美] 彼得·海斯勒 著 李雪顺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4年
反过来说,这些经不起推敲的用语也只是一个观察现实的窗口而已,更重要的是,就像指出这些用语可能是大而空的陈词滥调,连其中蕴含的情绪都整齐划一、距离普通人生活非常遥远的一样,何伟擅长写普通人命运如何被大时代塑造,这宏大影响中也不乏随机的成分。在《奇石》一书中,这种对比显得尤为强烈。他写2008年北京奥运前胡同改造工程引入了公共厕所,公厕又引入了外地夫妻和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就是在公厕边上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在《寻路中国》里也有这样的例子,他检查魏嘉的课本,发现小学生要学的东西令人迷惑不已——几乎是无关的事实和毫无系统性的知识,全凭背诵记忆,因为教育设计者想要囊括新旧知识、中西内容,然而却没有改变学习的基本策略以及课堂教育,所以小学课本成了这些东西冲突与妥协的战场。
何伟写作的含混之处在于,他针对的总是具体的对象——在魏嘉的小学教育这个案例里,他看到了人们理所当然接受的这个体系是有弱点的,却也承认这一体系运行的合理之处,即使是这样的机械式的、毫无章法的教育,也是有一定用处的:对村民来说,重视教育是代代相传的传统,而对孩子来讲,学到的东西虽然未来未必有用,却为他们进入中国社会做好了准备,基层的教化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基础。何伟不断以细节讽刺地指出体系的漏洞,接着又覆盖上一层解释,似乎在不断动摇观点与立场——这种具体的含混性的保留,也是阅读何伟时的困难之处,但是这样的写法是富有启发的,它教给人们如何解读自己的处境,既洞察它的弱点,又并非全然拒绝。
四、文学和社会学彼此对立吗
在先前南京举行的非虚构论坛里,与会者试图辨识非虚构与虚构文学的边界,从非虚构出发厘清社会学和文学的关系。潜藏其中的一重焦虑在于,虚构文体到底还能不能反映现实?这并不是一个新鲜的焦虑,美国作家奥斯卡·刘易斯初版于上世纪60年代的《桑切斯的孩子们》一书前言这样写道,当下的文学已经丧失了反映现实的能力,社会学应当接力踏入这片空白:19世纪时记录工业化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是由文学家来完成的;而今日同样的文化变革仍在欠发达国家不断上演,我们却看不到与之匹配的普世文学作品出现。——文学没有与社会现实与之匹配的重要原因在于小说家都在忙着书写反映中产生活的故事,已经和中下阶层与穷人的苦恼断了联系,而这时关心中下阶层和贫困问题的社会学就有了一席之地。
此处需要补充的背景信息是,何伟本人完全是文学教育背景,在普林斯顿大学英语系毕业之后,又前往牛津大学读了两年英语文学,而他后来的职业选择也确实和对学院派文学教育的不信任有关。原本他的计划是做一位英语文学教授,然而在英语系的教育中,他发现自己逐渐失去了对文学的热情,他不相信学院派的批评还与文学作品有关,更不相信这些大谈阶级斗争的人有足够的生活体验来支撑理论。谈及学院派文学批评,这几乎是全书最不含混、最锋芒毕露的时刻,他没有遵循惯常的写法和语调——在指出问题之后,他没有再转换视角覆盖一段解释。
“我发现,我不懂文学评论了,因为其中晦涩的学术性与作品的优美性相去甚远。对于绝大多数文学评论,我都不太明白,它们好似一团乱麻,无可救药地充塞着令人费解的字眼: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很少有文学批评针对文学本身做出反应,反而是文本被扭曲了,只有对评论家供奉的理论做出反应……无一例外,他们把手中挥舞的理论作为模子,把文本填充进去,挤出一个个形状均匀的产品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产生的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评论家生产出来的是后现代主义。真像是把毫无意义的同一本书读了一遍又一遍。”
在涪陵教授文学的两年时间里,何伟仍不断追问文学的意义;在课程即将结束之时,他也自问这些文学课对农家子弟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说相信有,那就是相信莎士比亚的诗歌可以在学生们未来的人生中留下一星半点的美感,而这美感中又有着一点永恒的不受日常生活所累的真实。只是下课以后,这种文学价值迎头碰见的就是严峻的现实,比如他的学生如何可以顺顺当当过上想要的生活。
我们从何伟的非虚构写作中仍然可以观察到文学传统的存在,至少在关注金钱、阶级、贫困问题方面,乔治·奥威尔是他的先行者之一。在写法方面也是如此,如詹姆斯·伍德在点评奥威尔时所言,奥威尔的文辞缺少一种“区隔感”,他形容贫困世界是“可恶”“恶心”“恶臭”,在巴黎的酒店也是“食物热乎乎的臭气”,他提醒着人们顾客和后厨的污秽之间不过一扇门而已,知识分子之所以能过上优渥的生活是因为有矿工在地底全身漆黑挥舞着铁铲。不在“我”和“他们”之间画出一条清晰决断的线,也是何伟的中国书写看起来让人亲切的地方,写着写着,Peter Hessler成为了何伟,或者是四川话里的霍伟。
从书本和学院走出,回到现实中来,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困境,这是何伟本人的职业路径。有意思的是,何伟也多次提到,他的家庭教育背景深刻影响了自己的选择:他的父亲是一位社会学家,教给了他与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陌生人相处的方法,也教会他付出时间和耐心来了解其他人,好奇、耐心、与他人交往的愿望也是好的报道的根本(《奇石》前言)。以何伟的案例看来,文学和社会学之间也许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位写作者的眼光、手法和内心。
相关链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