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萨拉热窝市郊泥泞的街上,两边都是老房子和杂乱的空地。4岁的迪亚娜(Dijana Voljevica)突然有了主意。她叫来四位小伙伴,悄悄告诉她们一个整人的点子:在巧克力包装纸上拉一小坨大便,将它送给街上那个叫做本巴(Bumba)的怪小孩。他什么都吃。看名字就知道。
迪亚娜将包装纸放在门廊上,敲了敲门,然后跑到灌木丛里,和其他女孩躲了起来。门开了,只有本巴一个人。她们大笑着,好像全世界都被捉弄了。本巴看到了包装纸,他捡起来放进了嘴里,下一秒便发出了尖叫。他的母亲立即跑出来,看到姑娘们落荒而逃。
几十年过去了,很久以后,1992年,迪亚娜的祖国波斯尼亚宣告独立,1995年,波黑战争结束,1996年,萨拉热窝的包围被解除——过去了这么久,迪亚娜仍然很喜欢讲这段童年往事。她有一种奇怪的幽默感。但恶作剧也预示着恶果。那天晚些时候,本巴的父亲找到了正在回家的迪亚娜。“嘿!来两口巧克力吧,你这犹太人杂种!”他高喊着,将“巧克力”糊到了她的脸上(当然,不知道是谁的)。弄错的身份(迪亚娜不是犹太人),粗暴的老男人,还有大便,这些还会出现在迪亚娜的战时生活之中,世界似乎又置身于一个恶毒的玩笑之中。不过,要想从战争中存活,迪亚娜先得从父亲的手里活下来。
2007年,迪亚娜带着她的自传体剧本来到洛杉矶。剧本记录了她的生活,她受到的种种伤害。它证明了战争并没有摧毁一切,它也会使人有所获得。战争让她有机会逃离虐待狂父亲。战争让她收获了爱情。战争改变了她,而且她喜欢后来的自己。尽管她痛恨战争,但自己活下来了,她觉得很骄傲。她所受的苦,让她对他人的痛苦更敏感。
2014年,我整理东西、准备搬家时,又翻出了迪亚娜的剧本。在大学读书那几年,我们俩一直在讨论这个剧本。她的人生故事不该被随意扔掉,写出来,感觉像一场小小的精神胜利。迪亚娜想讲讲她的故事,但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所以现在,我要替她讲。这离她的梦想很远,但至少迈出了一步。
本文基于多年来对迪亚娜和她丈夫尼古拉的采访。尼古拉是化名,他的家人还住在波斯尼亚,他担心他们有危险。本文也引用了迪亚娜自传体剧本的片段,为方便阅读,我做了一定的修改。当我向尼古拉核实迪亚娜的故事时,善良的尼古拉回答了这些有关他人生中最可怕日子的尖锐问题。我同时也参照公共记录、地图、史料、死亡证明、离婚记录、联合国调查、新闻报告及其他文件资料,确认事实。但在很多地方,迪亚娜和尼古拉的回忆是我唯一的资料。除了迪亚娜,所有名字均为化名。我相信她曾这样答应过别人,我为她遵守这个约定。
1974年“巧克力”事件之后,迪亚娜开始记录她混乱的家庭生活。她从奶奶法丽达(Ferida)开始,有关法丽达的一切都像肥皂剧。迪亚娜在剧本空白处写道:“奶奶太爱演了。她以为只要哭闹和哀求,别人就会同情和帮助我们。她的行为让我羞愧难当。”
法丽达曾问当地的钢琴老师,能不能让迪亚娜去上课,老师礼貌地让她先填写一张登记表。就是这么一张普通的登记表,让法丽达激动万分,连声道谢。她跪在地上哭喊着:“上帝保佑你,小姐。上帝保佑你。”尽管奶奶的行为总让迪亚娜尴尬,但她是爱着孙女的。毁掉一切的人是父亲侯赛因(Hussein),家中的独裁者,迪亚娜说。
1984年,迪亚娜15岁了。那时家里人习惯下午一起喝咖啡,但迪亚娜不准参与。那天,母亲纳米娜(Nermina)递给她一杯咖啡,这挑战了父亲的权威。迪亚娜在剧本中记录了这一幕:
侯赛因:放下杯子。
迪亚娜:不。
这更惹恼了他,侯赛因一把抓过迪亚娜的胳膊,把她拽倒在自己腿上,开始打她。法丽达看着他,脸上充满恐惧与犹豫。
纳米娜:侯赛因,别打了,我求你别打了。
侯赛因一边打着迪亚娜,一边指责说,是纳米娜的错。
法丽达试图阻止儿子。过了一会,侯赛因打累了,便放开手,迪亚娜掉了下来。
纳米娜抱起地上的迪亚娜。
1984年1月29日,纳米娜离开人世。她的去世总令迪亚娜难以启齿。她在剧本中曾含糊地提到,屋里某处传来了一声“惊恐的尖叫”。尽管没有具体的指控,但她总归罪于父亲。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父亲到底有无干系。
过了几周,侯赛因将迪亚娜从法丽达身边带走,和他的女友阿依莎(Aisha)住一起。“这是你新妈。”迪亚娜记得侯赛因当时的话。她不喜欢阿依莎的红嘴唇。
随着时间过去,迪亚娜学会何时躲开父亲,何时道歉,何时认错。但是侯赛因的脾气捉摸不定,随时都会爆发,迪亚娜永远无法安全渡过。有一天,迪亚娜放学回家的路上,侯赛因指责迪亚娜说,她搭了别人的车上学,他命令她说出那是谁的车。迪亚娜辩解说,她没坐车,她是走路去的。两人回到家后,侯赛因气冲冲地摔上了门。迪亚娜写了接下来发生的事:
阿依莎:怎么了?
迪亚娜:他觉得我坐别人的车上学。
侯赛因扇了迪亚娜一巴掌,一把抓起她的头发,拖到另一个房间里。迪亚娜尖叫起来。侯赛因把她按在地上,不停地抽打她。他趴在她身上,解开了皮带。
侯赛因:你这个小婊子。
迪亚娜想爬出房间。侯赛因抓着她的腿,将她拉了回来,用皮带的锁扣继续抽打她。迪亚娜尖声哭喊,开始流血。
医生说,迪亚娜头部遭受严重创伤,引起癫痫发作,情绪波动剧烈。脑电图扫描与核磁共振成像结果均确诊迪亚娜罹患癫痫,衰弱性癫痫就这样跟随了她一辈子。
好消息是,不忠的丈夫,必将是不忠的男友。阿依莎的朋友发现,侯赛因还和别的女人有一腿。阿依莎挂了电话,立马将迪亚娜赶出了家门。迪亚娜便高兴地回了家,和法丽达一起生活。
* * *
1984年,萨拉热窝举办了冬季奥运会。全世界看到了一个表面上多元包容的模范城市: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与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迪亚娜就是其中一员)和平共处,尤其是在种族如此复杂的波斯尼亚。种族是一种特征,不能成为“种族清洗”的理由——但这个词和即将到来的战争密不可分。
1991年,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解体,那年迪亚娜22岁。困于族裔民族主义、腐败司法、通货膨胀及失业率的六个共和国——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黑山及塞尔维亚分崩离析。当时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在邻国塞尔维亚及其军事力量的支持下,要求建立塞族共和国,扩充塞尔维亚版图,打造“大塞尔维亚”。迪亚娜的家乡萨拉热窝前途未卜。
危机早已存在:民族主义的军事力量,各种暴力的宣传,惹事的新闻报道,以及克罗地亚的血腥战争。
“我们是文明人。”迪亚娜在剧本中这样写道,表示她不相信。
然后,战争爆发了。
1992年3月1日,波斯尼亚举行独立公投。尽管投票遭到绝大部分波斯尼亚塞族人的抵制,但是在总人口315万之中,有将近200万人参与了投票,99.7%的选民赞成独立。一个月后,萨拉热窝爆发了围城战。在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之后被指控犯下种族屠杀罪)的支持下,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武装势力,即塞族共和国军队开始以穆斯林与克罗地亚平民为目标,事实上暴行殃及所有族群。军队在萨拉热窝周围的山上架起大炮,希望将这里并入赛族共和国及大塞尔维亚。居高临下的战略优势让萨拉热窝很容易被切断联系,并投放炸弹。迪亚娜和朋友在电视上看着她们的国家和世界崩解了。迪亚娜用一个朋友的尖叫,开始回忆那一幕:
桑尼娅(Sanja):我的天哪!
桑尼娅跑过来,将电视音量调高。我们难以置信地看到了他们的面孔。
桑尼娅:我们该离开这儿吗?
戈兰(Goran):妈的!
德拉甘(Dragan):好了,冷静。这是暂时的,一切都会平静下来。警方和军队会让所有人都平静下来。萨拉热窝不可能爆发战争。拜托,这儿可是一座城市,和纽约,和巴黎一样。
围城战爆发前,法丽达不幸中风。她一直请求让她吃最爱的巴克拉瓦点心,于是迪亚娜自告奋勇出门去买。她亲了亲法丽达的脸颊,喊了她一声“嬷嬷”,然后离开了。为什么不直接带法丽达上医院呢?我不清楚,但不管怎样,迪亚娜一出门就改了主意,决定去医院和医生谈谈。
在路上,她经过了两位自称为萨拉热窝警官的男子。事实上,他俩是非正式武装,和有组织的罪犯分子差不多。他们除了抵御塞族军队,还不时恐吓萨拉热窝的居民。
警官一:让我看看你的身份证。
警官二:你去哪儿?
迪亚娜:我去医院。我奶奶病了,得看医生。
警官一:我载你去。像你这样的女孩一个人走在街上太危险。
迪亚娜坐上了车。
警官一:你父亲叫什么?
迪亚娜:侯赛因。
警官一:你爸爸是哪门子穆斯林,给你取迪亚娜这么个名字?这什么破名字?迪亚娜,唔…
迪亚娜:这是个国际化的名字。我们走错了地方了。
他将她带到公墓,埋葬她母亲的地方。他命令她下车。听到她拒绝后,他靠近她,打开了仪表盘旁的置物箱,手肘还蹭了蹭她的胸脯。左轮手枪里有三发子弹。迪亚娜下了车。车外正是黄昏时分,而他强暴了她。
事后,这位警官在附近地公寓楼放下了迪亚娜,扔给她一卷钱,留下一句“明天六点见”,便离开了。那辆车转了弯之后,她想现在哭喊应该安全了。附近公寓的一位妇女听见她的哭声,跑了过来,并带她去了医院。
由于强奸犯是这座法纪越来越混乱的城市中的一名“警察”,迪亚娜怕报案会遭到报复。不只是她,医生也怕。他问她施暴者是谁,迪亚娜告诉了他。
“没人强暴你,”他说,“你该回家了。”
多年后,迪亚娜还能记起他那涨紫的脸色,肥短的手指和充血的眼珠。她还记得他额头淌下的大滴汗珠,还有他身上酒精的气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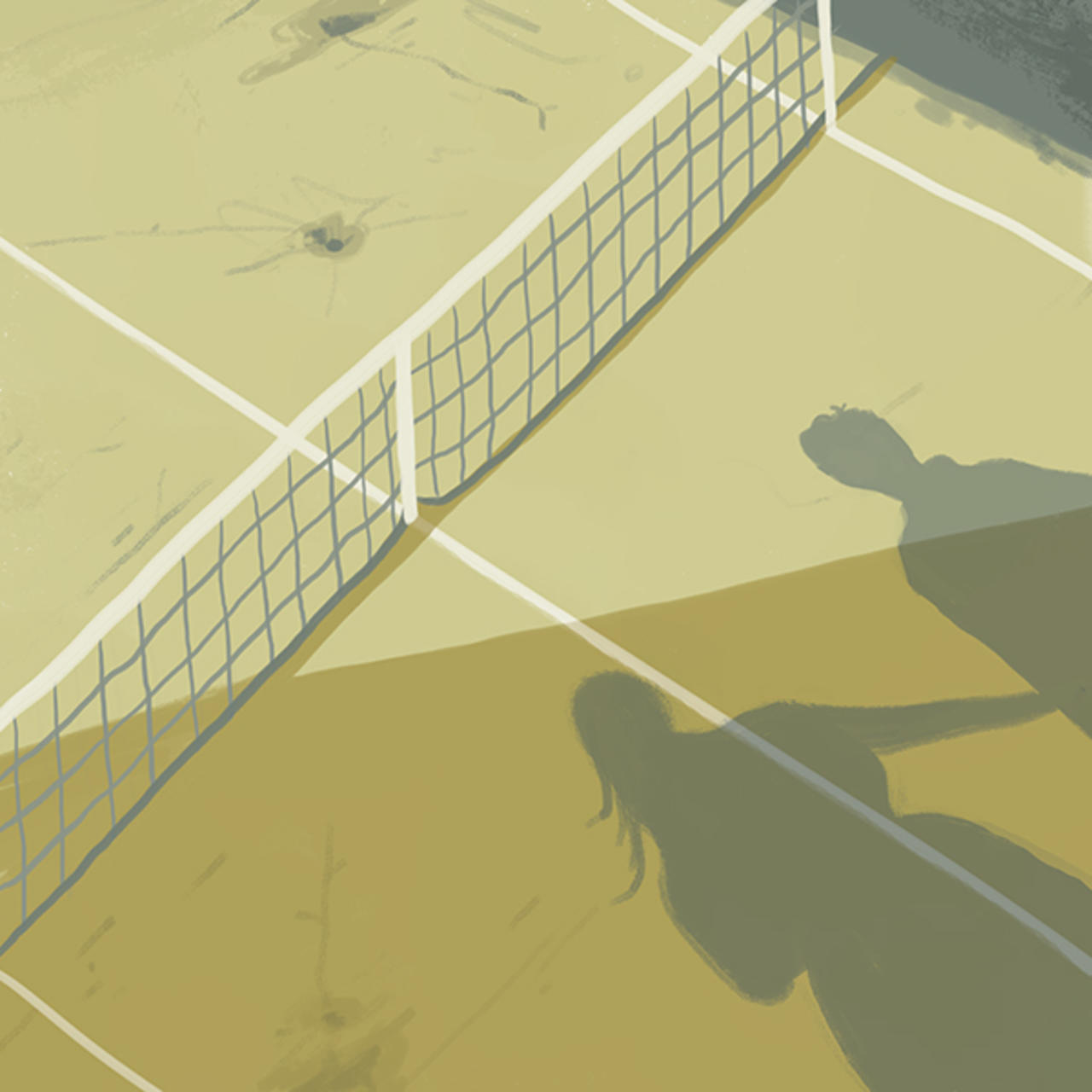
* * *
联合国调查显示,从1992年3月战争爆发到1995年12月14日《代顿和平协议》的签订,萨拉热窝平均每日经受的炮击次数高达329次,约35000栋建筑物遭到破坏。城市部分地区断水断电,人们活在塞尔维亚狙击手的恐怖阴影之下,成人平均体重足足减少了30磅。这座城市正在被谋杀。
法丽达在1992年、1993年之交的冬天去世了,当时迪亚娜和朋友们还在四处躲避狙击和迫击炮火,并寻找食物。
“我们得离开这座他妈的城市。”迪亚娜的朋友戈兰说。
要安全离开,得有钱和有人接应,迪亚娜和戈兰什么也没有。但是也有好消息。战争让迪亚娜远离了暴力的家庭。侯赛因跑了。他不在乎迪亚娜的死活,离开了这个国家,和阿依莎住在克罗地亚。这样一来,他们在萨拉热窝的住处就空了,那儿应该有吃的。
公寓在军队医院和假日酒店附近,国外媒体都喜欢在那儿逗留。迪亚娜和戈兰到公寓后,见到了阿依莎的姐姐阿雷瑞萨(Nevza),她问了一个今天看来再普通不过的问题:“你们是哪国人?”她的意思是:“你是塞尔维亚人,穆斯林还是克罗地亚人?”更进一步意味着:“你是哪边的?”戈兰说了实话:“我是塞尔维亚人。” 于是阿雷瑞萨报了警。
这次真警察来了,在他们来之前,迪亚娜和戈兰饱饱吃了一顿。迪亚娜说明了阿依莎是她的继母,警察便走了。她和戈兰留在了公寓。
尽管身处绝望之中,迪亚娜还是获得了片刻的幸福。
一个月后,迪亚娜在取水的队伍中遇见了未来的丈夫尼古拉。不知为何,动物园附近一间老房子地下室里的破管子里还在流水。关于两人的碰面,迪亚娜是这么描述的:
戈兰和迪亚娜排在队伍的最后面。等待取水时,一位年轻男子走过来,排在她们的后面,她们说:“嗨。”他高高瘦瘦,长发褐瞳,面带微笑,一下就吸引了迪亚娜的注意。
迪亚娜这样描写他们在网球场的约会:
尼古拉在吸烟。两人都没说话。他很高,很自信。迪亚娜脸红了,她看着他。很明显她被吸引了,但是又压抑着。我们想看到他们接吻,但什么也没发生。迪亚娜被叫去打球了。炮弹就在不远处炸响,但没人在意。有人放了个屁,大家都笑了。
他们第一次接吻,是在厨房的案桌底下。
尽管炮火纷飞,但迪亚娜和尼古拉在一起还是很开心。炮弹就在身边爆炸,屋子也为之一颤。两人热情地望着对方,呼吸变得急促,不仅因为恐惧,还因为爱。他们一直对视着,炮弹越来越多,他们接吻了。
迪亚娜、尼古拉和戈兰从提供食物和人道援助的清真寺走回来,遇见了四位波斯尼亚军官。接下来几分钟内所发生的一切,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迪亚娜写道:
军官二:身份证。
军官一:这位穆斯林女孩为什么和两位塞尔维亚人在一起?你们两个,怎么没在波斯尼亚军队里?17岁和18岁,可以参军了。
他用枪砸了一下戈兰的肋骨。军官三一把扯过迪亚娜的头发,她大叫起来。军官们揍了尼古拉一顿。军官三的无线电响了起来。人们从这里经过,装作没有看见。
军官三:我们有新包裹了。
一辆军用卡车来了。一位军官掀开卡车尾部的篷布,将他们三个推了进去。里头还有30位惊恐的男女。其中有一位男子已经断气,还有个女人一直在尖叫哭泣,不停敲打着司机的椅背。
车厢门开了。脚步声。一位军官掀开篷布,跃上来。他从坐在地上的人们身边经过,跨过那具死尸,揍了一个看他的男人,却轻轻地来到那位哭泣的女人跟前,拥抱了她。
军官四:你得呼吸点新鲜空气。来,没什么好怕的。他带着她下了车。
军官四:一切都会好的。
他迅速掏出刀子,朝她的太阳穴捅了进去。女人倒在地上,没了生气。他想把刀子拔出来,无奈它卡在中间一动不动。实在没辙,他只好握住刀柄左右挪动,最后总算拔了出来。他回到车上,发动引擎,猛一倒车,从女人身上碾了过去。
迪亚娜、尼古拉和戈兰被带到前线附近的一处废楼,就在萨拉热窝城内的山上,离市中心大概一两英里。铁丝网是用废旧自行车与金属零件熔化而成的,上面还有一根根的钢刺。大概有30名囚犯被囚禁在这个恶心的地方。只有一些人有毯子。当时萨拉热窝到处都是这种临时拘留营。波斯尼亚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人将塞尔维亚人抓起来,波斯尼亚塞族人也将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关起来,两边都对平民施以暴行。
Musan Topalovic,又名“Caco”,一个穆斯林军事领袖,自称“城市保卫者”,整个拘留营归他管。1997年,《纽约时报》采访了Caco团伙的一个成员Salih Jamakovic。“Caco杀死了不少塞尔维亚人,连一些穆斯林都不放过。他说,这些人在他的地盘与塞尔维亚人里应外合,”Jamakovic说:“他会在夜里载一些尸体来到这里,丢入挖好的坑里。那些在这里处决的人,要么被Caco的枪手射死,要么被特别行动小组杀害。”有可能迪亚娜、尼古拉和戈兰就被带到了这里。
在“那个地方”——该拘留营没别的名字——食物匮乏,警卫无情,前线是致命的。有些女人和孩子被用来交换塞族占领区的穆斯林俘虏,有些男人被叫去前线挖战壕,再也没有回来。女人都在避开警卫,但不是每次都躲得过去。迪亚娜还记得:
看到细小门缝中男人的眼睛,营地里的女人都噤声了。迪亚娜和其他女人一样,死盯着那扇慢慢推开的门。两个士兵走了进来,门没关紧,留了条缝。我们看着这两个家伙从左到右,逐一打量房子里的女人。
年轻士兵:想念被操的感觉吗?
两人大笑。
士兵一:让你看看穆斯林的鸡巴有多棒多干净。
士兵一扯过其中一个女人的头发,她倒在了床上,开始哭喊。
年轻士兵:把衣服裤子脱掉。你干净吗?
女人:干净。
士兵一:塞族人就连大便完都不洗屁股。这国家真够恶心的。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瓶白兰地,往女人的阴部一倒。女人尖叫起来,他立马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三人的逃亡并没有事先计划,不过可能正因如此,他们才成功了。迪亚娜、尼古拉和戈兰来这儿四天后,附近一场激烈交火分散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们趁此机会挖洞钻过了铁丝网。三人拼命地往外跑。
戈兰:我真不相信就这么简单。
迪亚娜:简单?我们还没跑出这鬼地方多远呢。
他们穿过废墟,朝萨拉热窝市中心跑去。接连跑了几英里,几个人来到了河边,找到一条下水管道。他们大口大口地喘气,在里面稍作休息,下水道的恶臭让人作呕。(迪亚娜真没想到,大便和民族仇恨会以这样的方式重现,简直荒谬极了。)一个小时后,他们确定后面没人跟来,唯一要做的就是往前走了。
他们打算去格巴维察(Grbavica)碰碰运气。格巴维察曾经是不同种族混居的繁荣街区。尼古拉就在那儿长大,他父母在那里有一套房子。但三个人都不知道现在谁控制了格巴维察,只知道一些也许是错误的传言。
夜晚,他们来到了貌似已经荒废的Pionirska大街,暂时躲在法迪拉(Fadila)的公寓里。五六十岁的法迪拉待人和蔼,她与患病的丈夫住在一起,迪亚娜在战前就认识她的丈夫。这对可怜夫妇给孩子们准备了点食物、衣服和德国马克——当时萨拉热窝唯一通用的货币。
三人重新上路,沿着河往满目疮痍的格巴维察走去。他们经过不少新挖的坟墓,还有个炸裂的水槽,在弗尔巴尼亚桥(Vrbanja Bridge)停了下来。
“欢迎来到塞族共和国。”迪亚娜在剧本里写道。
他们无意中踏入了塞尔维亚领地。迪亚娜解释了为何他们没有遭到枪击:那里的将军早前安排了用穆斯林俘虏交换他女儿及她男友,边界的士兵以为迪亚娜是将军的女儿,所以便把她、尼古拉和戈兰带到不远处的建筑物里。在那儿,他们见到了这位自称是将军的军事头目。他命令三人留在这儿,在他的统治下生活。两位士兵带他们到一处废弃公寓,他们在那里过夜,和其他士兵在食堂一起吃饭。看来,逃亡成功了。
但很快,尼古拉和戈兰又回到了将军的办公室。
波斯毛毯的上方挂着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和拉多万·卡拉季奇的巨幅画像,后者现正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前南法庭)接受审讯。塞尔维亚民主党建立者卡拉季奇被指控种族灭绝等一系列罪行,包括“谋杀、非法攻击平民、以向平民散布恐慌为根本动机的暴力行为、劫持人质”等。米洛舍维奇在审讯期间就已死在狱中。
将军:好消息。我们觉得你俩有成为优秀士兵、为国献身的潜质,我决定将你们送往Ozrenska。
尼古拉:长官,恕我直言,我们才17岁,才刚逃脱穆斯林地区地狱般的生活。Ozrenska可是萨拉热窝最激烈可怕的一条战线。
戈兰:我们不去。
士兵:在长官面前不能这么说话。
戈兰:去你妈的。我们不去。
将军:妈的孬种。你们算不上真正的塞族人。将他们带走。
将军把尼古拉和戈兰囚禁起来,和其他塞族人一起,关在萨拉热窝机场附近的军事用地。
在那里,一些囚犯喜欢拿自己的罪行开玩笑。一位退役士兵吹嘘他怎么将出轨的妻子和第三者干掉,另一个人声称自己杀掉了两个穆斯林老女人。八天后,尼古拉和戈兰参军了。
与此同时,迪亚娜一个人待在废弃公寓,恐惧又孤独地等待着。在塞族领地,她的姓氏很危险。她听说,这栋楼有两个女人都被醉酒的军官杀害了,她们都带有穆斯林的名字。但她能逃去哪儿呢?
戈兰和尼古拉被分派与另两名年轻人达克(Darko)、伯言(Boyan)一起驻守。他们都担心北约的飞机会把这块地方给炸了。
萨拉热窝Ozrenska大街上的楼群与树木形成了一条战线,波斯尼亚军队和塞尔维亚军队各占一边。狙击手经常在Ozrenska大街上寻找位置,这条街很长,足以看到整个萨拉热窝城。这条大街对双方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尼古拉帮迪亚娜写下了前线的驻守经历:
达克:去他妈的战争。去他妈的塞尔维亚人,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你们都不得好死。
达克开始卸下弹药、枪支、手刀和手榴弹。尼古拉和戈兰抓住他的臂膀,让他停下来。
达克(歇斯底里地):我要走了。就这样。去你妈的,去死吧。
尼古拉:闭嘴吧你。你这样会害死我们。
戈兰:冷静一下,兄弟。
达克(盯着远处):你们觉得美国人真的会炸飞我们吗?
戈兰:不会的,达克。他们才不在乎我们的死活。穆斯林只是希望美国人能帮忙。
突然,听见轻声枪响。达克的头回弹了一下,身子抖了两抖。
尼古拉脸色煞白,一动不动,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一阵沉默。我们看到尼古拉和戈兰汗涔涔的脸,眼睛瞪得老大,警惕地等待下一声枪响。一阵寂静。他们朝看不见的敌人胡乱开了几枪。
尼古拉哭了起来,他和戈兰合力将达克搬上担架,将他抬到一辆应急军用卡车上。尼古拉跟着他一起上了车。
尼古拉:达克,我们要去医院。别害怕。
红十字会官员:嘿,兄弟,挺住。
尼古拉:哦上帝,求求您。
尼古拉用手包住达克的头,泪水漱漱而下。
现在,尼古拉尽力不想起打仗的日子。“事实上,战争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较量,”他告诉我,“不幸的是,非人类赢了,我们只得四下逃散。”
* * *
1993年秋,尼古拉和戈兰得到了七天的休假,他们想趁机和迪亚娜一道逃到伊利扎(Ilidza)去。伊利扎也是塞尔维亚控制的地区之一,算得上是最安全的郊区,戈兰的父亲就住在那儿。但尼古拉和戈兰还属于军队,擅离职守很冒险。迪亚娜想出了一个疯狂、大胆的主意,再一次奏效了。她将这段故事娓娓道来。
迪亚娜:如果你去看医生,说你失去知觉,伴随头疼、尿失禁、舌咬伤,什么都想不起来——好几周以来都这样——医院就会怀疑你得了癫痫。他们会把你送去帕莱(Pale)医院的神经科做脑电图扫描,到时我替你上。拿到结果后,我们再在你名字后面添个“A”,就成了女孩子的名字。回来后,我们再把“A”擦掉。反正那里没电话,他们没法核实。只要确诊癫痫,你就成了残疾,不能再参军。
一周后,收到了来信。尼古拉确诊患上癫痫。
但戈兰还在军队,没法离开。(他们决定不在同一所医院再玩一次癫痫的伎俩。)不过幸运的是,戈兰被调去伊利扎,驻守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边界。尽管不时还有轰炸,但这差事算不错了。
他们在伊利扎待了一年,熬过了一个寒冬。1994年初,迪亚娜和尼古拉决定完全离开战争。他们逃到了塞尔维亚的首都贝尔格莱德。那儿更安全,他们或许能通过亲戚找份工作,同时在联合国难民署的帮助下去别国生活。戈兰的父亲给他们买了汽车票。迪亚娜还记得汽车司机的警告:“亲爱的乘客,为了躲避流弹,接下来的两分钟我们将开得非常快。一路上请低着头,上帝会保佑我们的。”
难民要想迁至别国,往往要等好几年。在此之前,迪亚娜和尼古拉只能想方设法活下去。尼古拉找到一份给杂活店供应食品的差事,但经济不断衰退,两个月后他就丢了工作。他只好做些杂工,画点画儿,在农贸市场卖些水果。尼古拉和迪亚娜永远都不知道第二天要在哪儿过夜,有时他们有个公寓,有时候啥也没有。也有热心人收留他们,给他们食物和住的地方,也有朋友向他们施以援手。
士兵要想得到前往贝尔格莱德的许可,往往也要等上好几年。但戈兰只用了四个月就到手了。他离开了军队,与迪亚娜和尼古拉汇合。
但是对戈兰来说,仍有一些障碍。联合国难民署不太可能帮助戈兰,他可是一位离开军队、未患癫痫的适龄未婚男青年。解决方法奇怪而简单——也是大家常用的策略。迪亚娜和戈兰结婚了。联合国难民署不会拆散夫妻。
迪亚娜保留了戈兰的姓。或许她想忘记自己的过去。
戈兰和尼古拉从军队里逃了出来,但也有可能再次被征入伍。在等车前往贝尔格莱德的郊区时,迪亚娜和尼古拉经过了臭名昭著、残忍至极的塞尔维亚军事部队阿尔钦老虎团(Arkan’s Tigers)。两辆黑色军用吉普车往汽车站开来,身穿黑色制服的士兵开始以打仗的名义强制征兵。
士兵一:所有来自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人立即到前面来。
他们开始检查身份证,还将一个男人带到了车上。队伍里有人开始往外跑。
迪亚娜:快跑!
尼古拉和迪亚娜成功逃走了,但他们还得等待联合国难民署的消息。
1999年3月,老虎团军阀泽利科·拉日纳托维奇,又名阿尔钦,被指控犯下反人类罪行。2000年,阿尔坎在贝尔格莱德洲际饭店被不明身份的枪手击中眼睛致死,逃过了国际法庭的审讯。
迪亚娜和尼古拉在危机与贫困中度日,直到1994年末至1995年初,一切才开始好转。联合国难民署通知他们将与戈兰一起迁至其他国家。(出于一些未知的原因,他们很幸运,联合国难民署原本没有义务将尼古拉与戈兰夫妇安顿在一起,因为理论上他们并不是一家人。)1995年12月14日,《代顿和平协议》于巴黎正式签署。1996年6月,三人抵达了佛罗里达奥兰多市,那儿是他们的新家。
联合国难民署代表:29号。这就是你们的家。
迪亚娜:这儿安全吗?
联合国难民署代表:奥兰多挺安全的。虽说不是最安全的,不过和你们来的地方相比,很安全。欢迎回家。
室内。佛罗里达州公寓。深夜。
尼古拉与迪亚娜躺在床上。尼古拉翻身看向迪亚娜,叹了口气。
尼古拉:我真不敢相信我们在这里。
红蓝警灯交替映入房间,在墙上不停地闪烁。
迪亚娜: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尼古拉:真让人激动。这是我们在美国的第一夜。
外面的黑暗中传来一声枪响。剧本结束了。

* * *
迪亚娜从未听说过山口疆,但她一定理解他的故事。
1945年8月9日,山口正在广岛出差。早上8点15分,艾诺拉·盖号轰炸机进入广岛上空,投下原子弹“小男孩”,九万人的性命毁于一瞬。两天后,幸免于难的山口返回长崎,再一次亲历原子弹“胖子”的轰炸。“胖子”夺走了七万人的性命。山口又一次活了下来。2010年1月4日,山口疆去世,享年93岁。
这个故事说明了迪亚娜剧本题目《13-29》想要表达的——不幸中的大幸。山口难道不是最幸运的不幸之人吗?这也是迪亚娜的人生问题。萨拉热窝围城战让她遇到了尼古拉。在弗尔巴尼亚桥被士兵误认为是“将军”的女儿——救了他们一命,但也将尼古拉和戈兰送上了战场。她的癫痫症让尼古拉逃过一劫,却让她痛苦不已。而这场战争最终让她来到美国的新家。“13”是迪亚娜8月份生日的日期,“29”则是两个特别的日子。1984年1月29日,她的母亲去世;1992年1月29日,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首次发起了独立公投。两个日子,都是幸运的,又都是不幸的。
我无法全然洞察迪亚娜的想法,但她非常希望有人见证自己这种矛盾的运气。迪亚娜的生活有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战争的模式,或许也是和平生活的模式,但是暴行使其清晰可见了。她清楚所有这一切何等残忍、何等荒谬,她希望他人也能看到这一切。她还希望让别人知道,她所经受的痛苦塑造了新的她,她很喜欢那样的自己。这些痛苦让她变得更好,让她更能感受他人的不幸。她待人热忱,甚至有些过了头。她习惯友好,可能是出于感激吧。
尼古拉和迪亚娜必须学习如何在美国生存。他们学英语,上驾校,找工作——做当地人平常都会做的事。但是经历了那么多事,想再过上普通生活并不容易。迪亚娜的癫痫没有好转,医生换药后甚至每况愈下。有一次服下新药后,迪亚娜差点从窗户跳出去。不过,多数日子并不这样。迪亚娜、戈兰和尼古拉都找到了工作。迪亚娜从社区大学毕业,尼古拉很喜欢美国的闲散氛围。
2003年前后,为了继续接受教育,迪亚娜和尼古拉搬到了马萨诸塞州,就住在波士顿外围。两人在那儿结婚了。(当然,她与戈兰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两年后,我第一次见到迪亚娜。早上9点,在爱默生学院的一堂发展理念的课上,她癫痫发作了。后来在媒体制作入门课上,她又发作了一次。这次,我知道她把药放在了哪里。几周后,她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帮助她完成剧本,而我只能在地图上找到萨拉热窝。
爱默生学院是波士顿市中心的一所艺术学院,对独特的事情都很开放。但迪亚娜实在是太独特了。同学和教授都很友好,但与她之间总是隔着一段冷冰冰的距离。他们不知道她的身世(他们为什么要知道呢?),于是无法理解她的言行。她认为有些人生来就是邪恶的,这样的言论吓跑了周围的人。
坏日子那么远,又那么近。每次迪亚娜癫痫发作,尼古拉都会接到电话,爱默生学院的教授和迪亚娜的上司都束手无策。尼古拉便换成晚班,第二天一早再跑来麻省大学波士顿校区上课。
尽管如此,迪亚娜和尼古拉在波士顿还是生活得很好。他们找到了工作,租了一间房子,结识了一些朋友,规划着未来的生活,还养了一只猫。他们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但迪亚娜一直梦想着把她的故事搬上荧幕。所以在2007年,迪亚娜和尼古拉踏上了西进之路。
迪亚娜在邮件里曾向我提到,她要去洛杉矶实现梦想。搬到北好莱坞后,她开始迈出第一步,在电梯里向中产阶级人士游说她的故事。据她描述,这些人似乎对她的剧本有点感兴趣。但什么也没发生。几个月后,迪亚娜对洛杉矶人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富人与名人是好人,只是难以碰面;而没那么有钱和有名的中产阶层几乎都待人冷漠(虽然容易碰面),因为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赚钱和出名,所有洛杉矶人差不多都这样。但迪亚娜没有就此放弃。
迪亚娜相信,在美国,人的故事是能被听见的。几年来,她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创作剧本。她自信地前去洛杉矶,想象着她生活在故事的结局。空中镜头拉远,她开着车风驰电掣,音响开得老大,一切皆有可能。这就是她想要的结局,这是她应得的结局。但是,一次癫痫大发作却在睡梦中夺走了她的性命。
几乎没人认识迪亚娜,更别说记住她是谁,她想要的不是这样的结局。她想要一部电影,作为生活极端不公的见证。她想让人们知道她如何死里逃生,来到美国。2007年9月17日,她去世了,连一篇讣告都没有。
尼古拉不知道戈兰在美国过得怎么样,是不是还住在那儿。多年前两人大吵了一架,尼古拉不想说太多,只知道之后他们再也没有往来。他说,戈兰可能已经改名换姓了吧,我找不到他。尼古拉还住在美国,他再婚了,看起来很高兴。每年,他还是会庆祝迪亚娜的生日。
——END——
Daniel DeFraia,自由撰稿人,正在波士顿大学读美国研究专业博士。
Eros Dervishi,阿尔巴尼亚籍插画师,现居纽约。现在他的时间主要花在阅读、学习烹饪、感知外界上。您可以在erosdervishi.com欣赏他的更多作品。
翻译:潘金花 校订:郭玉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