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不仅是我们操心的问题,也是历代哲学家操心的问题。对于幸福的讨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有着各自思考,且有着各自的观点差别。其共性是,他们都赞同“善”对于幸福生活的重要,但比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在意善的多元性。
比如,在某些场合,当勇敢无用且仅仅是无谓的自我牺牲时,不勇敢倒更是明智之举。而慷慨是好事,但太过于慷慨则使人成为轻率挥霍之徒。因此对德性而言,亚里士多德跟在意尺度的把握。
在《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一书中,哲学家理查德·大卫·普莱希特对上述两位哲学家关于幸福的思考进行了分析与描述。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经出版社授权,选取书中相关部分与读者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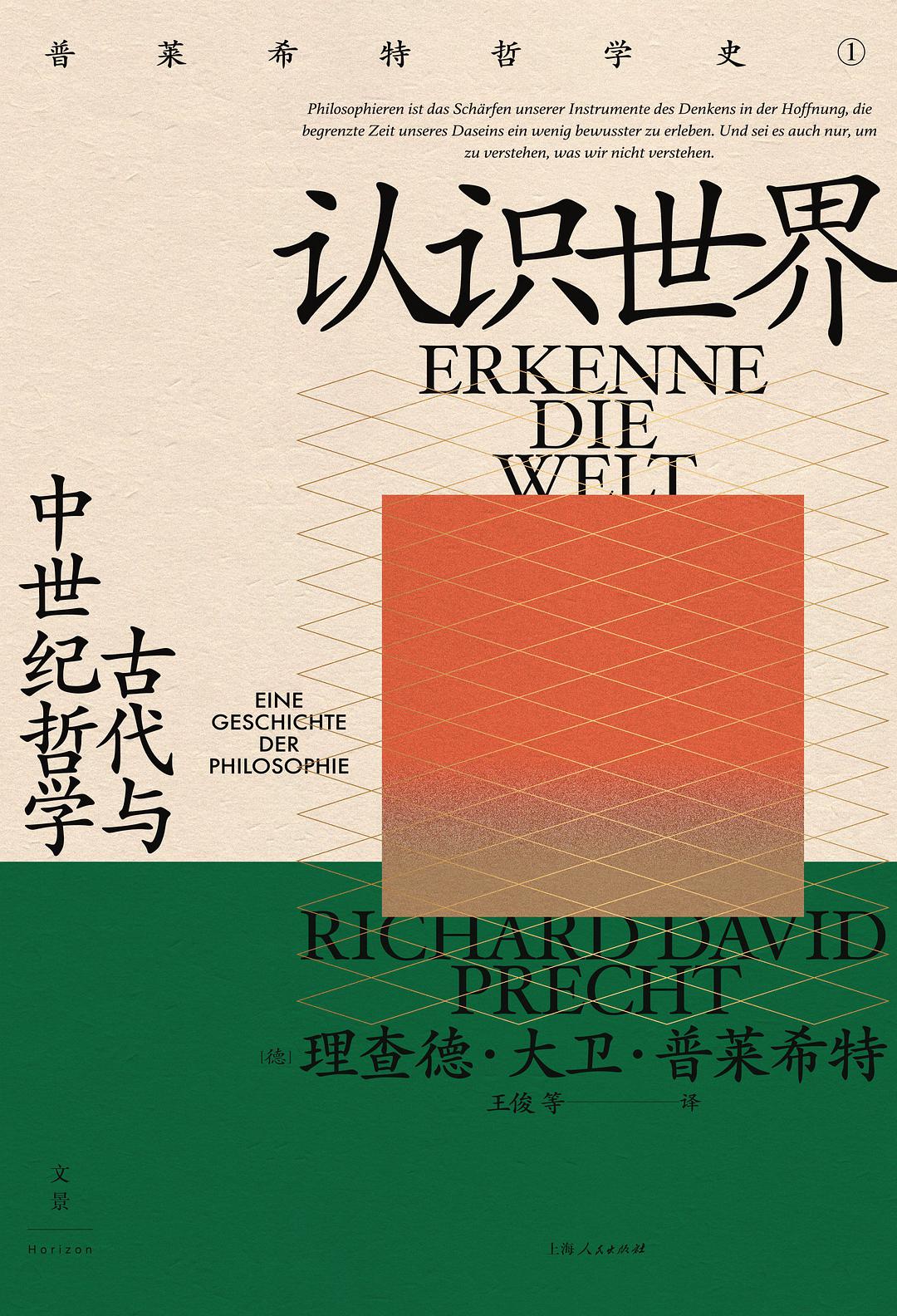
译者: 王俊 等
版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2021-4
道德动物学
教育出一位凭借穷兵黩武、挥霍无度、凶狠残忍、暴虐无道且杀人无数而从其同党中脱颖而出并被写入史书的王子,这对一位哲学家来说不能算是功绩。人们之所以能不计较亚里士多德曾兼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而仍认为他理应是哲学史上或许最重要的伦理学家,是因为一系列永远与他的名字密不可分的、格外明智的洞见。
从道德角度观察世界的人会把世界分为他所尊崇(achtet)的和他所鄙夷(ächtet)的事物。这一区分有相应的规则吗?我能客观地认识到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吗?如果我可以认识好坏,那么存在一条指导我将认识落实到生活中去的准则吗?从柏拉图开始,道德哲学一直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在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那里,一切“正确的”人类行为都有一个目标:一种成功的、“幸福”的生活!

亚里士多德对道德上善的生活的追求承袭于他的老师。然而,他们的共同点也就仅此而已了。当柏拉图作为形而上学家着手探讨伦理学问题,并在理念世界探察永恒和绝对的规范时,亚里士多德则更像一位行为研究者那般研究伦理学。人是如何行动的?为什么人们做出如此这般的行为?是什么推动着他们,是什么成就了他们的幸福,又存在哪些危险的诱惑?为什么道德行为如此困难?为什么尽管所有人都追寻幸福(eudaimonía),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偿所愿?
一直以来,亚里士多德既是伦理学家,也是行为学家。如在动物学研究中那样,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研究中也首先是一位细致的观察者。遗憾的是,他作为人类学家仅仅较精确地考察了单一的种类:自由人!而奴隶和妇女被他刻画为有缺陷的生物。他们在他的一切伦理和政治考察中被边缘化。许多同时代人也有类似看法,但如我们在围绕柏拉图的讨论中所见,肯定并非所有人都是这样。在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严格从确切经验和精细观察出发来发展其哲学的人看来,亚里士多德对于女人和奴隶充满成见的看法毫无疑问是令人失望的。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不算公民,而仅仅是一个不受待见、没有公民权的外邦人。因为这种身份,亚里士多德远比作为上层贵族的柏拉图对传统贵族伦理更具批判性。但他并不拒绝贵族伦理的核心:一种“光荣的”、有德性的以及沉思式的生活理想。亚里士多德反感的是威权、等级制以及伴随柏拉图的道德上善的生活的理念而出现的绝对之物。亚里士多德并非要推倒旧贵族伦理,而是要将这种伦理“民主化”,扩大其适用范围,让每个公民都能过上这样的伦理生活,而不仅仅是哲学王或护卫者阶层。19 世纪的市民阶层在流行时尚、精致礼俗和宅邸装潢中模仿贵族的举止仪态和品味格调,并让他们最高的政治代表在宫廷中居住,而亚里士多德则极力促成公元前4 世纪的贵族道德“市民化”。
亚里士多德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关于伦理学的论述。他的三部作品,《欧德谟伦理学》(Eudemische Ethik)、《大伦理学》(Große Ethik) 与《尼各马可伦理学》详细讨论了如何追求正确的生活与共同生活的问题。《尼各马可伦理学》远超他的其他伦理学著作,最为著名。它是第一部完全致力于伦理学的学术著作。而它的书名是谜一般的存在,因为我们不知道此书是献给哪位尼各马可的,亚里士多德的父亲和儿子都叫这名字。
《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目标在一开始就被提出。亚里士多德想要指明,一个人为了过上完满的生活必须具备哪些能力和物质财富。这一目标不仅仅是获得关于善的理论知识。柏拉图认为,对善的准确认识足以完成善行的实践,而亚里士多德则看到生活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跟柏拉图不同,他由此总结出一个关于必要的和值得追求的灵魂财富与其他财富的完整目录,对于追求幸福生活的人,这些财富是应该拥有的。
然而伦理学比动物学要困难棘手得多。尽管亚里士多德主张伦理学可以被科学地规定,但是,对善的生活的科学规定并非非黑即白,其中还有许多灰色调的细微渐变。在生活中,认识善是一件事,实践善的生活则是另一件事。除可精确规定的诸多常量以外,还会出现许多变量。伦理学是探讨规律外的例外情况之领域。这是令人信服的洞见。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比柏拉图“非人性”的伦理学更人性化——也就是说,更符合人类的本性。
行为研究者的“动物学”视角总归还是在伦理学中看到了一个所有人共同的目标。因为人类出于本性不仅仅生物性地追求着诸多目标。正如植物朝向阳光,人类也追求那些对生活有益的东西。人类是具有理性灵魂的生物,这一追求伴随着怎样才是特别有益的和能实现的这样的考虑。因此,在人类生活中,重要的不仅仅是成功,而更是幸福。因此,幸福生活(eudaimonía)是能够反思并最终改变其行为的生物之理性目标。在此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我们因此做出的许多行动决策,都是人具有的人类学基本特征之一。
人类天性向善。如果我们做好事,我们就过得好。凭借这个定义亚里士多德给人类设定了目标,而并没有让一种世界灵魂或人类世界之外的理念在此发挥作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也是一种自然法伦理学。而并不依赖于超验的善之理念,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理性的生物。好的行动合乎一种更高形式的意图。它将人类的追求导向其目标。
不过到底什么是好的行为呢?对于柏拉图来说,如果行为的意图是好的,那么行为便是好的。行为以这种方式分有善的理念。柏拉图的伦理学是一种意向伦理学(Gesinnungsethik)。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只有行为的好的意图得以实现,它才是好的行为。也即是说,意图与其成功实现不能分离,二者必须同时被考虑到。出于好意的行为若是没有成功,那么其目标就没有实现,行为便也不是好的。比如我想勇敢,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因为有太多的畏惧,我就是做不到。意志薄弱者、优柔寡断者以及失控者经常就这样失败了,尽管其意图是好的。
柏拉图没有考虑到这种情况。而后来的哲学家将对行为的评断进一步推至结果,且仅仅评价结果,也即行为的后果。据此,如果行为的后果是好的,那么它就是好的(后果主义)。然而,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走那么远。正如对他而言,生命不能被割裂为行为与行为的实现,伦理行为也由意图与结果之不可分割的共同体构成。谁实现了“行善”之目标,他便达成了善。正如实现了勇敢之目标的人是“勇敢”的,即使后来证明这种勇敢是不必要和鲁莽的。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也是意向伦理学家,而非后果主义者;当然,他承认,我们的意志是薄弱的,而我们的意图有时并不坚定。出于好意的行为因此往往难以成功。道德行为因而不仅仅如柏拉图所主张的那样以理性洞见为前提,而是同样以相应的稳定的品性(Charakter)为条件。那么我要如何获得稳定的品性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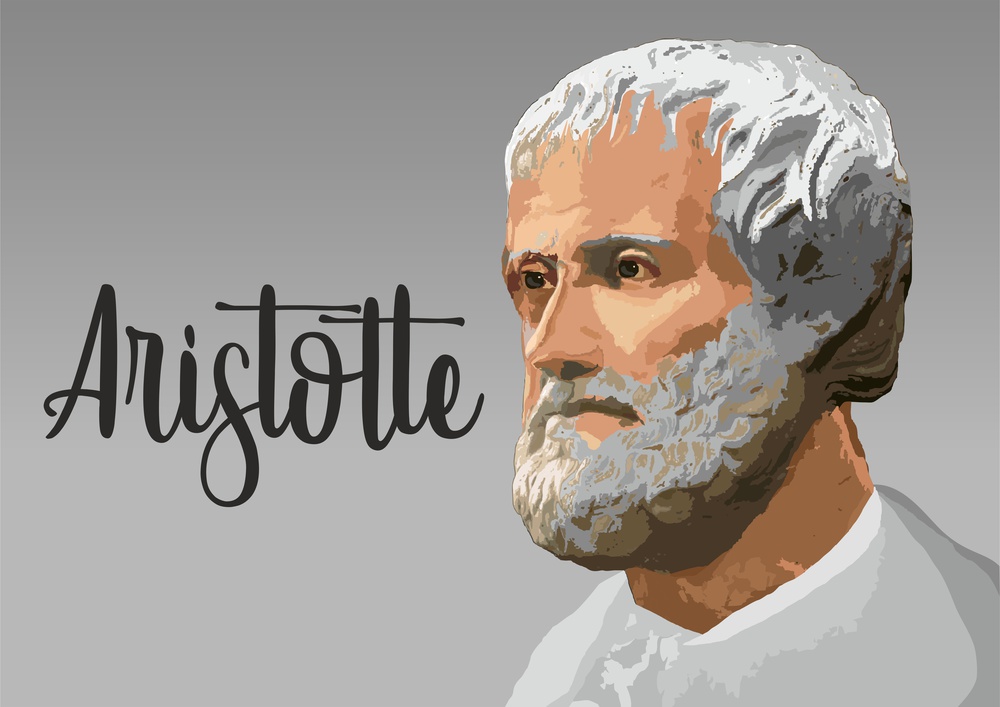
德性
我们行为的目的是幸福生活,这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是毫无疑问的。亚里士多德不考虑这一点,即一些人有意作恶。这一想法在他形而上学式的生物学中也是不适合的,在他看来,所有人从本性上都是追求善的。人类究竟如何达到完满的生活,这种生活具体存在于何处,对此人们往往争论不休,“大众与思想家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我们还要补充一点,即这种状况至今并没有改变多少。因为人们对思想和更高价值的需求显然是十分不同的。很多人将诸如性、有吸引力的伴侣、华衣美食、社会地位以及金钱等快乐的需求的充分满足视为完美生活,而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哪位哲学家完全赞同这一点。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好的品性是获得幸福生活最重要的前提。当具备尽可能多的德性(areté)时,一个人才拥有好的品性。德性有助于我们过上以幸福为目标的生活。而什么是正当的德性呢?对于有些文化来说,比如人们可以想到的斯巴达或者第三帝国,对非我族类和其心必异者的强硬与残酷曾是重要的德性。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伦理学也认可这种德性。相反,许多文化则恰恰认为仁慈和宽容才是重要的德性。所有人生来应该追求幸福的生活,这一点对于这些文化而言是无价值的,并不与某种德性相关。
亚里士多德对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对他而言,在什么是善以及哪些德性属于善这个问题中,不存在自由选择。尽管善不存在于宇宙空间之内,而是存在于每个个体的好的行为中,他依然相信一种对所有人同等有效的普遍预设。正如关于正当手段的论题,关于一个成功的人生是致力于善的,这一点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同样无须讨论。我们有向善的自然倾向。并且我们必须通过促进我们的德性来培养这种倾向。在这个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认为,关于德性的清单不是他发明出来,而是他发现出来的。缺少某些德性的人,绝对无法达成更高的生活目标。
过一种道德的生活,因此意味着一项持续致力于自身的工作,意味着对一个道德总体艺术品的塑造。最终,一个人有德性地行动,是因为他纯然是有德性的。他的品性德性,诸如勇敢、谨慎、慷慨、大度,和他的理智德性,诸如机敏、智慧、正义,得以充分发展并且彼此协调一致。他的理性判断力经过知识与经验的磨炼而变得敏锐,如此他便能实现善与公正的行为。人们了解生活,也了解自己。在这种充足经验的基础上,就能过上一种正确的伦理生活。
人尽管不是天生就具有德性,但却可以通过学习、思虑、练习和自我修养而成为有德性的人。伦理上的(自我)教育便是长期的判断力训练。人不是为了做出有用的正确决定而变得格外聪明和机智。而是,人们更应该出于正确的理由做正确的事,同时伴随着日益渐增的智慧。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的生活给人自己与世界带来快乐。至高的目标不是快乐本身。快乐仅仅是一种行为的心理回报,这种行为出于善本身(德性)而追求善(目的)。
至此,一切都是可理解的。然而,我需要哪些德性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这些德性又应该彼此处于何种比例关系?怎么评价这种理想的混合比例?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而是给出了为什么他不能确切回答这些问题的原因。因为不能在人类之外的领域对善的理念和德性予以实在的把握,我们最终也不能对其进行整理与等级划分。德性“本身”并不存在,而是仅仅存在于有德性地生活着的人之中。因此,也不能对其进行完备的描述。
德性从来不是绝对的,而总是可变的。这意味着人的慷慨、谨慎、勇敢都是可多可少的。善的理念对柏拉图来说就如凌驾于一切星辰之上的太阳或北极星,在他看到唯一的善之理念的地方,亚里士多德看到的则是善之多元性。人们勇敢的时候,人们为善;人们智慧的时候,人们为善。尽管二者皆“善”,但却是不一样的。有时候,善也会完全陷入互相冲突之中。在某些场合,当勇敢无用且仅仅是无谓的自我牺牲时,不勇敢倒更是明智之举。慷慨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但太过于慷慨则使人成为轻率挥霍之徒。在这里,有限度地帮助他人,同样更明智些。慷慨从何处起是错误的,界限在哪里,这只能在生活实践中定夺。
在某些情况下,那些基本上好的事物,偶尔也会是错误的,或者招致令人不悦的后果。理论上一直认定为“好”的东西,最终在实践中却也总得视情况而定。讲真话在理论上固然是对的。然而在生活中总有诸多情形,例如为了在不公正和危险面前保护心爱之人,说谎才是可取的。人们当然不应该杀人,但在自卫和战争的情况下为了救人则可以例外。
亚里士多德不仅了解价值与规范,而且知晓人性的和太人性的状况及弱点。因而伦理学一方面告知人们什么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也在什么是“合适的”这个问题上给出提示。在此,价值和规范要比道德机巧更为重要。一个人如果一生始终尽其所能、精明机巧地回避困难,他的生活肯定是不正确的。一种道德上好的生活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毫无疑问不是投机取巧,而在于意欲去践行一种道德上好的生活。
因此对德性而言,重要的在于恰当的尺度。因为高贵的与不那么高贵的品格特性仅仅是相对的存在。慷慨位于吝啬与挥霍这些恶习之间的中道(mesotes)。勇敢存在于鲁莽和怯懦之间的某处。德性不是极端,而是中间值。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必须在生活中不断历练道德判断力,并试图在生活中变得明智。
生活智慧(实践智慧,phronêsis)是所有德性中最重要的。因为我何时以及如何践行德性,最终必须由它来定夺。亚里士多德并未发明实践智慧这个概念。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在《斐多篇》中就已经指出,没有实践智慧的话,勇敢、正义和审慎将不能得以适当地运用。柏拉图在旧有的贵族伦理中已经发现了这个概念。当一个贵族人士了解自己以及他在生活中应当得到的财富与尊重时,他便拥有了实践智慧。以这种自信的方式成为自我确信之人,是值得称赞的品性。
为了心理上的自我确信与自我肯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排除了物质上的自信,或者说,对社会地位的注重。拥有实践智慧意味着,自信且明智地掌控生活。这种生活智慧是一种非常模糊的概念。就连为食物或冬眠操心的动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也具有前瞻性,并因此是具有实践智慧的。另一方面,他不把智慧看成一种人的本能,而是当作通过经验与知识的积累而逐渐成熟的理智德性,当作我在生活中并为了生活而培养的一种习性(habitus)。拥有实践智慧之人管理自己的生活,了解自己的愿望,反思自己的判断,继而在任何个别情况下,着眼于全局与整体上尽可能好的生活而做出决断。
生活智慧首先要面临两个不同的挑战。人的幸福由这个问题决定:我能否在与他人的共处中实现幸福。我的社会生活幸福吗?另一个问题是,我自己本身是否幸福。因为很有可能一个人尽管很有名望且受欢迎,自己却是不幸福的。在这里,只有笼统的建议和明智的原则还不够。
(本文节选自《认识世界:古代与中世纪哲学》一书,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