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一场令人迷失方向的紧急状况、一场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大灾难。对许多人来说,每天的现实是孤独的,甚至是沉闷的。它还是一场对于行动的号召,但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做的最有用的事情,就是呆在家里。新冠病毒是一种攻击肺部的疾病,但它也恶化了精神健康,导致因抑郁症、自残、饮食失调和焦虑而寻求治疗的病人急剧减少。美国领先的神经科学家、精神病学家、生物工程师、作家卡尔·代塞尔罗思(Karl Deisseroth)说,无论这场疫情往后怎么发展,“新冠疫情已经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它改变了我们所有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49岁的代塞尔罗思在他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帕洛阿尔托的房子里那郁郁葱葱、松鼠跑动的花园里进行了这场谈话。在这场疫情中,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在这里照顾四个年幼的孩子。但是,他还有很多其他想法。他一直在撰写著作《连接:人类感觉的故事》(Connections: A Story of Human Feeling)——它是一次对人类情感本质的调查。他一直在与精神病患者见面,并作为医院的紧急精神病医生值夜班,他把这些与日常工作结合起来。他的日常工作是使用微小的光纤电缆向小鼠的大脑发射激光,在此之前,他事先用光敏藻类的细胞感染了这些小鼠。然后,他会观察,当他打开或关闭单个神经元时的每一毫秒里会发生什么。
这就是光遗传学(optogenetics)的基本方法,这项技术是代塞尔罗思在2005年与他的团队在斯坦福大学代塞尔罗思实验室(Deisseroth Lab)开创的,已被广泛认为是21世纪最伟大的科学突破之一。从本质上讲,他找到了一种以难以置信的精度激活或停用单个脑细胞的方法——这反过来又给神经科学带来了一场革命。光遗传学现在已经成为独立的领域,其技术和原理在世界各地的数百个实验室中被使用,以促进人类对大脑回路和精神分裂症、自闭症和痴呆症等疾病后果的理解。这主要是通过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来完成的,例如调高或调低控制攻击性的回路。然而,其来带的可能性似乎是无穷的。今年5月,瑞士神经学家博通·罗斯卡(Botond Roska)发表了一项研究,阐述了他如何在人类视网膜上使用光遗传学原理,部分恢复了一个盲人的视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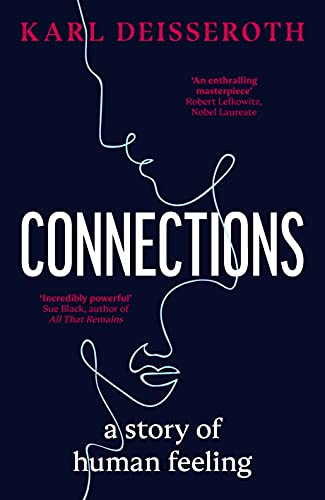
代塞尔罗思还有另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透明的大脑。2013年,他的团队想出了一种方法,将小鼠大脑中不透明的脂肪物质抽走,将所有的脑细胞悬浮在水凝胶支架中。这是一种透明的果冻状物质,可以进行非常详细的大脑成像——与标准的fMRI扫描相比,这是一个重大飞跃。这个理念是他在换尿布时想到的。
不修边幅、不紧不慢的代塞尔罗思更像西海岸摇滚乐队的贝斯手,而不是一个业界领先的科学家——而他的说法是,他所有对高科技的探索都源于他童年时想要成为一名诗人的雄心。他说:“那是我的初恋和天职——我想成为一名作家。”他曾经撞坏了自行车,因为试图在骑车时阅读杰拉德·曼利·霍普金斯(Gerard Manley Hopkins,英国诗人)的作品。“我一直对文字如何激起情绪感到好奇。它们究竟如何使我们振作起来,如何使我们沉沦,又如何成为有力量的符号?了解这些符号如何转化为感情的一条途径,可能就是研究大脑如何工作。所以我对神经科学非常感兴趣。”
但他是借由精神病学的研究最终进入神经科学的领域的。这两个领域通常被看作是截然不同的——一个是大脑,一个是心灵,但在咨询病人时获得的洞察力为代塞尔罗思的许多实验提供了灵感。他说:“任何人都可以阅读诊断手册,看症状清单,但对病人来说,真正重要的并不是这些。这让我思考:我们在实验室里可以做的,与此类似的事情是什么?灵感如何能够双向流动?”

他说,《连接》象征着自己“绕了一圈”,兜兜转转回到了他“最初和最大的爱好”——写作。这是一本具有启示意义的书。书中引用了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阿根廷诗人、作家、翻译家)和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美国非裔女性作家)的话,从黄蜂的进化到自闭症,从哺乳动物皮毛的起源到边缘性人格障碍患者的自我伤害,从音乐到痴呆症,本书随意地打破了粗暴的艺术-科学二分法。它既让人想起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英国医生、生物学家、脑神经学家、作家)所写的病历,又让人想起尤瓦尔·诺亚·哈拉里(Yuval Noah Harari,以色列历史学家)的《人类简史》,不过,代塞尔罗思说,他的情形更接近诗人兼化学家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与他的《元素周期表》。他用热爱书写文字,同时他的写作也有清晰的科学探究路线。什么是感情?它们是如何运作的?我们为什么会拥有它们?新的感觉是如何演变的?以及,为什么它们经常不适应我们的环境?

[意]普里莫·莱维 著 牟中原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 2017-4
“感觉是对世界上的信息的反应——但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它们遵循自己的轨迹,”代塞尔罗思说,“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凝聚和消失。有时我们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虽然我们对感情的物理性质连一个粗略的了解都没有,但光遗传学正开始让我们理解它们是如何、为何产生的。“我们不仅可以在数万个神经元的活动中记录下与感觉相对应的过程,我们甚至可以非常精确地直接调高和调低这些感觉的表现。我们可以调高或降低动物的焦虑、攻击性、母性、饥饿或干渴水平。而所有这些神经生物学问题都指向了‘感觉是什么’这个基本问题上。”
在很多时候,代塞尔罗思记录的病例与我们所处的奇怪时代相呼应。其中一个令人困惑的例子的主角是亚历山大,一个富有的、精神状态良好的美国人,没有精神疾病史,他的退休时间恰好是在9·11事件前后。袭击发生时,亚历山大并不在纽约附近,也不认识任何相关人员。但两周后,在希腊度假时,他开始表现出“典型的狂躁症”。他极度兴奋、睡眠时间大幅度减少(他觉得没有必要)、性欲增强。回国后,他自愿加入美国海军,并开始进行战争训练,练习爬树、瞄准,阅读军事战略。面对困惑的妻子和孩子,他坚称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
对代塞尔罗思来说,这个案例是一种寓言(顺便说一下,亚历山大的结局是好的)。“为什么存在这种对狂躁症的易感性?它是否有价值?哪怕对个人没有,那对整个社会或者整个物种呢?它是不是在漫长进化中的不同时期里曾经发挥过更多的价值?”他推测,狂躁状态“在某些方面是人类的最高表现”,是大脑中等待被跳闸的电路,也许这种状态在过去曾帮助人类应对战争、饥荒、气候危机或疫情。我们所认为的精神疾病可能是一种进化过程中的适应,或者是一种对于适应的尝试,它帮助曾经的人类社群生存下来。伟大的遗传学家西奥多西·多布赞斯基(Theodosius Dobzhansky)写道:“生物学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有意义的,除非从进化的角度来看。”
这让代塞尔罗思思索中世纪法国圣女贞德的案例——一个十几岁的女农民,和亚历山大一样,似乎也充斥着这种不恰当的狂热,但她还是在全法国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这种特殊的状态在历史上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即使它对个人来说是不适的,它仍可以给社会带来变革。”

我们很难不想到被阴谋论刺激的成千上万的人们,刺激他们的虚构紧急状况包括5G天线、疫苗接种和深层政府(deep state,非经民选,由政府官僚、公务员、军事工业复合体、金融业、财团、情报机构所组成的,为保护其既得利益,幕后真正并实际控制国家的集团)。“这就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与遥远的和较近的过去形成了对照。但背景都是错的。我们都希望在新冠疫情期间被号召采取行动。但任何个人能做的并不多。”
患有自闭症的查尔斯害怕与人接触:他在社交场合会出现恐慌发作,不能与人对视,将目光接触与“消极的主观内部状态”(即感觉不好)联系起来。代塞尔罗思能够治疗他的焦虑和恐慌发作,但目光接触的问题没有改变。然而,通过与查尔斯交谈,他能够了解到问题的“真正本质”。使他感到焦虑的,并不是眼神接触,而是通过眼神接触传达出的太多的社会信息——查尔斯发现,这些东西让他不知所措。
“对我而言,他的这番话给我带来了惊人的转变。我们把这些想法带到实验室,研究它们,甚至以比特每秒的量级,量化发生在自闭症中的某些变化如何影响哺乳动物大脑的信息处理。它以一种论文、研究或问卷调查永远无法做到的方式,非常有力地连结了所有的线索。”
对于与朋友、家人、同事有着深厚的社会关系的人来说,疫情具有很大的挑战性,这并不奇怪。有时,计算机技术将我们多层次、多感官的人际交往简化为单一的信息——喜欢,或不喜欢?计算机技术只是我们日常社会接触的一道可怜的影子。“视频会议如此令人疲惫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建立我们对对方的认识——而视频会议还往往不止一人,”代塞尔罗思说,“社会互动是生物学中最难做的事情之一。所有输入的信息,不仅仅是语言和肢体语言,还有你对对方的愿望和需求形成的认知,你必须随着对话的进行而调整这一切——这是一项巨大的信息处理任务。视频联络使之变得更加困难。”

然而,对于像查尔斯这样的人来说,远程交流也有其好处。代塞尔罗思认为,将自闭症视为对心灵的限制是错误的。“自闭症患者确实在了解他人头脑中的想法方面存在困难。但这不是一个基本的限制。他们的大脑中有某些结构和组织,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很难跟上社会互动的信息速率。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他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不实时进行的数字交流,例如电子邮件或聊天功能,可以带来巨大的好处——一些自闭症患者确实发现封城带来的慢节奏是有益的。
由于采用了数字技术,现在心理健康治疗的覆盖面比以往要大得多。“毋庸置疑,由于疫情,心理健康问题将大面积爆发,但从长远来看,我希望心理健康护理的可及性将因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而大大提高。如果说疫情带来什么好的结果,那就是这一点了。”
代塞尔罗思认为,我们应该吸取的另一个教训是,不要把我们所有的科研力量集中在狭隘的目标上——比如治疗某种疾病。“我们的本能总是让我们的资金流和人力直接与当下的那些需求保持一致。这样做的危险在于,首先,我们的认知是如此不完整,以至于这种程度的有针对性的努力通常不会成功。我们也无法做出颠覆一切的巨大、变革性的改变。”《连接》赞成思想的交叉传播和科学自由——为了科学而遵循科学。光遗传学的巨大飞跃,依赖于一位19世纪的植物学家对他在肯尼亚的一个盐湖中发现的光敏藻类的笔记:“他研究它们是因为它们很美,没有其他原因,”代塞尔罗思说,“人们永远无法预料,有一天这将使我们有能力打开和关闭大脑中的细胞,并让我们理解关于连接和映射建立我们的动机结构的因果关系。而这样的故事在科学界一次又一次地出现。”
我想知道,身处硅谷的中心地带的他是否感到沮丧,他这一代人中有那么多最优秀的人,决定把他们的智力用于为科技巨头销售在线广告,而不是改善人类的健康。他给出了一个狡猾的微笑。“这有点......让人不安。你会看到来自斯坦福大学的优秀人才走上非常有影响力的工作岗位,他们都专注于在某个小广告上获得一点更多的点击。我曾与他们中的一些人交谈过,他们也不一定觉得这很好。”

他特别关注脸书和谷歌现在对脑科学的巨大投资。“这不是利他主义。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我们,而是为他们自己做的。很多人对此感到担忧。这些公司披着公共服务的外衣,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所提供的工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即使是谷歌地图,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仍然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我们必须理解这一点。”
由于疫情带来的影响,他有时间和他5-12岁的孩子们待在一起,并很享受这些时光。“锻炼身体、解决数学难题、写诗、研究治疗疾病的方法......”他有个诞生于上一段关系的儿子,现在正在读医学院。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作为父亲的经历为他的工作注入了多少内容。他在做单亲父亲的过程中取得了光遗传学方面的突破。他称,早期与一个患有脑癌的女孩的临床接触是他工作的灵感来源,恰好,他的妻子米歇尔·蒙杰(Michelle Monje)现在是一名儿童脑癌专家。
“所有这些经历都是饱含感情的,因为我当时经历了很多事情。但直到我写完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它们与作为单身父亲的挑战和随之而来的情感风暴有多么紧密的联系。我开始发现,这是我生活中的一个统一的主题:可能走丢的孩子,可能被找到的孩子。”
的确,光遗传学帮助人们对父母身份本身有了更深的理解。“它确实改变了你。这种结构就在那里,只等开关被打开。这不是一种新的连接的形成,它就在那里,等待着被激活。”当新父母谈论孩子出生后被“重新连接”或“重新编程”时,他们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更准确。他提到了哈佛大学的凯瑟琳·杜拉克(Catherine Dulac)的研究,该研究绘制出了小鼠脑中的育儿回路。“有一种连接支配着小鼠在分离时寻找小鼠宝宝的动力,另一种连接支配着保护和照顾小鼠宝宝的动力。育儿的整体状态是由所有这些不同的部分组成的。这真是太美了、太震撼人心了。”
在整个疫情期间,他一直试图通过研究解离性状态来提出一个统一的自我理论,真正让他兴奋的是大脑的“大原则”。“任何东西都可以分为各个部分。真正神奇的,是系统的属性是如何从各部分中产生的。我们可能在几十年内都不会有真正深入的了解,但我们至少已经设定了一个进程,我们必须尽可能地推动它。”
本文作者Richard Godwin是一位自由媒体人。
(翻译:王宁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