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黄月
9月21日,《工人日报》以《狐狸的尾巴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为标题刊文怒批“佛媛”,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跟进评论,如央视网评论《这群佛媛真是欲壑难填!》、《新京报》评论《“佛媛”的“僧服”底下,爬满了炫富带货的“虱子”》,将“佛媛”乱象推至舆论聚光灯下。各大社交媒体平台迅速做出回应,9月23日,抖音共处罚利用“佛媛”形象营造人设开展虚假营销行为相关账号48个,其中永久封禁账号七个,小红书清理“佛媛”违规笔记70篇。10月1日,中国佛教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称,“佛媛”实际上是利用佛教资源牟取商业利益的佛教商业化行为,已涉嫌违反《宗教事务条例》等相关法规规定。
无独有偶,继“佛媛”之后,“病媛”冲上热搜。《健康时报》报道《“佛媛”之后再现“病媛”: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妆》在网络平台大量散布转载。该报道称,一些女性博主在社交平台上放出自己患甲状腺癌、甲状腺结节、乳腺癌、抑郁症等的文字与照片,她们有着“精致的住院照,生病不忘化妆”,有时还会带货,比如疤痕修复贴、保健品等。
媒体和公众的口诛笔伐还在持续中,事件出现了变化,媒体报道配图涉及的数位当事人在社交媒体上做出澄清。微博博主@张吉晶-cat发布病历报告和律师声明,表示《健康时报》报道错误使用其个人照片,对其装病带货的描述与事实严重不符。另一位当事人表示,自己拍照仅仅是记录治疗过程,未曾想照片会被盗用并因此遭到网暴。微博博主@零十二画生澄清说她拍照的地点是燕方归客栈,因觉得院落好看就拍照在小红书上分享,却被盗图构陷为“佛媛”。在这几位当事人身上,病媛没有带货,佛媛也不在寺院,反倒是盗用她们照片的评论者有借机赚取流量的嫌疑。

“媛”原本是一个寓意美好的字,《说文》和《尔雅》对这个字的解释是“美丽的女子”,然而近两年来,这个字不断遭遇意义解构。在“拼单名媛”引发的热议沉寂一年后,“媛”被挂上各种定语,在整治网络环境的大势下将批判的矛头直指年轻貌美、在社交网络上活跃的女孩。诚然,社交平台上确实存在违规网络账号进行虚假营销等非法牟利的行为,但从上述几位当事人的澄清来看,“X媛”是否是一个已成气候的现象,甚至说主流舆论批判的这个靶子是否属实,依然难下定论;另外,在网红经济的大背景之下,对网红人设和带货行为的“公愤”,针对的究竟是虚假营销行为,还是反映出了更深层次的偏见,也是一个亟待辨清的问题——为何年轻女性吸引了不成比例的关注度,并要承受更多的道德指控?
中国历史上女性与佛教的关系是怎样的?

某主流媒体批评佛媛“在宗教场所大肆摆拍,搔首弄姿,缺乏起码的尊重,看似与世无争,实则物欲横流”,不过从历史上看,宗教场所实际上是少数女性可以自由出入且不会遭遇过多非议的公共空间之一。美国塔夫茨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许曼在研究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儒家伦理本身存在不少松动矛盾,为女性在实际生活中造就了自主空间,宗教生活即为一例。
宋代是中国宗教组织的发展和繁荣期,经历了广泛的商业化和俗世化。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佛教自唐代起从出世转向入世,新禅宗的思想在宋代已传遍整个中国社会;新道教也在宋代蓬勃发展。佛教、道教和其他地方宗教在这个“有利可图且充满活力的环境中”相互竞争,女性积极参与宗教活动,扮演传教者、朝圣者、布施者等各种各样的角色。
对于宋代福建的女信徒而言,宗教是一种嵌入闺阁日常的生活方式。在家庭内,她们能与父母、丈夫、兄弟姐妹和子女讨论宗教问题,学习和操演宗教仪式的家庭程序,并与来自其他家庭的男性或女性访客见面交流宗教知识。同样重要的是,她们能够走出家门,进入由佛教、道教和当地大众宗教构成的错综复杂的方外世界,成为繁荣的宗教市场中引人注目的客户。女信徒经常光顾当地庙宇,参观寺院活动,为庙宇提供各种物质和人力资源,以显示虔诚,寻求精神慰藉和祈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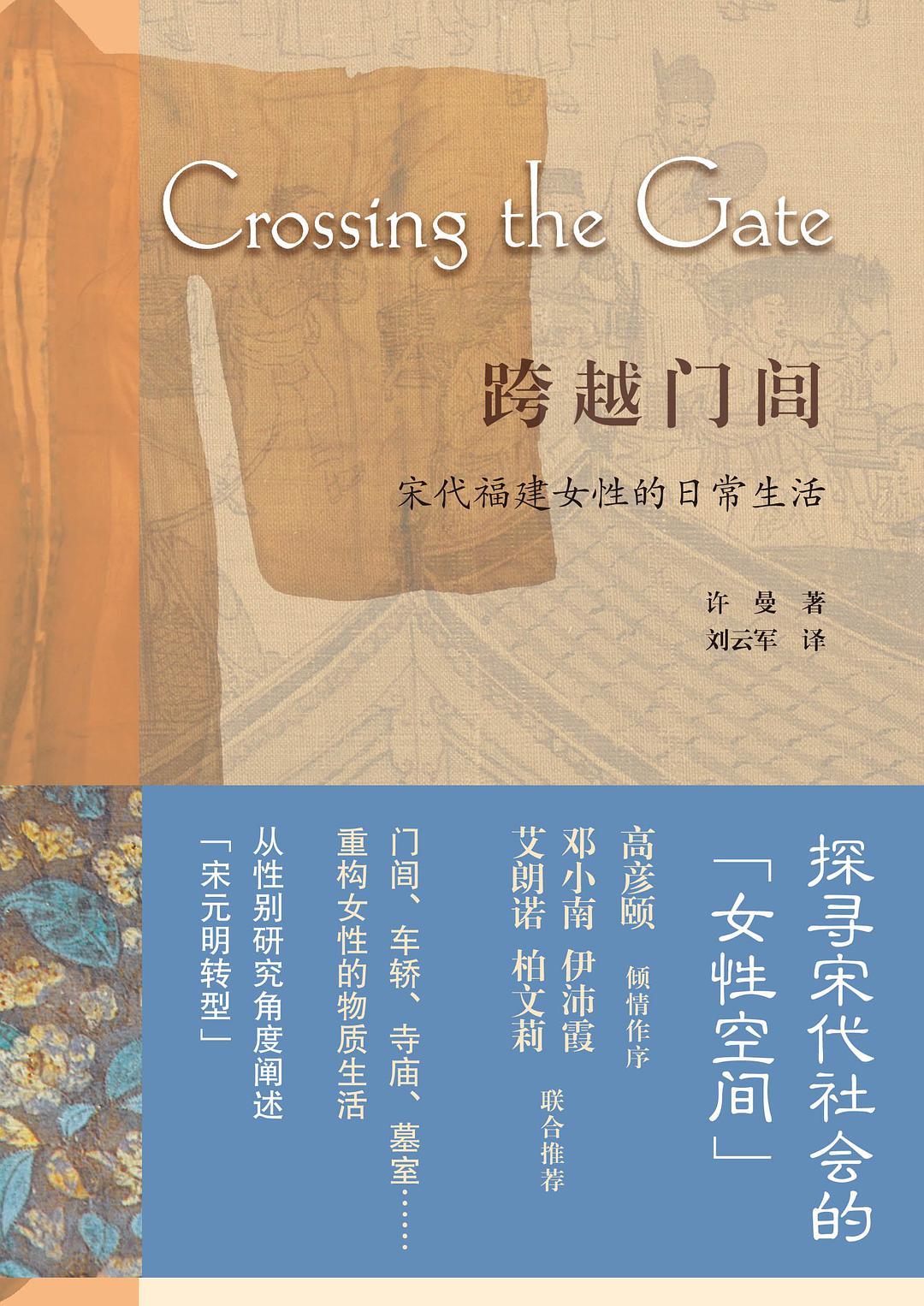
许曼 著 刘云军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9-6
许曼指出,宗教人士实际上也非常乐意为女信徒提供服务,以换取经济上的资助,从而在宗教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获得更高的声望和更多的潜在客户。也就是说,宗教其实无法完全隔绝俗世的烟火气息。史料显示,福建的女信徒去寺庙参加讲经课,观看并参与宗教仪式,并不断为宗教组织提供物质和金钱捐助。根据个人和家庭经济水平的高低,她们的布施形式多样:有人会向寺庙赠送带有宗教图案的刺绣等手工艺品,有人会雇人制作宗教物品,有人会购买度牒,财大气粗者甚至会布施金钱和土地用以建造宗教建筑和寺观物品。
福建地方寺庙的发展非常依赖于女信徒的布施,根据南宋名臣梁克家(1128-1187年)的记录,“(福州)富民翁妪,倾施貲产以立院宇者无限。”这意味着,年长的女信徒往往拥有掌管家庭财产的权威,且能够将家庭财富布施给庙宇,以为家庭祈福的名义发展她们的精神追求。朱熹批评福建僧侣一看到女性就上前攀谈,这位理学大儒的抱怨表明,与地方女性沟通,并寻求她们的布施,在福建的宗教神职人员当中是一个普遍现象。宋代女信徒积极布施的物证至今还能在一些福建庙宇中找到,比如在福建最大的佛寺泉州开元寺,拜庭中轴线的两侧矗立着两座宋代宝塔,其中一座保存了南宋初的铭文:
“右南厢梁安家室柳三娘舍钱造宝塔二座,同祈平安。绍兴乙丑七月题。”
根据历史学家余英时的分析,从韩愈至宋代的新儒家都全力排斥佛教——新禅宗虽然有了入世转向,但从根本上来说并未改变否定“此世”、舍离“此世”的基本态度,因此与儒家最重视的“事父事君”人伦纲常有所龃龉——那么宋代的男性士人是怎么看佛教对女性的吸引力的呢?许曼用一句话来概括,“无论精英人士多么真诚地为一个没有佛教的世界而努力,他们都认为女性的宗教空间是相对独立的,在这一点上,男人不应该强行干涉。”

许曼指出,福建儒学复兴的许多关键人物都对佛教和道教有很深的认识,亦吸取了佛道两家的思想用于儒学的重新阐释,坚称儒学是实现自我完善、履行家庭、社会和国家义务的唯一恰当途径,他们一方面希望男性能够远离佛教和道教,但另一方面却对女性的宗教信仰和实践抱有更宽容的态度。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学者们意识到允许女性拥有宗教追求的益处:佛教能让女性变得安详沉静,缓解家庭中的紧张关系,有助于实现儒家价值观推崇的家庭和谐;另外,女性的宗教信仰也能够使地方社区受益,比如她们开展慈善活动救济贫民。
当然,正如朱熹的批评所流露的,宋代精英士人也不可避免地对女性参与宗教活动有所担忧。参观寺庙让女性得以与家庭以外的非亲属男性接触,挑战了儒家提倡的性别区隔原则,她们与男信徒和僧道之间的交往引起了士人的特别焦虑,这种焦虑在明清儒家学者中展现得特别明显。即便如此,许曼发现两宋时期代精英士人对女性参与家外宗教活动的态度是宽容的,虽然时不时会有地方官员推出禁令试图打击女性对宗教活动的热情,但这些努力往往难以持久。直至明清时期,在福建和许多其他地方,女信徒对家外宗教活动的兴趣和参与从未消退。
进入现代社会,女性“跨越门闾”的合法性已无需论证,宗教信仰也被广泛视作个人自由而对两性一视同仁。如果宋代就有“佛媛”的说法,她们被批评的理由大概率是因为僭越了两性交往原则;而今,“佛媛”因为截然不同的理由被批判,体现了我们时代因女性在社会中应然和实然位置出现偏差引发的一种全新的焦虑或不安。那么,这种焦虑或不安又该作何解释呢?
网红经济何以掀起道德焦虑?
“佛媛”“病媛”争议引发大量网民参与或围观的另一个背景是网红经济的崛起,这些女性受到指责的原因之一是“炫富带货”。带货,为什么这么招人恨?我们也可以试着在历史中寻找答案。
随着90年代消费革命的兴起,当代中国被逐渐整合到全球消费资本主义文化中。根据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现代美国文化史学者威廉·利奇(William R. Leach)的定义,这种文化将获取与消费标榜为实现幸福的手段,崇拜新事物,推行欲望民主化,把金钱作为衡量社会所有价值的主要尺度。在倡导这样一种文化的社会中——即消费社会——人们专注于消费、舒适与安康、奢侈生活,商品极其充裕,消费者喜新厌旧。根据利奇的考证,美国的这一文化转向完成于1880年至1930年。在20世纪的剩下时间里,全球的许多角落都在向消费资本主义文化靠拢。

在利奇对美国消费主义文化史的研究中,与本文主旨相关的一个发现是,时尚的概念被发明出来,迫使人们为追逐潮流而不断购买和丢弃,而时尚产业也为女性开辟了新的社会活动空间——时尚业雇佣了大量女性,其中的少数高薪者以“时尚采购员”的身份脱颖而出。20世纪初,美国各大百货公司都雇佣女性时尚采购员,她们对流行趋势的敏锐嗅觉对其雇主的盈利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采购员中的佼佼者甚至享有明星般的地位,比如梅西百货的采购员莉娜·罗本娜(Lena Robenau)。她曾被当时的行业期刊称为“零售女王”,频繁前往法国巴黎等地采购,商店员工会集体为她的海外之行送行。有时候,这些女性采购员的出发还会被拍成电影。
而今,消费社会的运作机制已臻于成熟,数字时代为商品营销插上了翅膀。在移动互联网高度发达、互联网行业狂飙突进式变革的中国,网红经济更是成为了一个瞩目的新现象——意见领袖(KOL)或影响者(influencer)在这里获得了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称呼“网红”,他们以贩卖生活方式的形式在社交网络上承接商家软广,将社交网络与电子商务结合,助推消费。网红经济利用了消费心理学中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信赖(他们因不代表某个公司的利益而显得更为可信),让(看似)中立的网红与消费者建立更强的情感联系,从而获得带货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网红的带货优势是一把双刃剑——他们的可信度建立在中立和无特殊诉求的基础上,一旦他们展现了较强的(带货)目的性且尽力矫饰这一点,便容易在公众面前留下道德可疑的负面印象。

网红与品牌一样,需要在浩繁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利基市场,通过某个鲜明的标签来建立人设于是成了最便捷的做法,而潮流的转瞬即逝(潮流既可能是指时尚风潮,也可能是指文化思潮)则让人设不断推陈出新。以“佛媛”为例,在这个标签引起主流舆论注意前,礼佛、抄经、喝茶等行为并非异端,在“国风盛行”的当下,它们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有文化有品位”的象征。公众号“知著网”刊登的一篇分析文章指出,热衷于礼佛的人天然带有某种“物质生活丰饶与精神世界平和”的双重想象,这是“佛媛”标签可欲的出发点。如果“佛媛”未被主流舆论绞杀,它不过是一个彰显差异的人设标签,是人们每日在手机屏幕上草草划过的数字化人格中的一种;但“佛媛”因一部分群体通过社交网络提前透支了想象力红利和信任额度而遭到污名化。我们目前难以定论以“佛媛”为人设牟利的网红有多少,但可以确定的是,“佛媛”污名化的恶果要由所有追求佛教信仰慰藉、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相关话题的年轻女性共同承担。
网红经济的野蛮生长带来了问题和焦虑。网红经济的高超营销手段不断蛊惑人们、煽动起不必要的消费欲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间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值服务,而自己则沦为资本逐利的工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此有了反思。“佛媛”一说能够挑动神经,恰恰在于其表面无欲无求实则物欲横流的强烈反差,激发了人们的厌恶。另一方面,网红经济中一直存在虚假营销、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比如“带货一哥”辛巴曾因售卖假燕窝遭到行业广泛讨论和监管重罚,罗永浩也曾经带货“翻车”,其影响的恶劣程度不言而喻。然而,往往是在针对女性网红的抨击中,这些问题的严重程度被放大为群体性现象。从“佛媛”“病媛”到仍在出现的各种其他“X媛”,此类指控呈现泛化趋势,值得深思。
“X媛”偏见从哪里来?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X媛”成为众矢之的是偏见使然。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指出,人有产生偏见的倾向——泛化、概念化和分类是人性本能,这能帮助指导我们尽快适应日常生活,但人们也因此容易形成非理性的分类,对经验世界过度简化。个人价值体系是一种尤其使我们倾向于做出毫无根据的预判的分类,消极的偏见往往是我们自身价值体系的反射,我们有多么珍视自身的存在模式,就会以多大的强度贬低或攻击那些看上去威胁到我们的价值观的事物。无论是积极的偏见还是消极的偏见,都容易让我们形成刻板印象——它反映了某种夸张化的群体特质,将我们对某一群体的喜爱或厌恶合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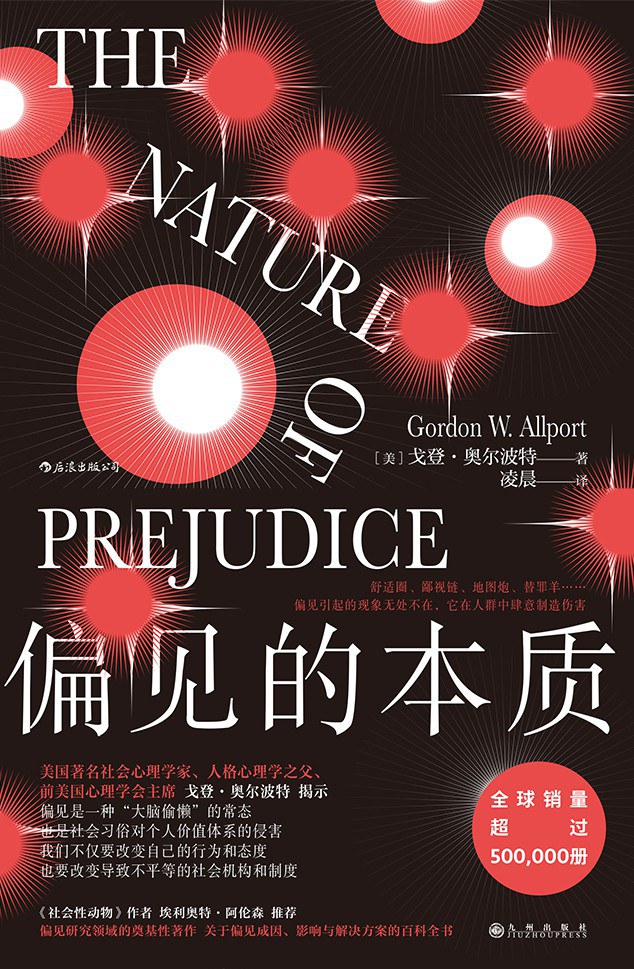
[美]戈登·奥尔波特 著 凌晨 译
后浪丨九州出版社 2020-10
奥尔波特指出,广泛性的社会偏见与社会结构和文化格局息息相关。当社会的垂直流动性(每个社会成员被允诺潜在平等,被鼓励通过努力和好运实现向上流动)给社会成员带来激励与恐慌,特别是在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加速崩坏的情况下,那些对个人境况不满的人更容易对社会弱势群体产生偏见。“伴随着对未来的不可预测性而来的焦虑感增加,使得人们倾向于将恶化的处境归咎于替罪羊。”在社会失范时期,人群之间的利益冲突和被感知的竞争会被夸大,不满之人由此产生敌对心态和攻击冲动。奥尔波特认为,为了保持社会的核心稳固,大多数社会都会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鼓励公开表达对特定“女巫”群体的敌意,以此充当公众发泄情绪的安全阀门。15世纪的欧洲社会和17世纪的马萨诸塞州公开鼓励人们猎巫即为先例。
某种程度上来说,“X媛”是阶层流动焦虑下产生的偏见,这在一年前的“拼单名媛”争议中已初见端倪:“拼单名媛”的冒犯性在于用拼单消解了消费符号的稀缺度和区隔属性,僭越了社会等级秩序。一年以后,这种越轨指控几乎原封不动地指向了“佛媛”和“病媛”。利用本来纯良无辜的“人设”带货牟利遭到抨击,除了涉嫌虚假营销等非法行为以外,更重要的是戳中了人们对网红经济创造的“新贵”的敌视——网红经济让一些出身普通的女性可以直接用美貌和喜爱度对接资本,打破门槛实现阶层跃升。抛开这个原因,我们几乎无法解释为何不直接称从事非法流量生意的女性为犯罪者,而是发明了“X媛”这个在道德情感上充满暧昧的标签。
“佛媛”“病媛”的舆论发酵以及数位当事人的澄清提醒我们,大众传媒在促成和加深刻板印象方面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此媒体应当对发明标签保持克制和谨慎,特别是在标签被错误地贴在社会弱势群体(比如年轻女性)头上时。2016年,诺顿安全公司的一项研究发现,在1000名接受调查者中,近半数在网上经历过某种形式的辱骂或骚扰,其中30岁以下的女性所占比例高达76%。许多研究发现,女性会为了避免受到谩骂而选择在网络上隐蔽自己。与此同时,网络语言暴力会对受害者造成实际伤害,比如经历焦虑、压力、恐慌、缺乏自信和产生无力感。当“X媛”的指控泛化为无差别攻击,女性将在自我审查的压力下丧失在网络上合法表达的自由,这比某几个树人设带货的网红大V更值得我们警惕。
参考资料:
【英】塔比·杰克逊·吉,弗雷亚·罗斯.《女性主义有什么用?》.译林出版社.2021.
【美】威廉·利奇.《欲望之地:美国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美】戈登·奥尔波特.《偏见的本质》.九州出版社.2020.
许曼.《跨越门闾:宋代福建女性的日常生活》.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余英时.《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水中月影镜中面,“佛媛”污名从何现?》,知著网
《在一个只能从消费中获得须臾慰藉的时代,我们应当指责的,绝不是一群虚荣的女孩》,T China
《消费无止尽:说好不再剁手,怎么转头又迷上了直播购物?》,界面文化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