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7期主持人 | 林子人
11月下旬我们才聊过上海迪士尼乐园爆红的全新原创角色玲娜贝儿,短短两周时间她就“塌房”了。近日,一位网友分享了自己去迪士尼乐园过生日与玲娜贝儿互动的视频,称自己排队了两小时,玲娜贝儿却在互动合照时摇头晃脑显得没礼貌,而且疑似把比划的爱心扔地上踩了两脚。这则30秒短视频迅速引发关注,随后“玲娜贝儿下头”的话题冲上热搜,评论里充满了对玲娜贝儿演职人员的不满,一些网友甚至用充满物化和蔑视的词语——“内胆”——来形容扮演玲娜贝儿的工作人员。
随着话题发酵,“玲娜贝儿下头”的理由也越来越多,没作品没内涵、怼游客没礼貌、对男性游客和女性游客区别对待……之前那期聊天室里佳靖说“随着玲娜贝儿的走红,她的面貌也会变得越来越模糊”,很讽刺地预言了现状。不过我觉得所有指责中最显著也最值得深思的一个理由是,游客是付了钱来迪士尼乐园的,就应该享受到与之相称的优质服务,没能满足游客的愿望(比如在生日当天获得特殊优待),就是玲娜贝儿(演职人员)的错。在这些人看来,袒护玲娜贝儿的粉丝都是莫名其妙地“与迪士尼/资本共情”,他们仿佛全然忘记了扮演玲娜贝儿的工作人员也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会疲倦、会脆弱、会不耐烦的打工人。
感觉在中国,“消费者是上帝”是一种耐人寻味的心态和社会现象。它有一种进步性的一面:在市场经济及其法律机制仍未完善的时代,消费者确立自我身份和权利的意识日益增强,在横行假冒伪劣商品和糟糕的服务面前,人们越来越不惮于动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一种由商业催生的个人权利意识,客观而言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进步。
但另一方面,“消费者是上帝”又似乎在演变成一种“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的傲慢。花了钱,消费者的一切愿望就应该被满足——当它成为了某种具有绝对正当性、不容辩驳的价值观,我总觉得现在的很多现象在冲击我自小以来接受的人情教育,比如礼貌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前两年社交网络上有过一场关于“要不要对上门的外卖员说谢谢”的争论,我当时看到觉得简直刷新三观,这都能被争论吗?在我看来,“消费者是上帝”是一种极端强调自我的观念,许多社会摩擦由此产生。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观念出现了泛化,在自己看不惯的人和事面前,人们越来越不愿意克制和宽容,随时随地表达愤怒和不满变成了一种下意识反应。
01“消费者是上帝”的底层逻辑:消费者的话语权被无限拔高,服务者日益被动卑微

赵蕴娴:我觉得这句话里的“上帝”换成“巨婴”比较贴近现实。说“消费者就是上帝”,大致有两层意思,一是消费者怎么样都是对的,二是消费者应该得到一切。前者意味着消费者可以无理取闹,资本要的不过是他们口袋里的钱,至于无理取闹所造成的伤害,就交给服务人员来承担。后者的典型案例,发生在一些烤肉和火锅店。刚上大学的时候去了一家烤肉店,我震惊了,桌子上有好用的烤炉和烧烤工具,竟然也要专人来烤,不就是刷刷油翻翻肉吗?就算有一点失败,吸取教训不就好了吗?总之,这在我以前的经验里是没有的。当时我十分局促,有种被人“伺候”了的感觉,体验非常差,但我和朋友要求自己烤,服务员又显得为难,旁边人也觉得遇上了土鳖。现在一些火锅店下个蔬菜虾滑也要由服务员来代办,商家宣称这是“宾至如归”,让人人都能平价享受“贵族”待遇,但除了制造紧张感以及给服务员增加不必要的劳动,我看不出这种做法有何意义。
陈佳靖:在餐饮业,把“消费者是上帝”这一理念践行到极致的莫过于海底捞,这也是我近几年几乎不再去吃海底捞的原因。众所周知,海底捞的服务丰富周全到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我第一次听说很多人去吃海底捞是为了顺便做美甲时真的感到很困惑,美甲和火锅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后来才明白这是商家为了让顾客在排队时也不浪费时间的一种补偿措施,由此衍生出来的项目还包括擦鞋、按摩等等,这些显然都超出了一家火锅店的业务范围。用餐过程中的服务就更不用提了,几乎每隔十分钟就会有服务员过来帮你加水添菜整理桌面,询问你还有什么额外需求,好像如果没做什么就是TA服务得不够好。我曾经目睹有人在海底捞过生日,一大群服务员像排练好一样围上前送蛋糕、送祝福,集体唱生日歌讨客人欢心,那种情形也许会带来惊喜,但也确实让人尴尬。我会担心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并非发自内心,在面对顾客或商家提出的各种奇怪要求时,他们是否也会感到为难,想说“这不是我们该做的”却又无法拒绝?

说到底,消费者和服务者只是供需关系,不该有所谓的地位高低之分,但“消费者是上帝”这一说法却把消费者的话语权无限拔高了,也将服务者推向了完全被动、卑微的一方。这里的底层逻辑是“谁买单谁说了算”,消费者甚至可以去自行界定服务的标准、内容和范围。这也是为什么玲娜贝儿这么快就“下头”了——游客们在一个人偶身上预设了太多溢出范围的消费期望,却忘了那个人偶之下也只是一个普通的服务人员,不可能也没必要满足所有附加在玲娜贝儿身上的“人设”。
叶青:查了一下,“消费者是上帝”这句话居然来自一位日本歌手,且他的原意是指自己像对待神明一般对待听众,结果却演变为一句服务业最有名的口号。在有小费文化的国家,消费者是“金主上帝”我尚可理解——如果服务人员提供了令消费者满意的服务,有机会拿到高额小费。可国内大部分的服务场所是没有小费文化的,那么在我的理解中,对服务人员而言,他们的首要目标就变成了完成老板或公司的要求,比如送餐、泊车、领座等等,其次才是满足客人的要求。毕竟这对他们来说属于额外劳动,拿不到对应的报酬,将心比心,谁愿意天天无下限地伺候一个不给钱的上帝呢?
《康熙来了》曾经办过好几次“奥客”(闽南语,指那些很麻烦、讨厌的客人)主题的节目,看完那些服务人员的吐槽后,才知道原来很多我以为理所当然的请求,其实并不在服务人员的工作范围内或是会让他们那么不高兴。自己居然不知不觉地当了那么多次“奥客”!这之后我都会尽量避免麻烦他们,因为就像蕴娴说的,被伺候的感觉也没那么好——服务人员在桌上忙手忙脚时,往往是一顿饭中最尴尬的环节。和朋友说话也不是,帮忙也不对,又不能立马开吃,只好彼此呆坐望着烹饪中的食物。还是让我们自己来吧!
02 道谢文化的缺失:无视服务人员,是因为我们有了更便利地无视他们的条件
赵蕴娴:大学去台湾地区交换了半年,回来的时候“谢谢”二字已经常挂嘴边。虽然之前去餐馆也会对服务员说谢谢,但远没有那么频繁。在台湾地区,接到菜单时说谢谢,服务员上餐具茶水时说谢谢,每上一道菜也要说谢谢,总之,只要服务员为你提供了服务,都应该看向对方轻声道谢,最后出门时还要说声谢谢。比起餐厅里面的谢谢,更让我印象深刻的道谢发生在便利店和巴士上。一般大家在大陆的便利店买东西,几乎不会和店员有关收付款以外的对话,有了二维码支付后,顾客更是连问价的一步都省了,乘坐公共汽车也只管上下。但在台湾地区,便利店结账完后顾客总会对店员微笑说一声谢谢,如果你排长队结账,道谢之声不绝于耳,巴士下车时更是如此,老人小孩,叽叽喳喳的国中生,男人女人,都会对司机说“谢谢”,此起彼伏连成一片,好听极了。
你可以说这种道谢文化有点像条件反射、有点机械化了,比如我现在被别人不小心踩到脚,嘴里蹦出来的经常是“谢谢”而非“没事”,但也正因为这样的社会习惯,服务人员不再隐形,不再沉默无声。有些人会以“提供服务”和“享受服务”来划分人群,认为司机、服务员提供服务是他们的工作本分,而自己花了钱就理所应当地去享受,购买一个人提供的服务和购买一件商品一样,是种金钱交易,不需要温情脉脉。这种观念之下,司机和店员从有血有肉的人变成了某台机器的外延,想想我们坐公交的时候,是不是经常忽视司机呢?整个车变得像无人驾驶的幽灵车一样。我认为道谢文化是对这种观念的抵抗和拆解,它重新定义了服务业中消费者和劳动者的关系,也重新定义了工作——工作不止关乎金钱,它还有为社会福祉付出、相互关怀与照料的部分。因为“谢谢”所包含的看见与尊重,劳动者的尊严得以维持,价值得到肯定。通过不断地说谢谢,每个人都会意识到日常生活的运转有赖于许许多多不同职业者的劳动付出,尤其是中下层的蓝领工作者。

姜妍:说到在台湾地区的经验的话,我也深有感触,对我的台湾朋友们来说,来到大陆的一些经验反而成为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种反差。比如说我有一位朋友到了北京没两天就学会了在地铁里面要下车的时候冷着脸对前面的人说“让让!”这种巨大的差异化经验让她觉得非常有趣。还有一位台湾的诗人讲起90年代初第一次来北京在一家国营餐厅吃饭,因为椅子不够,和服务员讲,对方以他问询的几何倍音量回敬道:“你不会自己搬啊?!”
我们在对待他者的时候,不管对方是谁,为我们提供服务的人也好,老板也好,清洁工也好,当然都应该保持基本的教养,把礼貌用语挂在嘴边,这和是消费者还是打工人的身份无关,是和一个人的自身素质有关。
另外如果把服务行业当成一个工作来看待的话,这个工作是不是也需要一种衡量其好坏的标准?比如媒体从业者我们需要看稿件质量,那评判一个从事服务行业的人的工作好坏,我们依赖什么?我们做好自己作为消费者的部分的同时,假如遇见了我们认为对方不够敬业的表现时,应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讨论空间的。
董子琪:我想将这个问题倒过来想,为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无视服务人员?是不是现在有了更加便利的可以无视他们的条件,像是餐馆里有扫码点单、便利店有自动结账,连优衣库都不用人工结算了,我都怀疑这些系统设置的目标就是为了鼓励人们忽视服务人员,鼓励顾客相信二维码而不是面前的生动面孔,这难道不是一种对顾客和工作人员的双重驯养吗?每次进到那种明明有服务员但还需要扫码的咖啡店,我都会奇怪自己和服务人员的身份和关系,我们是什么机器人吗?连招呼都不打,只能通过代码交流?交易以外的礼仪和表情一概没有,我们需要吝啬到这个地步吗?
想起托卡尔丘克小说里讽刺地写,每过一代,仆人的脸就更难识别,而且据科学研究,仆人是不需要脸的。大概是因为没有脸、缺少情感特征的人让顾客可以更肆无忌惮地将交易只视作交易,即使有点暴力性质滥用了交易关系又有何妨?所以最稳定地符合“顾客是上帝”需求的服务人员一定是机器人、二维码还有自动点单机器。只是我也奇怪,酒店里哼着歌曲送菜的小机器人为什么发出儿童般的声音?这也是为了想象服从的感觉吗?实在是太诡异的发展了。

顺着这一点,又觉得有时便利也潜藏着一种霸凌的风险,立刻满足直达目的感觉特别美好,但是以蔑视中间环节为代价。像是《我在底层的生活》里女作家扮作客房服务员亲身体验清扫工作,才明白是谁在擦净了马桶、叠好了被子、拖光了地板,而被教导享受酒店便利优雅生活的顾客是不会看到客房人员身影的,或者说正是在忽略她们肌肉酸涩、肢体僵硬的基础之上,他们才能安心享用高价购买来的完美体验,这是一种对心安理得的驯养。
说回玲娜贝儿, 我看到不少网友在讨论贝儿时为其辩解说,是这个“内胆”不好,所谓“内胆”就是扮演贝儿的工作人员啦。好家伙,托卡尔丘克还没想到,仆人不仅可以没有脸,还能成为“内胆”吧!称为“内胆”既区分了卡通角色与工作人员,又表达了用过即弃的消费态度,真是伟大的发明创造。便利的、可以随意替换的内胆,当然是可以立刻消失的,因为它从来没有被看见过。
林子人:说到服务人员的“隐形”,去年我采访上海交通大学的社会学家沈洋,她曾在上海某餐厅以服务员的身份做过一段时间田野调查。她提及自己亲身体会到的一起服务员“隐形”事件:有一次沈洋爸爸和他的朋友来餐厅吃饭,沈洋向其中一位她认识的叔叔打招呼,那个人对她视而不见地走掉了。沈洋跟我说,“因为阶层的差异,低阶层的人就会变得不可见。”还有一次,一位中年男性客人当着沈洋的面大声说,“不知道这个人听得懂上海话伐,怎么像乡下人一样。”多么讽刺,仅仅是因为服务员的身份,一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女学者就会被无视、被讥讽,这明明是对现有社会分工下需要服务他人的“下位者”的无意识偏见,却偏偏要强装成对“下位者”内在品质的质疑。
03 消费者至上心态的外溢:个人权力侵蚀社会凝聚力,造就一个越来越冲动的社会
潘文捷:“消费者是上帝”这句话是彻头彻尾的自恋。人们用消费的方式来标榜甚至炫耀自己的身份,以为占有了某个商品、某个符号,自己就是那样的人。但是说到底这也只是占有,而不是成为。当然这样的人也会倾向于把自己和别人都当作一种商品,明码标价了。他们想要得到自己所在群体的认可,也会根据交往对象的阶层不同来区别对待别人。
跳出消费者自身的自恋视角,“消费者是上帝”这句话更加是谎言了。先来看看消费者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吧!在广告宣传和物欲刺激之下,人的欲望被放大到远远超过自己的需求。在城市里,欲望的放大让人们变得越来越忙碌。波士顿学院社会学教授朱丽叶·斯格尔在《过度劳累的美国人》一书中提出了“工作-消费循环”,日本经济学家森冈孝二在《过劳时代》里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人们用物质消费的刺激取代空闲时间来消解自己的欲望,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不仅不能持久,还会推动欲望不断升级,人们为此再增加劳动时间,进一步削减空闲时间。而没有进入工作-消费陷阱的人,不是不会落入,而是无力落入。如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的,被排除在消费之外的“新穷人”由于没有购买力,在物质与精神上都被抛弃。一种对消费至上的无个性的认同树立起来——钱,更多的钱,是参与那个世界所必须的。请问,在这种时刻,真正的“上帝”,真正掌控者一切的,还是消费者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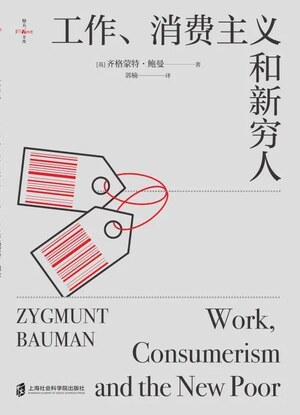
[英]齐格蒙特·鲍曼 著 郭楠 译
燧石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1-9
黄月:在纯粹的消费场景之外,更可怕的或许是消费者至上心态的外溢、滥用和对其他人际关系形成的侵占。学生交了学费,师生之间就因此成为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了吗?病人付出金钱,与医生的关系就只是购买医疗服务吗?订阅、订购或打赏了媒体内容,就获得了对其内容或观点的主宰或限制的权力吗?有观看过表演、比赛或购买过某团体的周边产品,某位偶像、某志球队或某一团体就不能发表与你相忤逆的言论了吗?在教育和照护的含义中,到底是什么或者有多少可以被消费所限定与衡量?对于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消费到底能够决定多大部分,又会造成何种扭曲?
如果消费了即代表你要听我的,那么金钱就等于权力和正义。这个绝对的画等号关系,难道不正是漫长的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人所鄙夷、所恐惧、所反对的吗?
林子人:美国记者保罗·罗伯茨(Paul Roberts)在《冲动的美国:被撕裂的社会和被放纵的民众》一书中提出的观点对我理解“消费者是上帝”这个观念带来了更深入的思考——在罗伯茨看来,是消费者的心态让美国社会内部越来越缺乏妥协、相互理解和合作精神。随着社会日益接受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社会中的个人变得更加个人主义,从而更不愿意支持传统的集体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当“消费者”成为一个人实现自我、满足个人欲望、确立社会地位的最重要身份时,他们往往会表现出愚蠢自私的行为,从而损害整个社会的利益。

[美]保罗·罗伯茨 著 鲁冬旭 任思思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21-4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社会能够呈现出今日的繁荣,是因为人类发明了种种制度、习俗和意识形态来确保合作共赢,无论在哪个社会里,个人权力都会被制约,个体都需要履行对集体、对他人的义务。然而这个历史常态已经被消费者社会打破了。如今,消费显得无所不能,经济体系已经能够在各个方面满足个人欲望和各种个性化需求,这种自由给人们带来一种“只要我有经济实力,我就无所不能,我就能立刻让我不喜欢的人和事消失”的错觉。这种巨大的个人权力在侵蚀社会凝聚力的基础——耐心、妥协、同情、理解和自我牺牲——造就了一个越来越冲动的、不愿为他人的感受和福祉着想的社会。虽然罗伯茨描述的是美国的情况,但我们亦应当对类似趋势保持警惕。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