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徐贲做客宁波,与羽戈对谈“什么是良好的公共生活”。涉及的话题有公共生活、说理、教育、犬儒等,也谈及“钱杨”话题、公共知识分子及其责任。本文为其演讲实录的节选。
如果别人说你是一位“公知”,你接受吗?
徐贲:我能够接受的。按照布鲁姆的说法,不公共的知识分子是不可设想的。余杰评论钱钟书的时候用的是“知道分子”。我们现在的汉语当中,知识分子这个词重在“知识”上。但是“知识分子”并不只是“知识”加“分子”。“知识分子”是有特定含义的,不是中国原有的一个词,是一个需要界定的概念名词。
简而言之,知识分子指的是对社会和公共事务有独立、批判思考并发出良心声音的有识之士。现在论述知识分子,十有八九是用系谱学的方法界定知识分子,一个是来自俄国,一个是来自法国。但是,我们平时以知识分子看待什么人或哪些人,经常是经验性的,并不追溯得那么久远。我认为,在一般的讨论里,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
传统中国的士大夫,他们非常有知识,但是他们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我们今天所说的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其形成是较迟的。人们最早提出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功能并不是从有了读书人开始的。按照现在一般的看法,批判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故乡是法国,起源于左拉发表《我控诉》这个事件。在此之后,才有了知识分子的说法。知识分子只有发挥了公共作用之后,这个身份才得以确认,而不是说有人开始念书,有了某种学位文凭,或者开始很有学问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知识分子了。
现在我们讨论知识分子,碰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是知识分子。我以前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大家都说念了大学就是知识分子。我一位朋友是文革后第一批考研录取的,他对我很得意地说,“从此我就是高级知识分子了”。第一批研究生是没有学位的,连个硕士头衔都没有,现在看,不算什么高级知识分子。再追溯到更早一点,比如回到革命时代,延安时代,有个初中或者是高小的学历就是知识分子了。在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恐怖统治时代,只要戴眼镜的就是知识分子,许多人还因此遭到肉体消灭的命运。文革中,叫臭老九,那时候只有党的知识分子,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谁也不敢妄想当什么公共知识分子。但那些不是我在这里说的公共知识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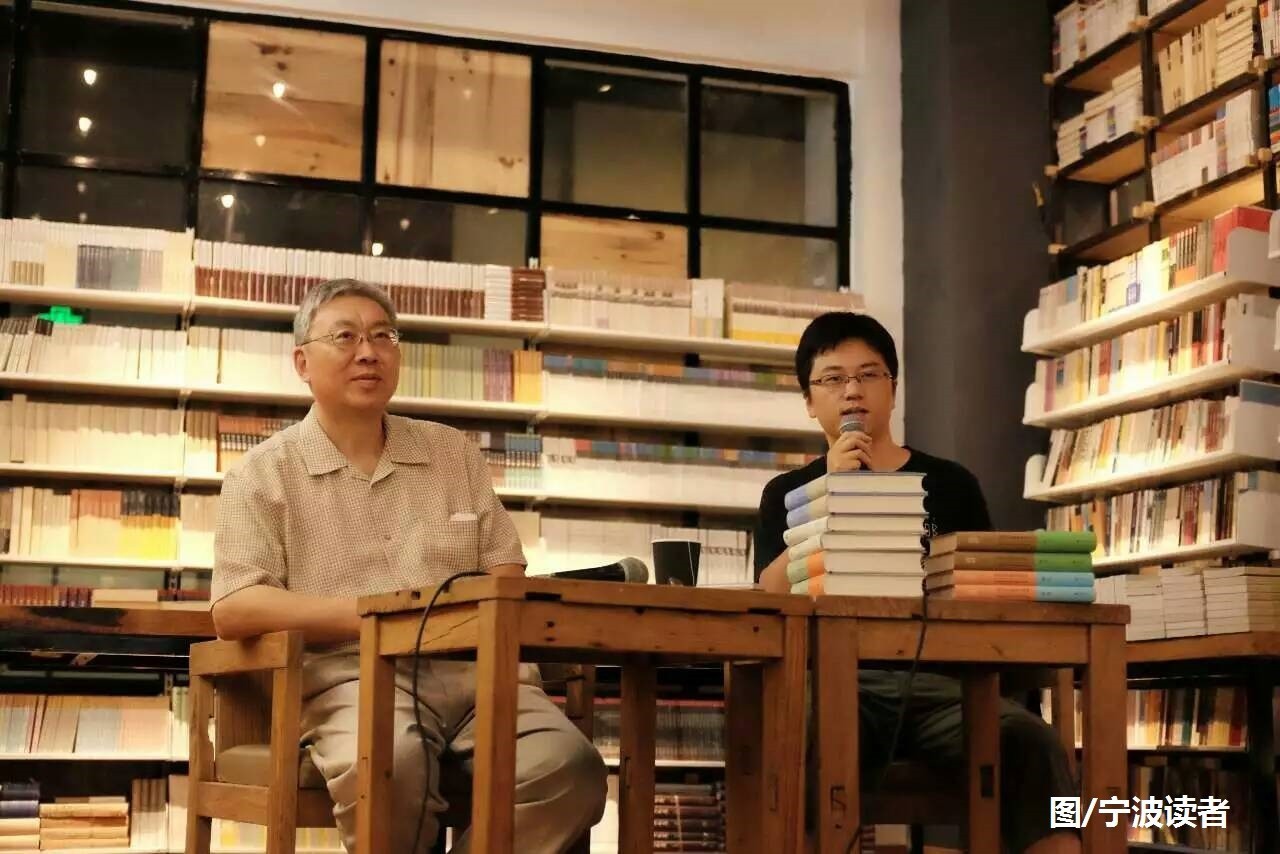
宁波讲座现场,左为徐贲,右为羽戈
怎样才算公共知识分子?
徐贲:我前两天在写托尼·朱特的评论,他非常明确地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也就是说,起公共作用的知识分子。我将他的观点归纳了几点与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是把明确的伦理倾注到对问题的讨论中去的知识分子。我非常认同他的看法。公共知识分子需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并坚持他的价值观。这对知道分子就不是必须的了。现在反公知伴随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反普遍价值。如果价值不是普遍的,不能运用于人类的每一个成员,那它就只能是小集团和党派的价值了。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在普遍价值和党派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呢?这是一个讨论知识分子问题时必须提出来的问题。
公共知识分子不同于一般“知道分子”的另一个方面是他的写作方式和文风。比如说我自己就有过一个转向,在写作方式和文风上从学院知识分子转向公共知识分子。朱特在去世前不久,回顾他从学院知识分子向公共知识分子的转变,说他逐步拓宽了自己公共写作的范围:从法国史中撤出,进入政治哲学、社会理论、东欧的政治和历史,进而进入欧美的外交政策问题。他不愿意把时间和精力只是耗费在专业历史学家的职业道路上,觉得自己从非纯粹历史学家的写作中受益匪浅。
我深有同感,觉得他说得非常正确。我们在写作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阅读对象是谁。我在学校里教写作时也跟学生说这是首要的问题,你一定要弄清楚你在为谁写作。我们把读者分为两种:一种是意向的读者,是你写作时在头脑中设定的读者;另一种是可能的读者。比如我写一本书,并不是为所有人写的,但是所有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读这本书。
公共知识分子的写作跟学院知识分子是不同的。学院知识分子只要小圈子里的人认可就可以了。公共知识分子需要面对更为广大的读者,这就要求他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进行写作。我自己也是慢慢学起来的,并不是天生就会的。一开始我也很不愿意这么做,媒体邀请我做专栏作者的时候,我也是再三推辞的,后来我同意了。但是开始我做不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不习惯于用一种跟大众读者对谈的方式来写作。
我从报刊基层编辑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跟我说,徐老师,你一个句子不要超过25个字;你写标题不要用名词格,不要用“什么的什么”,你要用一个反问句,用一个修辞问句,或者用一个动宾陈述来直接表明观点。这些是一般大众普遍的接受方式,大学教授们往往不在意这些,认为不过是雕虫小技。
第三个,我们谈公共知识分子,要谈他捍卫公共语言的责任。公共语言一定要清晰,反对用含混、暧昧的语言来混淆视听、欺骗民众。乔治·奥威尔称那种语言是乌贼鱼喷出的墨汁。大家都知道奥威尔,没有人会怀疑,他是一个货真价实的公共知识分子。他特别强调语言的清晰,民主毁于语言被侵蚀。这里涉及许多公共说理的具体问题,比如我们使用的概念一定要跟读者交代。因为他们是普通的读者,不一定清楚你用的概念是什么意思。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要意识到,他和读者的知识可能不在同一层次上,他有把问题说清楚的责任。如果一般读者弄不懂或者是读不懂他的东西,那么责任是在知识分子,而不是在读者。学院知识分子没有这样的责任感。他会觉得自己专业水平特高,读者水平太低,所以才看不懂他的文章。
我要强调的是公共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的一些不同。一个知识分子并不自然地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是需要知识分子自己去努力的。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有一些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骂他们是“臭公知”。我们需要知道,批评的理由是什么呢?最常见的是这样一个理由,他们对不是自己本行的事情随便“开黄腔”,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批评。因为任何一个知识分子都不可能对所有的事情发言,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不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我们说他还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而不是说他是一个“臭”的公共知识分子,这里面是有区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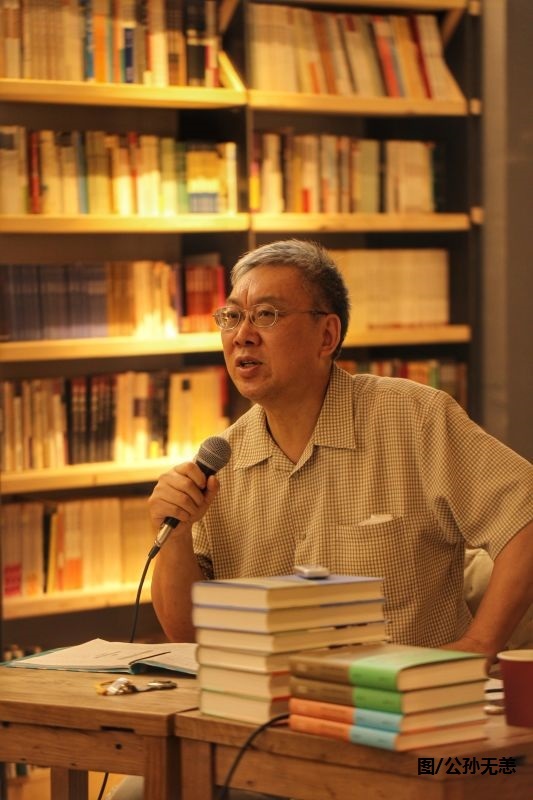
什么是良好的公共生活?
徐贲:这个问题让我觉得有点为难,因为我们知道,良好的公共生活就像良善、正直或者良心一样,没有办法简化归结为一种形式,不同的人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
再看这个问题。“什么是良好的公共生活”是以一个正面的方式提出来的,而我们认识正面的、好的东西往往先是从它的反面出发的。所以我们不妨从另一个问题谈起——什么是不良好的公共社会?
人类对负面的事务比对正面的事务更敏感,也有更持续的关注。从反面来表述正面事物的原则,乃是凸显负面行为对社会道德秩序的严重破坏作用。不少哲学家都是从反面来讨论正面问题的。比如不久以色列哲学家马格利特《正派社会》的中译本出版了。在马格利特那里,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不是不做哪一些事,而是不做哪一种事。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这是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按照马格利特的解释,不正派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人的各种羞辱。马格利特对正派社会的定义是从反面描述的。
我们对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比对什么是应该做的事情来得更明确。我们避免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自然也就浮现出来。
但我还是要讲一讲什么是正派社会,我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正派的社会。除了马格利特说的避免羞辱这件事,还有一点值得说一说,良好的社会允许人们成为“充分公民”,他们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身份是可以互换的,这是亚里士多德提出来的。在现代良好社会里,充分公民的意义就是,让尽量多的人成为拥有自由权利,并担负社会责任的公民。永远处在被管制状态下的人民不可能成为良好社会的道德主体,他们在有权的时候会是恶吏,无权的时候则是刁民。
知识分子是社会里比较特殊的一部分,在行使公民权的时候,他们也许与其他公民差不多。但是,他们是社会群体中智识程度和能力——阅读、写作、分析、思考——最强的那一部分人,因此而担负更多的公共道义责任。这是一种不应该转换为特权,包括话语特权的责任。良好的公共生活应该是知识分子能够担负起自己道义责任的公共生活。最近媒体上有一件事情讨论得比较多,那就是杨绛去世。这件事情不仅涉及杨绛和钱钟书,而且还引发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比如知识分子在一个良好的公共生活中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今天早上我看到清华大学教授萧瀚写的一篇文章,反驳有的人批评钱钟书和杨绛这样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不公不义从来不发出自己的声音。萧瀚教授的论点是,只要他们不伤害别人,就已经守住了道德底线,别人也就没有理由去批评他们。这是萧瀚教授为钱钟书和杨绛所做的辩护。在这个辩护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对良好公共社会的一种理解:在这个社会中,大家互相不伤害,就构成了每个人的善良或者良善,或者好的公共品德。
但是有人会不同意这样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伤害”这个词并不是一个客观的说法,而是一个理解性的词语,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个看法。对于什么是伤害,我们是可以有不同理解的。杀人越货当然是伤害,但是在看到有人遭到不公正待遇或是遭遇危难的时候,你袖手旁观或漠不关心,这是不是一种伤害呢?如果一个社会认同比较充分,比较高程度的良善,那么这个社会中许多人都会认为,袖手旁观不等于不害人,更不是一种道德行为。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里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遇见一个快要渴死的人,而你又带着水,你就有责任帮助他,你不能以自己的消极自由为理由,见死不救。这个例子也许可以说明,越是好的公共生活里,每个社会成员对自己的道德要求——康德所说的“不完全义务”的要求——也就越高一点。
徐贲:1950年出生于苏州。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英语文学博士,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兼职教授。徐贲客居美国,却以最大的热忱担当起中国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其兼具思想性和时事性的文章以极高的频率出现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严肃媒体上,聚焦公民社会建设、公共生活、国民教育、公共文化记忆等领域,深入分析当下的中国社会。
本文转载自公号“三辉图书”:sanhuibooks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