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约翰·凯(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首任院长)默文·金(英国央行前行长)
(本文摘自作者新书《极端不确定性:如何为未知的未来做出明智决策》第23章节。界面新闻获出版社授权刊发。)
电影《第三人》中,奥森·韦尔斯饰演的黑帮头目哈里·利姆有一个著名的观点:“意大利在波吉亚家族统治的30年里,经历了战争、恐怖、谋杀和流血,却产生了米开朗琪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在瑞士,人们相亲相爱,民主与和平延续了500年—这样的环境里诞生出什么?咕咕钟。”利姆和很多人一样贬低了瑞士人的成就,这个国家涌现了爱因斯坦、卡尔·荣格、勒·柯布西耶、保罗·克利和赫尔曼·黑塞这样的大家,更不用说“邦女郎”乌苏拉·安德斯、网球大满贯得主罗杰·费德勒,以及总数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的诺贝尔奖得主了。利姆抨击的咕咕钟,只不过是这个国家在精密工程方面造诣的滑稽化和脸谱化,精仪产业和特种化学品行业使瑞士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不过利姆有一点说得很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特有的政治动荡确实与一个伟大非凡的创世时代相吻合。
《土拨鼠之日》是一部很特别的电影,由比尔·默里饰演的主角注定要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循环往复昨天,每个风险厌恶者都向往已知,但即使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主角也没有尽情享受这种确定性,而是在绝望中试图终结生命,最终才发现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没有死亡这回事。影片是大团圆式的结局,也许是因为好莱坞喜剧必须如此,但也是因为默里饰演的角色已经从重复的经验中学到了足够的知识,从而摆脱了循环。
哥伦布横跨大西洋的50多年前,中国船只就开始了同样雄心勃勃的探险活动。但明朝皇帝后来的重心转向了内政,拒绝外来影响,向往不变的安逸。两个世纪后,日本幕府也仿而效之。1792—1793年,马戛尔尼带领英国使团访华,他的礼物和建议都被清朝皇帝回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是乾隆皇帝的原话。
大分流由此开始。工业革命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同样条件优越的中国东南沿海。直到19世纪,英国皇家海军借着胜之不武的鸦片战争将英国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时,中国才开始思变。无独有偶,1853年,马休·佩里威逼日本打开国门,日本才开始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但日本真正走进现代世界要等到1945年麦克阿瑟将军强行登陆,之后的半个世纪,麦克阿瑟也对东南亚大部分地区做了类似的事。在人类社会中,不变并不是一个好选择,长远来看也不可持续。

风险和不确定性
凯恩斯和奈特都认同概率游戏不可预测的结果和极端不确定性是不同的概念,前者可以用概率表示,后者则不能。二战后,弗里德曼否认了这种区别,从此,这两个概念不仅在经济学领域销声匿迹,在决策理论和贝叶斯推理举足轻重的其他领域也逐渐被忽略。
我们可以为每一起可能的事件附加发生概率。未来发生的事情可以被描述成一系列互斥选项之和,每个选项拥有各自的发生概率。这意味着我们可以给风险定价。一旦定价,风险就被驯服了,不确定性事实上被市场压制了。
在金融理论中,风险被定义为相比已知平均收益的价差。价差越低,风险越小。由于人类都是天然“风险规避”的,在这个意义上,只有提供激励,人们才有动力持有风险资产。因此,风险和收益之间存在一种权衡。只要有足够的补偿,风险规避者就愿意承担风险。风险不再可怕,因为有了价格,可以据此价格交易。和肥皂粉、汽车一样,风险资产也是可以买卖的商品,最终风险会落入那些购买意愿最高、购买能力最强的人手中。极端不确定性被排除在这样的讨论之外,因为它无法被量化,也不能被定价。
不过世界虽小,但并非完全属于你我。日常用语中,“风险”和“不确定性”被用在各种不同的场合,由于术语和日常用语的区别太大,针对的特定语境不同,其解释产生了许多混乱。我们也把风险定义为无法实现的参考叙事。达·芬奇的才华受到卢多维科·斯福尔扎、切萨雷·博尔贾等资助人的热捧,他在参考叙事中得到保障,能够自由作画和思考。即使是在博尔贾家族互相残杀的时候,资助也给予了一个乡下私生子实现抱负的机会。对达·芬奇和米开朗琪罗来说,动荡年代的艺术创作生机勃勃,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斯福尔扎死于法国监狱,博尔贾被剥光衣服,在纳瓦拉的一次战役中丧生,而达·芬奇因中风于家中逝世,米开朗琪罗则享年88岁。
没有观察到波动性绝不应该与没有风险相混淆。休谟对归纳的阐释告诉我们,不能因为太阳总是升起的历史信息就相信它明天会照常升起。到现代,伯特兰·罗素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述,火鸡在12月24日前的每一天都会被精心饲养。纳西姆·塔勒布重新构建了这一叙述,将银行家与出租车司机进行对比:前者每个月末都会收到一份固定工资,但总是面临突然被解雇的风险;后者的收入总在变化,却很有保障,因为这些钱是持续地从多个来源获得的。认为当前没有波动就不存在风险的错误想法,正是金融危机发生的核心所在。就像圣诞节的火鸡一样,许多金融机构的录得季度每股收益的确按照华尔街的要求稳定增长,直到2008年才发现自己突然面临破产。这些金融机构和许多企业的报表盈利稳定,是值得关注而非祝贺的。波动更大对这类营收来说反而说明业务运作得更可靠。世界本质是不确定的,伪装出平稳的假象是在制造风险,无法降低风险。
塔勒布介绍过“反脆弱”的概念,即找到合适的落脚点,从极端不确定性和未知的未来中获益。期权的价值会因波动性而增加。据传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通过天体观察,预见到橄榄的丰收,并事先低价租下橄榄压榨机再转手高价出租,不过交易的细节并没有记载—如果这事真的发生过的话。也许他是和橄榄压榨机的所有者签署了一份期货合约,也许是购买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看涨期权:有权利但没有义务以事先约定的价格租用橄榄压榨机。如果的确像泰勒斯预测的那样大丰收,这个价格就显得很低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都参与了第一笔有记载的金融衍生品交易。衍生品市场的存在是由于证券价格的波动性,波动性越大,期权的价值就越高,无论是看涨期权(购买权)还是看跌期权(出售权)。大多数期权交易就是打赌,赌注双方对于未来有不同的看法,谁的观点更接近正确,谁就能在零和博弈中让对方认输。臭名昭著的大空头就是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和其他人关于美国次级贷款抵押市场的一场赌局。不过期权交易也能使双方都受益。今天的芝加哥商业交易所是全球金融投机的中心,它的出现是为了让农民和食品加工厂提前锁定尚未收获的农作物价格,以保护他们的参考叙事。尽管“期权”一词如今最常出现在金融市场,但现实中,期权的实际意义要大得多。一个类似的战略决策,有机会打开一扇门,也可能关上一扇窗。
……
创业精神和极端不确定性
奈特认为,正是极端不确定性为创业提供了机遇,这一洞见是理解社会、技术和经济进步的基础。在进化的过程中,包括生物进化、制度演进、政治变革、市场驱动变革,开创者精神推动着我们前进。不仅仅在商业领域,学术、实用知识、艺术和许多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穷小子凭借出色的商业想法单枪匹马杀出一条生路,脱贫致富;孑然一身的学者在车库或者小镇牧师家中文思泉涌,奋笔疾书。这样的孤独榜样往往只是传说。很多例子和这种想象大相径庭。爱迪生曾经是西部电气的电报员,后来是现在的通用电气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他仅做过的两份工作,都被炒了鱿鱼。贝叶斯生前是个牧师,去世时籍籍无名。如此极端的例子不多,要想举例,得追溯到更早的历史。现今典型的成功企业家通常在大公司里积累一段时间的经验再创业,并且一开始就和志同道合的人团队协作。只有当社会环境给予这类人支持时,他们才能做出贡献。尼日利亚并不缺创业人才,但太多的好苗子倒向了机会主义骗局和寻租。奥巴马在2012年的罗阿诺克竞选演讲中受到广泛批评,因为他说“如果你成功了,并不是全靠自己”。但如果你再听下去,就知道他说得非常对:“我们取得成功,既因为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也因为我们共同奋斗。”也许在所有孤独的天才中,最了不起的是斯里尼瓦萨·拉马努詹,这位穷苦出身的印度数学家没有通过高考,数学是在公共图书馆里看书自学的,这给一位印度税务官留下了深刻印象,并给了他一份工作。这位税务官还给G.H.哈代写了一封信举荐他。凭借这封信,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给了拉马努詹一笔奖学金。如果没有哈代,拉马努詹的思想永远不可能在主流数学家群体中获得认可。
富有创造力的个人利用集体智慧,在与他人的交流中磨炼自己的想法,并在稳定的参考叙事中通力合作,人类就能在极端不确定性中蓬勃发展。在有安全保障的参考叙事中,不确定性并不吓人,反而受到欢迎。在包括交友、度假、享受休闲时光的私人生活中,平静无波非常无趣。在政治和商业中,尽管官僚由于风险厌恶决心保护自己既得的参考叙事,有时导致决策瘫痪,但不确定性仍然是进取的机会之源。在艺术领域,不确定性和创造性形影不离。拥抱不确定性吧,同时规避风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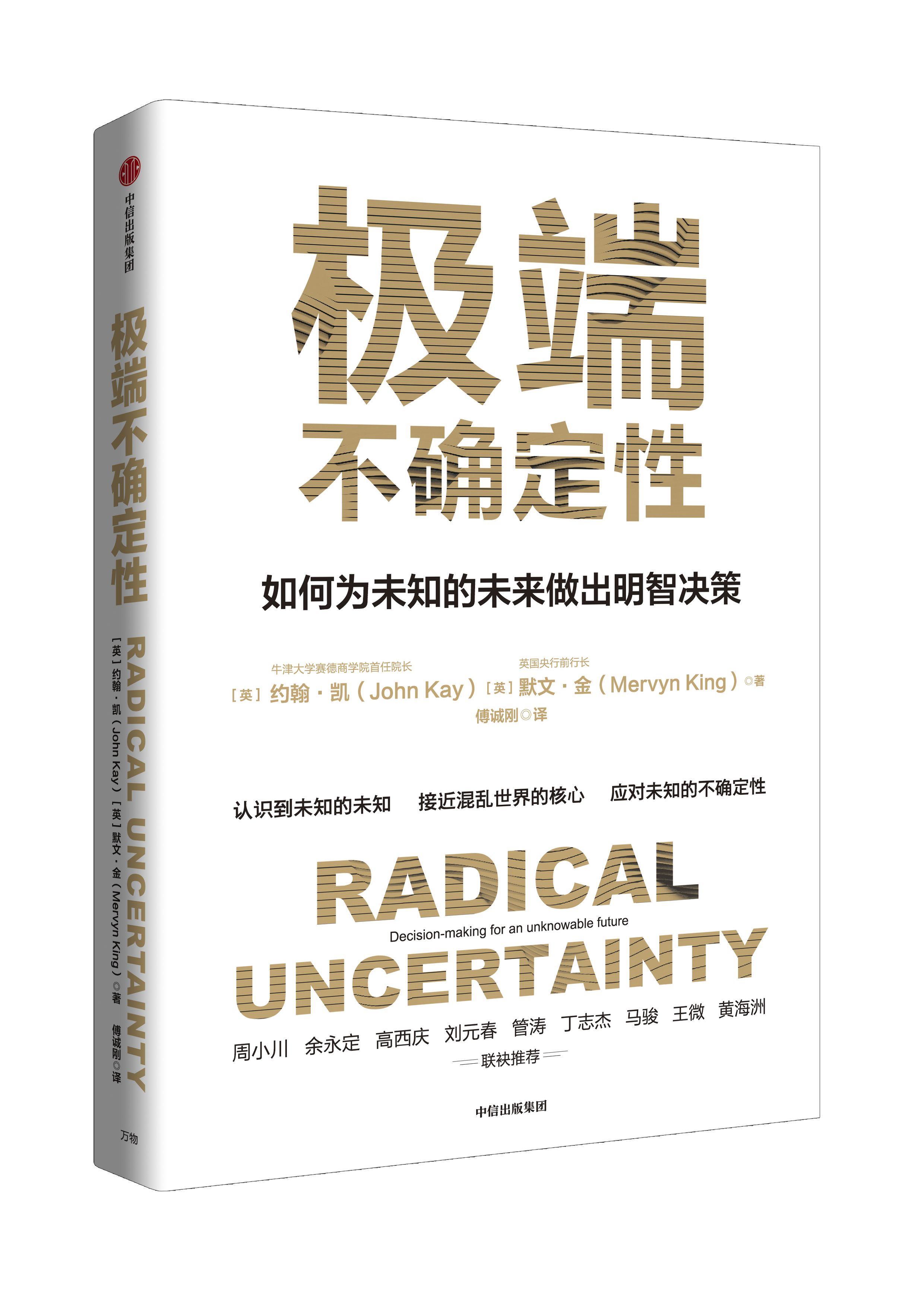
译者:傅诚刚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责编邮箱:yanguihua@jiemian.com。)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