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不再有人质疑:媒介能改变一切。如今早起头一件事,先看手机,生活才算开始。在我出生的90年代初,姑且赶上“写信”时代的末流,还未写多少字,数码时代便轰然而至。想想自己15岁时的第一部手机,摁八九键才出一个字码,简直远古年代的事了。
数年前,施坦威纽约总部的录音师告诉我,他们已将霍洛维茨的录音输入了其电子琴Spirio的软件系统内。乐器自动演奏的技术早已不稀奇,只是效果一概粗糙,全无艺术性可言。但那天,在施坦威总部的展览间里,我确凿目击“霍洛维茨”在那架空无一人的琴凳上自行弹着舒曼《梦幻曲》,逼真至此,简直活见鬼。是人的幽灵,还是机器的幽灵?看来,“显身”的奇迹已离我们不远了。或许近在咫尺的将来,你便能在自家客厅的钢琴旁,听着千里之外某人在卡内基音乐厅的“现场直播”;甚至坐在自家琴凳上,紧盯眼前飞速舞动的键子,起落间,仿佛你已附身于奏者,或者已被他附身。
前人显然没那么幸运。肖邦曾告诉他的学生,演奏他的玛祖卡时,务必严格按照舞曲三拍子的节拍弹。他总强调:左手(节奏)与右手(旋律)应如树的根叶。叶自随风摇摆,根则岿然不动。但有一次,一位友人告诉他,在某场音乐会演奏自己的玛祖卡Op.17之2时,他的节奏不仅跃出了原本的三拍子框架,甚至将其中第二拍的时值延长了一倍,从而将整段拉宽成了四拍。对这一反馈,肖邦大为恼火,坚称那绝无可能,并要当即在琴上验证。这次,友人随节奏大声打着拍点—结果,确实是四拍子。铁证在此,肖邦汗颜大笑,继而辩解:他虽然弹了四拍,但应被“听成”延长的三拍。
初读这则逸事,我失笑之余,也不禁同情。两个世纪前肖邦的尴尬,道尽所有当代独奏家的苦衷—这是主、客观之间无法弥合的断裂。无论对友人如何辩解,肖邦自己知道:现实与他自身期望的不符。听者实际听见的,与奏者“以为”它是如何被呈现的,其间不仅存在着盲点,且主观永远无法捕捉这些盲点。画家或作家尽可规避这个问题,能在边创作时,边退身自审:文字、图像不会随过程的进行而消失,于是可检验,可更改,可雕琢。但音乐做不到:表演的即时性,使人只得“投身”而无法“抽离”。这确实是演奏的秘密,一个令演奏家时时痛苦的秘密:聆听自我,成了那最难获得的经验。
在肖邦的时代,只有作为文本的乐谱得以永存。演奏仅在听者脑海中留下一个记忆:一个瞬间的记忆。两者的分野由此明了—乐谱承载绝对的意义,指向永恒;演奏关乎当刻的表达,指向自我。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演奏者只顾随性,而无须忠实原作。彼时,忠实旨在“态度”,而非“成果”:成果本就留不住。但也是这个局限,赋予了演奏在前录音时代某种神秘的魅力。在一切声音都无可留存、无可审视的年代,或许连肖邦自己也难分清:哪些瞬间关乎当下感受,哪些又是为了重现文本?对一切旋即而逝之物做出耐久的推敲、重复的审视,非人所能为。除非演奏能够留下来—除非,它可被复制。

传19世纪摄影刚出现时,第一批目睹照片的人都会历经强烈的不适。此即“视差”。虽平日照镜早已熟晓自身相貌,但那终归是肉眼所见的自己。而在相片中,“主观”破裂:我们获得的是镜头—那只机器的眼睛—所捕捉到的“我”。人第一次被逼到了他者的处境来审视自身:一个被强迫且陌生的地带。但这“视差”,正是所有演奏者求之不得的—他们比任何艺术家都急需“陌生化”。对此,他当然不适—没有哪位演奏者会绝对满意自己的演奏—可一旦面对,他便会当即认同这种不适,并努力靠近那个使其不适的对象:他自己。

19世纪末音乐复制术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人与聆听的关系。因可复制,演奏即与乐谱同样恒久了。换句话说,演奏自身也成了“文本”。原先关乎“当下”的立场成为不可逆的过去,一种“完美”的意识开始逐渐垄断演奏的主流观念。从第一代录音的钢琴大师科尔托、拉赫玛尼诺夫、弗里德曼、霍夫曼,到20世纪中后叶的波利尼、阿什肯纳齐、内田光子等等钢琴家,我们能清晰地看到这种变化的趋势。起初,这样的演化是式微的:毕竟在留声技术还趋于原始的20世纪初,录音顶多只是现场的粗糙留念。彼时的老一辈演奏家料想不会通过机器去“审核”自己,更免谈通过它去审判其他同行。但随着录音技术的捕捉愈发细腻,留声传播的迅猛普及,某种精确化的审美不知不觉收编了我们的听觉。起初,演奏者通过录音听到了真实的自己;而后,渐渐地,他成了这种“真实”的依附。罗兰·巴特曾在论及摄影时说道:“从我觉得正在被人家通过镜头看的那一刻起,就什么都变了:我摆起姿势来,我在瞬间把自己弄成了另一个人,我提前使自己变成了影像。这种变化是积极的:我感到,摄影或者正在创造我这个人,或者使我这个人坏死,全凭它高兴。”巴特的话不也同样适用于音乐吗?现场本不存在统一,听者所在的位置不同,音响声效、聆听体验自有差异,索性无所谓“客观”了。但麦克风给出了某个“客观”,将聆听同化,使人不由地卷入这同化中。录音时,演奏家须兼具三个视角:我想要如何演奏;我实际是如何演奏的;录音又是如何呈现出我的演奏的。麦克风可以“创造这个演奏家”,也可以使他“坏死”。此中的纠结与隐衷,只有音乐家自己知道:
话筒距离乐器的远近、话筒品质的优劣、不同音域的收音、各种播放器的不同效果等等,一切细节都可左右演奏的成果。记得我录制第一张专辑前,临前反复通过手机判断自己所弹;直至踏进录音棚,才发现先前粗劣的“手机经验”全然无法核对。你甚至开始怀疑那是否是你的诠释,是否是你这个人(或借巴特的话:是否使你“坏死”),但同时你必须冷静面对,因为演奏的道德命令你撇清一切主观,去找寻那个相对可能的客观。
* * *
但从来就没有什么客观。有的,毋宁说是演奏家渐渐成了“客体”—他开始从各种角度审视自我。在对自身每个细节的不断雕琢、不断打磨、不断复制中,原先19世纪那个无辜、不自觉的“我”开始自觉,继而过分自觉。借巴特论及摄影的另一句话:“你感到镜头正在对自己实施外科手术”。
这话与本雅明对电影的论述同出一辙。本雅明曾将绘画与电影相较,将前者比作古代巫医,后者喻作现代外科:巫医在人体外施法,一如画家面对景物。但电影不同—电影“深入”事实—一如外科医生进入病患体内操作。不同机位的镜头以不同的视角,使人获得凭借自身肉眼无法获得的另一种真实,一种仅属于电影的真实。而这“深入”的手段,不外乎剪辑:一如形形色色的手术刀,将无数分割的镜头/视角系结起来。
录音又何尝不是一种手术?与20世纪初,因技术限制、浪漫思潮所共同生成的美学不同,当代审美越发科学化、精密化(仿佛一个错音真如毒瘤一般,能损作品的性命),使其不可能逃避剪辑(“手术”)的命运。进录音棚,红灯一亮(真的,录音过程,同样打红灯),演奏的死活即凭录音师“宰割”。坐在音控室里的人不是你,你更无时间在每遍演奏间隔往返校对,你只能暂时信任录音师—就像手术前,病人不得不信任医生。
信任医生,就是信任技术。录音的“切口”随着精确化的需求逐步细化:原先交响乐团的录音只需两三只话筒,近似我们双耳所能听到的现场,而今时几乎每一组乐手的谱架前都会放置一只。由此带来的变化是惊人的:许多被现场所遮蔽的、听不到的配器细节、隐秘声部都能在录音中被清晰而立体地捕捉到。(多少音乐家自小到大的学习经验,包括我自己,不是依赖唱片,并得益于录音精确的细节捕捉力的?)此外,录制的“缝合”技术也同步跟进:古尔德曾要求调律师将某几个琴键加倍调亮,以求达到某种声部凸显的奇特效果,而后在录制下一段时,再请调律师将那些键子调回原初的音色—这是现场无论如何也办不到的。真正令古尔德兴奋的,不是演奏中的未知,而是将一切未知尽数“已知化”:将自我置身于无人的世界里,不断录放、试验不同的想法及处理,以敲定最终的拼接方式。某次,他突然发现自己两段版本的速度截然不同,但若拼在一起又会产生奇特的效果,权衡再三,决定照此剪拼。虽严格说来,这样奇特的“成果”非人,而是机器所为,但撇开此中的“道德”命题不谈,有多少演奏家能拒绝这样的诱惑呢?录音已不再是对演奏的复制:它俨然成为创造本身。
与现场体验的“整体感”相反,录音凸显、暴露了一切局部。它以手术刀般的专注与无情,深深切开了音乐的“原作”。常听画家谈起印刷品与原作的差距,我也深有体会:数年前我在多伦多安大略美术馆的展厅内,面对凡·高“星夜”系列中的某一幅目瞪口呆,那是印刷品所无法复制的震撼。借本雅明的修辞,那是原作的“光韵”。这光韵一方面来自其“作”自身,但另一面,也许是更为关键的,来自你与它共享的那个时空:即时、即地。你只在那个瞬间、那个场所才遭遇它,而后它逃逸,仅留你的记忆捕获其光韵的末端……
但音乐,其实不存在“原作”。哪怕作曲家的手稿,也常在不同出版商手里存有不同版本,各自的细节标注均有所异。讽刺的是,最接近原作特质的,反倒是秉持“忠实原作”的现场演奏:只有现场存在特定的时间、空间,特定的“光韵”。而这一切,都在录音中行将消解:“时间”不再独一(不仅演奏可剪辑、可拼接;聆听也可倒带、暂停、快进、重播),“空间”也随之消隐—作为听者,你可以身处任何地点,音响的另一端则无所谓地点。即使在视频中,你也得以在自身所处之地,通过屏幕进入“彼端”—那个音乐发生的原场所—借由镜头特写直击演奏者的面部表情、神志状态、举手投足,再通过镜头的远近切换把握现场各方细节—这赋予了视频录播以某种特有的“事件感”。然而在唱片中,无论纽约卡内基,还是柏林爱乐大厅,都与你的聆听无关。音响似乎具有某种“空间感”,但那并非空间本身—你没有“在”那里,也无法像看视频那样,一睹事件的发生。

听者如此,演奏者呢?台上再孤独,演出毕竟存在“对象”:为场合本身、为某个具体的人、为热切的公众、为深爱的作曲家,凡此种种,各含温度与激情……而录音时,“对象”不在了。那是一个绝对内部的空间:琴三尺外,几只麦克风猫眼般不动,窥视着空无人迹的一幕。红灯亮起,无数声波与数码的神秘转换便即开始—现在,是音乐孤独了。
在谈及影像与死亡的关系时,巴特写道:“越出镜框,就是绝对地死了。”这让我想起音乐—在现场,演奏作为空间的一部分,向其余部分(环境、他人等等)敞开。那些部分,同样构成了演奏的生命力。但在机器的世界里,声响之外,是绝对的“无”。听者面对的,是绝对黑暗中的意义流动,是一段段排除了观赏体验、演奏真相的音乐,一份份剔除了“事件”的纯粹文本。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录音远比现场更为饱满、雄辩地呈现了音乐的“抽象”。
* * *
何谓抽象?想来“媒介”,不过是些物质。越趋现代,艺术中“物”的成分越凸显—在现代诗歌中,读者越发依赖词自身的“质感”以触及诗境,而非通过传统的格律、语言的美感。在塞尚或凡·高的画中,先是笔触和色块的物质感,再及结构之美;到了杜尚,观者借由小便池想到“喷泉”;到装置艺术,物索性“站”了起来……但更无哪类形式,如摄影、电影那样,时刻照见美学与媒介的绝对关系。人通过使用镜头、快门、胶卷的快感进入摄影—布列松有言:“从事摄影的人只是摄影的工具。”而人对电影的百年情结,更是对电影院的情结:脱离荧幕、放映机、暗室所带给人的物质体验,Film(即“胶片”)的魅力又何在?艺术的伟大,因其不自知于媒介,又时时体现为媒介:一次次快门、一组组镜头、一笔笔涂抹;音乐也无非这样:一个一个音奏下去。说到底,钢琴,就是键槌撞击的变幻,大提琴,无非木盒振动的共鸣……
但录音不同。第一次进录音棚,我看着满屋的处理器、调音板、功放系统,已然迷失:声音轰然响起,但似乎并不来自它们,而是另一个世界—一个缺席了物质的世界。这些密密麻麻的器械,可以是任何东西,但绝不是制造声音的“工具”。相反,它们是在抹杀,抹杀声音的器具性(或“杂质”—以录音的立场来说),仅留给听者一片过于洁净的抽象之境。“媒介”,在电子技术的绝对精密中,消失了。这是它与摄影、电影的最大不同。电影中,你时刻意识到镜头的存在;但播放任意一张唱片,你绝少意识到话筒的位置。任何一位录音师都会告诉你:若有意识,则是录制的失败。想来颇有深意:镜头永远是观看的一部分,但话筒却时刻隐匿自身。某录音师曾告诉我:“声音的来源,必须是神秘的……”
我想,说音乐“抽象”,在高的意义上,是指它不满于媒介—巨大的不满。自有音乐起,它便试图超脱于具体的媒介,超脱于“即时、即地”,超脱于历史。同一件作品世世代代演奏、不同场合演奏、不同乐器改编演奏,都在宣示着这一不满。但只在机器的复制中,音乐果真逃逸出“即时、即地”,彻彻底底自由了。巴特论及摄影的怀旧性,用到“此曾在”一词;桑塔格说过相似的意思:“拍照就是参与另一个人(或物)的必死性、脆弱性……”
但音乐似乎没有这个问题:音乐自有其时间,也善于舞弄时间。无论怎样剪辑拼接,如何暂停快进,一旦按下播放键,它旋即进入自身的生命,并霸占外部的时间。相较影像的“此曾在”,音乐时刻“此在”:这是复制技术不仅不会削弱,反却强化的一面。此在的记忆、此在的期冀、此在的“死”。数十年前录下的瞬息,此刻翩然复活,且音质越纯净,越“抽象”,越超其然于“历史”……
当然,我也无意将这种抽象性绝对化:录音的许多问题,仍不无暧昧。例如古尔德录音中随处出现的跟唱,卡萨尔斯老年录音中突兀的哼吟……这些历史的“杂质”,因唱片放大局部的能力,使之远比在现场以及视频中更暴露。然而它们并未损伤,反之增添了音乐的魅力。这魅力,究竟源自我们对演奏者已存的敬意,抑或它们早已化作音乐的符号(毕竟我们只闻其声,未见其形)扩大了我们想象的边界?—在隐去了空间的维度里,“人”与“琴”的分野还重要吗?
这些问题,且看作留给听者的余地吧。想来唯一确定的,还是那句话:媒介能改变一切。随着科技自身的发展,也许音乐的复制会在久远的未来,带给我们更多的解答,或更深的困惑。此刻谈未来,我脑中一片空白,仅想到一个现成的例子—
1977年,美国旅行者1号、2号探测器相继升空,各自载着一盘特殊的音碟。碟中录下了55种各国语言的问候、诸地风景、各族人脸的图像信息。这是人类第一次向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释放信号,也是唯一一次。又怎能忘了艺术?于是附上巴赫的序曲与赋格(古尔德版)、莫扎特的咏叹调、贝多芬的弦乐四重奏、斯特拉文斯基的交响乐……
在外太空,一切都变得抽象了,包括最具象的表情、问语。如果当真有外星人截获,不知会怎样评判这两张唱片中的内容?是否会看待人类的姿态言行,犹像我们看待自己科幻片中的外星人一样,甚觉畸异丑陋?暗自庆幸:好在还有音乐—好在,是录音。如果是配上现场视频,看着指挥家手舞足蹈,钢琴家俯身琴面、拱背自语,该多怪异……
是我的私见吗?在外太空,相比图像、文字,那些音符显得那么适宜:绝对黑暗,绝对自在。两年前,适闻旅行者1号、2号刚刚驶离太阳系—四十余年的旅途。现在它们真的孤独了。百年前,兰多夫斯卡曾说:“弹《哥德堡变奏曲》时,仿佛地球上仅我一人。”叔本华的话恍若回答:“即便从未有人类,宇宙中,也会有音乐。”
喂,外星人,你们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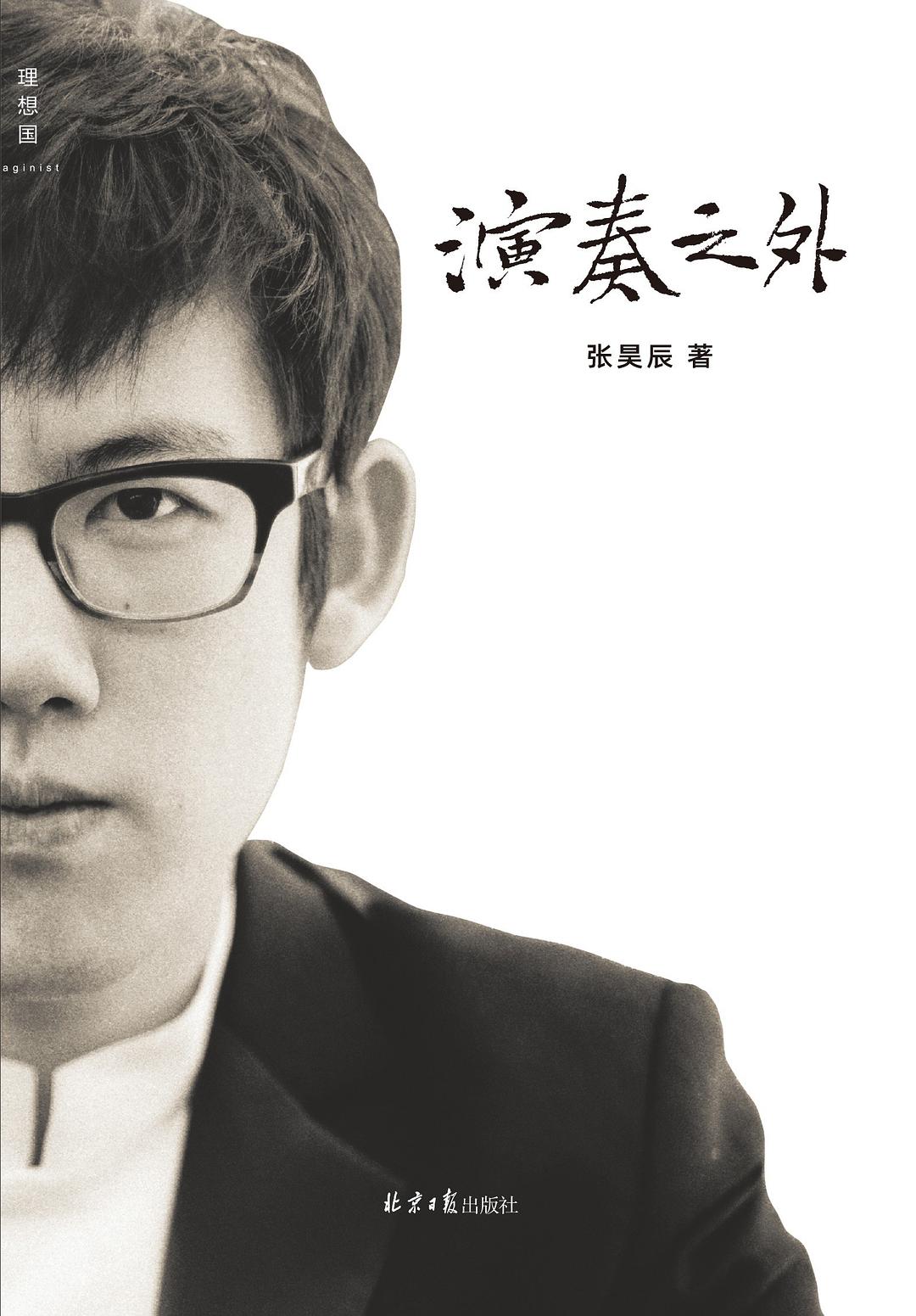
版本: 理想国·北京日报出版社 2022-7
本文及配图均选自《演奏之外》一书,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