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着扎实的田野调查,社科院文学所副研究员陶庆梅在《当代小剧场30年(1982-2012)》一书中将“小剧场”置于30年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之中,从小剧场的发展个案入手,折射了整个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历程。如今,4年时间已经过去了,陶庆梅书中的小剧场都还好吗?在戏剧节热热闹闹、层出不穷的今天,中国大陆的戏剧质量有更上一层楼吗?
没有,“剧场陷入了停滞”。——在日前两岸小剧场戏剧节的一场对谈活动上,陶庆梅非常肯定地说道。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陶庆梅。在她看来,国内戏剧节的创作者高度重合,观众群也高度重复,“当政府补贴和戏剧节越来越多的时候,戏剧的质量其实没有往上走”,“如今的戏剧一直在玩儿一些花样,但是我却看不到什么内在的动力。”商业戏剧、体制内戏剧、实验戏剧以及IP剧的市场分野在不断变化之中,却也有着各自的问题。这是一场创作者与资本的博弈,也是一场与市场需求和观众期待之间的博弈。当我们试图追问国内戏剧陷入停滞的原因,我们似乎要追寻到最根本的问题上去,“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艺术要如何重新与生活建立关系,不管是反应、对抗、还是介入。”
以下为陶庆梅在16日两岸小剧场戏剧节《小剧场生存之道》对谈活动上的发言,经主办方授权发布,经编辑整理,小标题为编辑所加。
大陆戏剧陷入停滞:
从创作群体、剧场到作品风格的全方位停滞

《当代小剧场30年(1982-2012)》那本书我一直写到2012年,现在是2016年,已经过去了四年时间。记得2013年《文艺报》记者采访我,我说“我们需要一场变化,需要一场从市场范式到美学表达的变化”,可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看到那个变化。作为一位学者,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是什么样的原因,让剧场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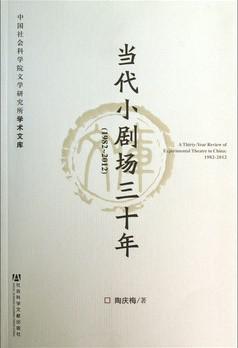
我的论调有点悲观,我所看到的大陆剧场陷入了停滞,台北和香港不在我的观察范围之内,不过我想内在一定有一致性,只不过停滞的方式是不一样。我从三个要素来说明剧场的停滞了。
第一个方面,创作群体没有特别多变化,不管是两岸小剧场艺术节、青年戏剧节,还是乌镇戏剧节,做这些事情的差不多都是这同一群人。其中有一些是从2000年到2005年之间大学生戏剧节时成长起来的一拨人,有一些是青年戏剧节上成长起来的一拨人。他们今天走向了剧场,我们在许多戏剧节上都能见到他们的作品。我们原来是希望从这代年轻人身上看到他们与上一代人(比如说孟京辉和田沁鑫)不一样的地方。他们的确不一样,但并没有形成特别鲜明的印象和属于自己的语汇。他们带新的东西到来了吗?好像并没有。
第二方面是剧场的停滞。剧场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剧场的出现与成长本身会孕育一些话题,孕育一些和他相关的创作者。这几年剧场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并没有为剧场的格局上带来多少大的改变。听北师大北国剧社社长说,在他们剧社卖最好的票,一个是北京人艺首都剧场,另一个就是鼓楼西剧场。他说的这种卖票情况和我们看到的大致相同。鼓楼西剧场的一系列“直面戏剧”作品的确吸引了不少以大学生为主体的观众,这是个新的要素,但并没有改变大的剧场格局。
第三个是在作品风格上,我有一句话叫“看上去都是新的方式,散发的都是过去的味道”。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前两天看青戏节的《拥抱麦克白》。演员丁一滕应该是孟京辉工作室的签约演员。在青戏节开幕式上我看了这部戏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很打动人,觉得这个孩子真的很有才华,上来就唱“莎士比亚,我们不满意”。然后我就去看了《拥抱麦克白》。导演和演员真是满场地耍。但我看表演时总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种表演方式——不是说这种表演方式不好,而是他不能说服我的是他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演。在这些表演后面看不到表演者的内在动力。在我看来,观众虽然说不上来为什么不好,但你没有动力他会觉得有些空。
国内当下的戏剧环境与现状
1、以开心麻花为代表的商业戏剧迅速成长
开心麻花成立于2003年,直到去年获得了爆发性增长,电影《夏洛特烦恼》票房达到15亿。在开心麻花出电影之后,搞艺术的说这不是电影,看不惯;其实真没有必要说人家商业,人家在剧场坚守了10年,熬了一个大电影出来,应该骄傲才对,这也是剧场的骄傲。开心麻花很明确地说,他们就是要做商业戏剧,做好看的、和观众有关的商业戏剧。它也比较走运,但我相信也有内在的因素。它为什么能上春晚?为什么能拍电影?其中某些东西一定是和观众的内心需求是吻合的。他们一直沿着商业戏剧的轨迹走,2015年一年内在60个城市演出1200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规模。从这两年来看,我觉得开心麻花成长非常迅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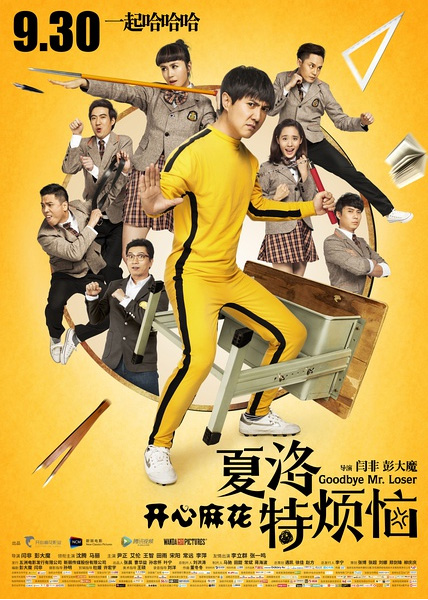
2、体制内的戏剧:国家艺术基金4亿投入带来深刻变化
同时,体制内的戏剧又开始成长,03年以后国家艺术基金每年将4个多亿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它为戏剧生态带来了非常深刻的变化。国家艺术基金不仅仅是提供戏剧制作的钱,而且你要演出还有给场租的钱……所以,随着它的投入加大,这些投资会把剧场吸到它的需求内部去。就是你有戏也找不到剧场演。国家艺术基金除了把剧场吸过去之外,把人才也吸过去了。之前体制外的创作能出来,原因是体制内没有戏演或演出很少。现在体制内有了创作经费,马上就把人都吸进来了,他们就没有时间再去创作(自己的戏剧)了。从整个生态来说,这个影响太大了。然而,体制内做出来的作品又很难在市场上被销售出去。许多作品是宣传部在抓选题,而舞台审美又落后于时代,所以没办法卖出票。
3、从实验出发,走向主流与商业
另外一方面,从实践出发,不管是台湾的赖声川还是大陆的孟京辉还是田沁鑫,都是在往主流和商业戏剧上靠。赖声川的团队能把《如梦之梦》做成一个商业戏剧,确实是一个成功。有时候,我觉得赖声川独具慧眼,能挑中胡歌,那时候胡歌还没有那么有名;现在你看,《如梦之梦》一开票马上就卖完了。
孟京辉比较特别,他做的是小剧场形式的商业戏剧,他的作品孕育都是以蜂巢为核心,运用的要素也是小剧场要素,想要通过戏剧挑战一些东西,用他的话说就是挑战大众审美。《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就非常具有挑战性。他一直坚持从小剧场出发,然后把小剧场的戏带入大剧场,据说他们在全国付工资的人有100人左右。这几乎是个剧团的概念了。孟京辉的作品可以在全国同时进行很多演出,他的蜂巢一年演出将近400场,有下午场、晚上场甚至有午夜场。
4、IP剧:从《三体》中看到希望
此外,IP剧是这些年大陆剧场必须重视的一个产品形态。最开始,我也看不上IP剧,觉得《仙剑奇侠传》《盗墓笔记》不就是cosplay么,怎么能是戏呢?但等我看到《三体》的时候,我觉得是个戏了。虽然《三体》舞台剧的舞美还是很粗糙,但确实是个“戏”了,而且有“三体”这么一个我觉得具有爆发性增长点的好IP。既然第一部做成了,只要不放弃做好内核的想法,我相信它会成为市场当中很大变量。《三体》演出时,2000多人的北京展览馆剧场被坐满了,做戏剧的知道,北展剧场的技术要素很一般,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做出这样的规模很不简单。从上海出发做到北京,我相信未来的路会越来越远。

5、戏剧节:作品风格雷同,观众固定
记得2000年做剧场时,我们希望有很多很多的戏剧节,但有了戏剧节之后,我们又觉得“哎呀太重复了”。不管是乌镇戏剧节、青年戏剧节还是南锣鼓巷戏剧节,并没有让戏剧更好,反而有些下降的感觉。一般来说,戏剧节的观众比较固定。我总觉得好像他们对于戏剧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戏里有一点点他要的东西就够了。在戏剧节低额的补贴之下,往往也就演出两场,也还是有观众,能够维持运转,但这不代表他的作品质量就好。
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当政府补贴和戏剧节越来越多的时候,戏剧的质量其实没有往上走。
6、小剧场:走向泛政治化,政治成为其消费方向
另外,尽管现在小剧场很难做,我还是看到个别小剧场的演出在创造一些新的东西,比如当年看《驴得水》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在美学上有自己的追求,内容上也有自己的想法,很有意思;去年看《造王府》,包括今年在鼓楼戏剧节看《搁浅》感觉也是这样:它们都不够成熟,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都有自己的追求——内容上的美学上的。我在想也许小剧场的内容与美学潜藏着一些变化,家庭,职场、爱情做得太多了,观众可能没那么大兴趣,但观众对泛政治化的表达还是有兴趣的。当然不要太犯忌。从小剧场的特殊性来说,它的消费方向在变。
大陆戏剧如何创造新的可能?
如何重建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创作是一场博弈,是创作者和观众的内心节奏、想要的东西之间展开的博弈,创作者在博弈中才能成长。现在的问题是,市场的空间很少,所以你博弈的力量要更大才行。我很担心现在在戏剧创作上资本进入越来越少。怎么能够说服社会资本流向你,同时在里面留出创作空间,这是接下来最大的任务。在政府力量重新回来的情况下,必须要创作新的社会投资的范式。
再说美学风格,我觉得其实不是要谈论“风格”,而是要重新思考艺术和生活的关系,要在今天重新定义“艺术是什么”。我看丁一滕的作品时,感觉上这种风格很符合国际戏剧节的口味,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长远呢?我很怀疑。我们的年轻的创作者习惯于用国际戏剧节的标准来定义艺术,但是国际上艺术的风格也是会来回变的。这个时候,我还是愿意回顾一下贡布里希的话:“世界上从来没有艺术,只有艺术家。”这句话太深刻了——艺术的风格会变,所以艺术的定义不是恒定的;它要求艺术家要学会在自己的时代找到艺术的风格,去体会它,去表现它。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有三种形式:艺术反映(或者再现)现实、艺术对抗现实、艺术介入现实。这三种形式现在都受到了挑战。
“艺术反映现实”是现实主义戏剧,这是最早被挑战的,一次两次三次,直到2013年话剧《雷雨》出现观众笑场,那是最直接的一次。
“艺术对抗现实”是孟京辉的道路。他和现实主义之间一直有着对抗性——他说的现实主义是“溅满泥浆的现实主义”。他非常清楚,他要对抗的就是所谓人艺的表演风格。但这一点上,丁一滕就不如他深刻。我想问的是,现在所有走先锋艺术的人,你们对抗的是什么,你们自己清楚吗?如果清楚,你们自己的意念够强大吗?丁一滕在《拥抱麦克白》里把“你们就是看不懂我的戏”印在T恤上,但是他在演后谈上表现的态度比孟京辉温和得多,所以我认为他对抗的动力其实不是很强。我这么说一点没有贬低丁一滕的意思,只是他的强烈的表达能力让我举他做个例子。我只是想说,这一波的实验艺术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在动力。说到这里提一下帐篷戏剧了,帐篷戏剧虽然充满对抗性,但是它的对抗性实际上来自60年代的社会运动,当社会运动烟消云散的时候,我们现在再来演这个戏,其实只有表演性,而没有内在动力。

从帐篷戏剧正好说到“艺术介入现实”。上世纪60年代,日本的帐篷戏剧彻底颠覆了剧场这一现代建筑的稳定性,而其在象征意义上更是在颠覆与“剧场”这一现代建制伴随在一起的一整套的演剧体制:文化地位,演出生产,组织形式,消费方式。而“艺术介入现实”的问题是:现在怎么去介入现实?它现在介入的方式,还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巴西《被压迫者剧场》的戏剧理论出发而来的。我怀疑这种方式还能适应现在的现实吗?现在和当时的生活之间已经有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我们现在要思考的是,艺术要如何重新与生活建立关系,不管是反应、对抗、还是介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