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声Pro 赵铭
在社交媒体让人们对东南亚产生某些刻板印象的时候,纪录片《出海》展现了越南的另一面。
时光机理论说,越南如今的经济发展阶段,约等于二十年前的中国。老王、黎叔、涂与豪,三个中国人选择背水一战,来到越南创业。镜头记录了他们在疫情之下如何撑下去,「跳入苦海,是为了到达更好的彼岸。」导演花总这样总结。
这是继《口罩猎人》之后,花总导演的第二部纪录片作品,由他与腾讯新闻夏至工作室联合出品。最初看到素材,打动监制孟田芳的是场记中的一句话:在出海的幕布下,中年创业的困境,步步求生的压迫感,孤注一掷的决绝,都是这个被疫情冲刷了三年的世界的注脚,「这几年有千言万语想表达,它让我们找到了一个出口。」
《出海》并不像《口罩猎人》一样跌宕起伏,更依靠的是人物与观众在精神层面的连接。孟田芳说,经过疫情三年,相比猎奇的内容,人们更需要一种恒定的、安定的、稳定的价值。
在和花总合作的过程中,她发现,花总身上很突出的特质是「有真好奇」,「对于内容从业者来说,真好奇才能激发出最真切的关怀、关心、关注以及表达动力。」

在成为纪录片导演之前,过去十余年,从2011年在微博因给官员鉴表一举成名开始,打假世奢会,写《装腔指南》,通过《杯子的秘密》揭秘酒店卫生问题,在21世纪初涌现的这波初代大V中,花总是一个难得在社交网络穿越周期的存在。
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带着一种悲悯的底色,在公众视野外,花总支教、卧底珠三角的工厂、寻访援越抗法老兵墓地,对他者和公共问题保持关注。
另一方面,社交网络和舆论场的快速变化,以及因打假世奢会造成的对自我影响力的幻灭,让他选择了一套更安全的KOL生存哲学——怂一点,以长期主义为第一原则,先保证活得久,再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和作品。
作为一个1997年就开始上网、和互联网同步成长的原住民,从博客、微博、公众号再到视频形态,花总努力适应内容产生方式的改变,生产高质量内容。他称自己为「脉冲型网红」,每隔两三年交一次「作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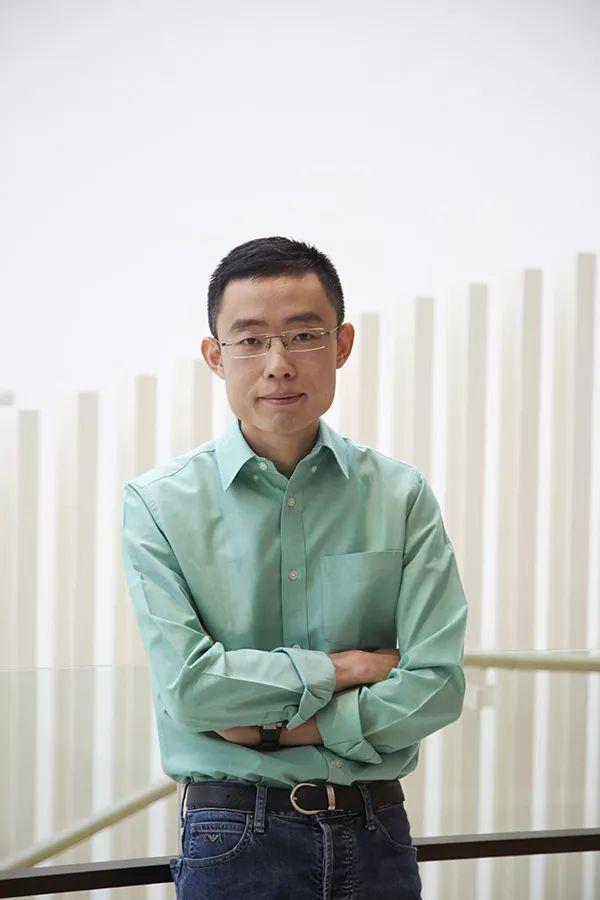
花总
但相比更为流行的Vlogger,花总至今给自己的定位都是Blogger,那指向了他怀念的时代,有一种古典的江湖气。
21世纪初,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也以同样速度在两极分化。基于市场转型相关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的错位,早期的互联网折射着人们对于乌托邦的想象,成为一种建构替代性认同、界定与肯定共同价值的一种方式。
改变了Web1.0时代信息自上而下的生产方式,Web2.0的生产主体拓展为个体,博客让个体得以写作记录时代,满足了花总年少时想成为一名专栏作家的愿望。
从具有「启蒙意义」的博客,到知识分子主导、「围观改变中国」的微博时代,那几年,花总在社交媒体春风得意:给官员杨达才鉴表,最初只是花总验证自己对互联网传播规律的一次实验;公众号爆发前夜,花总又通过《装腔指南》系列文章成为阅读量最高的账号之一。
直到打假「山寨社团」世界奢侈品协会,在与对方长达三年的纠缠之中,他意识到,面对无赖,所谓KOL只是一种幻觉。他也停下了《装腔指南》的更新,再也无法回到自认为高人一等的情绪里,重新在社交媒体上找自己的位置。
世奢会对花总等起诉败诉前一年,微博发展细分垂直领域,公知色彩被淡化,中小网红和圈层文化取而代之。
随着BBS、论坛、博客成为黄金时代留下的遗址,许多曾经推动黄金时代形成的面庞也逐渐模糊,有些人退出了互联网江湖,有些人走向了另一个方向。
于一代与互联网共同度过青春期的网民来说,就像黄舒骏在《改变1995》里唱到的,「属于我们的精彩,早已不复存在。」
最近几年,则是被算法布控的、充满茧房和割裂的舆论场,越来越和人们最早对互联网的想象背道而驰。
「作为第一代互联网人,没有人教我们该怎么做,都是一点点摸索。从1997年第一次上网到现在,媒介环境已经翻天覆地。有些人还活着,但已不在互联网中。」花总说。
他依然保留着对一些问题的关怀,但也承认自己不够勇敢,一切的前提是要活得久。
他视账号为线上生命的延伸,「怂一点比刚一点好」,为此他的大号「花总丢了金箍棒」只间歇性发布作品,更多的时候在小号「花总」里卖萌、放大自己的宜人性。但骨子里他还是一个骄傲的人,看不上那些洗粉的意见领袖,和粉丝保持一定距离。
 花总的小号
花总的小号
「活得久并不伟大,只能说明你鸡贼。」他将自己的不勇敢和畏惧和盘托出,这种坦诚也带有了一种自我保护。
前段时间,花总看了网剧《漫长的季节》,感慨于大时代下个体力量的渺小。「但这些个体倔强的抵抗,让他们活得像个人一样,这点非常非常打动我。」
《口罩猎人》主角林栋曾告诉花总,如果不是小时候吃不饱,也不需出来搏命。花总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觉得「苦」不仅仅限于具象之苦,而是人的命运被推到某个位置,成为众多利益的交织。在这个层面,回看多年前的杨达才、欧阳坤,很多人在一个转型期,卷入了宏大、残酷的游戏中。生不由己,又不完全是生不由己,赌性、贪婪也掺杂其中。
某种程度上,花总也是一个在特定时代被卷入游戏的玩家。在见证互联网进入中国所造就的技术创新、文化变迁、舆论变化的同时,也一次又一次或主动或被动地,进入到由时代洋流和社会情绪促成的网络漩涡之中。目睹了许多人走上巅峰、又消失不见,人来人往中,努力找到自己的位置。
前几年,意识到非虚构报道在未来会影像化后,花总开始寻找视频上的出路。相继与凤凰网、新浪微博、腾讯新闻合作纪实视频,花总负责输出观点视角策划和前期拍摄,平台负责剪辑制作和运营传播,成了他生产网生视频的一种常规模式。
他称自己为故事猎手,最享受的就是在森林里hunting故事。面对被采访者,首先是江湖的标准,其次才是纪录片的标准。比如基于对舆论场的了解,在必要时保护自己的采访对象。
他给自己印了新名片,title是Documentary Filmmaker。意识到自己步入中年后,新的阶段,他不愿再通过「内容」去炫技,证明自己作为流量捕手的能力。现在要做的是「作品」,能立得住的作品。
当谈起他曾经的青年时代,谈到自己不会像从前一样愤怒时,他陷入了某种虚无。昔日的记忆还没散去,他不想再触碰,宁愿用日常生活中那些浅表的情绪,去遮盖内心深处的巨大波澜。
尽管一直否认「野心」的存在,但花总承认,自己不希望这个世界被低级流量玩家所操纵。「大家迟早都会变成老王,你唯一能做的是变成老王之后,心里是一潭死水,还是有个火种。」
1、首先是江湖标准,然后才是纪录片的标准
新声Pro:为什么这次关注出海越南的公司和创业者?
花总:商业,越南,都是一个背景幕布,把地理和行业剥离之后,就是老中青三代人求生、创业、上岸的故事。和《口罩猎人》还不一样,那个还有一些商战的色彩,这次没有特别浓郁的MBA案例式的东西。
新声Pro:《口罩猎人》和《出海》这两个纪录片似乎都和商业有关。
花总:一定是利益越集中,纠葛越多的地方,故事越多。
新声Pro:你之前复盘的时候提到过,成片里关于人的部分呈现的有点少?
花总:对,这是我这种拍摄方法的局限。我属于守株待兔式记录,享受的就是Hunting的过程。完全没有脚本,可能你跟了一个月,都不一定有波澜起伏的戏剧性冲突,但人物的很多性格是要遇到事情才能体现。
这种拍摄方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只能等,最头疼的就是,带着几块电池一直拍到没电为止。拍完回去以后再痛苦一遍。哪怕没有故事我也得做场记,我就重新把所有素材过一遍。
我比别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熬得起,只要签证没有过期,只要那个人还让我拍,我就能三个月、六个月一直拍,总能拿出东西来。
新声Pro:不用计较成本吗?
花总:我不是为了那个片子才活着,就算我不拍片子,我也很想去越南。拍片本身没有成本,都是单人单机位。我最多的就是时间。
新声Pro:但你会焦虑自己两三年没有产出片子。
花总:我的压力源于我是一个脉冲型网红,隔两三年出来交一次作业。我还是有很强的虚荣心,第一,我不是谁能定义的一个人,这是我骄傲的一个地方。第二,只要我认真,我能做出不错的东西,别看我平时嘻嘻哈哈。第三,我不比谁差,我会经常定一个目标,看到别人做了什么我就心想,我也能做。吹完这种牛,就得把这个坑填上。所以这么多年我有目标,但没有很强的目的性。
新声Pro:目标是什么?
花总:目标是能不断输出一些作品,而不是单纯的内容。因为作品更能满足我的虚荣心,作品能拿奖,内容无非就是爆款。我总不能和别人介绍自己说,这人就是整天上热搜的人,我觉得这是一种侮辱,听起来像这个人是搞流量的人,这不很Low吗?
新声Pro:你当时和林栋、老王第一次见面,怎么介绍自己?
花总:很难,我现在出去拍片都拿名片。自从《口罩猎人》之后,我的名片上的title就是Documentary Filmmaker,二维码里是我的自我介绍,告诉他们我多少是个人物,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你得认真对待。
林栋一开始不怎么上微博,可能觉得我就是个微博大V,可以帮忙宣传一下。
新声Pro:选择采访对象的时候,你有什么标准?
花总:不是我选的,都是时间或者命运推给我。要有眼缘。
我也是一个老江湖,在商场上见过很多人和事,有基本的判断,聊几分钟就知道这个人有多少量。你跟他聊的时候也会判断这个人的开放性。以及他想得到什么?让你拍肯定要得到一些东西。
如果有人想沽名钓誉,想表演,那也没事,有本事你在我镜头面前表演一年?那你很厉害。
我每次开拍之前会提醒他们,关注度和流量是双刃剑,想清楚再决定要不要让我拍,一旦我开始拍了,除非涉及个人隐私和商业机密,否则要对我无条件开放。以及在片子播出之前不能看成片。
他们对我也有一种信任。因为拍摄过程中也会对我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观察,觉得至少被我拍不会太危险。
新声Pro:你做过很多年PR,这段经历对现在做故事猎人有什么帮助或者影响?
花总:我和大部分记者最大的不同是,记者的世界都和新闻相关,本身没有涉足、勾兑过利益,没有设局、破局,是旁观者视角。但我全部都做过和经历过,我和我的采访对象某种意义上是同类人。
所以我也一直和他们强调,我不是记者,但我肯定是懂他们的人。当他们遇到困难和困惑的时候我们还能聊几句。这可能也是我吸引他们的另一个地方。
有些东西他不说我也知道,我甚至会为他考虑。
新声Pro:比如呢?
花总:比如黎叔有时候会顺口说越南人怎么样,类似这种明显可能埋雷的表述,我就会谨慎建议让他换个表述。过程中会建立我们更深的信任,他会意识到我在保护他。
《口罩猎人》里我问了林栋三个问题,大家说我很傻白甜,其实是为了帮他避雷。在观众质疑之前,不如我先来问。
还有采访对象打孩子,我会主动回避这种画面,只录声音,不让孩子窘迫的一面暴露出来。

《出海》中的三位主人公
新声Pro:这些直觉是公关思维带来的吗?
花总:其实也不是,我觉得是江湖气。但换了别的导演,可能不会干涉,但会冲出去拍。我是会去干预的,并且主动不拍。
新声Pro:那你会不会担心对真实性有影响?
花总:我觉得不妨碍。首先不影响剧情走向。
我的干预都停留在不要因为某一个表达在社交媒体被放大被喷。我在拍片子的时候,会想这个镜头放到微博上会不会被人误解?明显对主人公造成不好影响的,我会尽量避免。但我不会操纵剧情。
其次,什么可拍什么不可拍,我有自己的标准——首先是一套江湖标准,然后才是纪录片的标准。
我一直是Vlog的拍法,记录我的生活。只不过有时候我登上别人的岛转悠。我不是记者姿态,是熟人姿态。
之前想做的《花总鉴识录》卖点也是带着摄像机走入大佬的生活中,揭示真实一面,不是采访。我以前也会去这些人的中间,只不过这回我带了相机,这种视角更有意思。
新声Pro:从《口罩猎人》开始,你一直想尝试网生视频,现在有哪些进展?
花总:社交媒体就是由流量组成的。我一直想把互联网时代内容的书名号改成双井号,比如《出海》就是#出海#。你拍出了一个内容,同时你也在设定议程,这时话题不是宣发的产物,网生视频本身就是一系列话题的集成。我们不能操纵舆论,但可以引导话题。
我一直想要有更大胆的尝试,让运营本身作为作品,但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
2、我希望花总这个帐号活得久一点
新声Pro:不过你给自己的title还是纪录片导演。
花总:那只是一个title。第一个title是Blogger。
新声Pro:为什么你会一直沿用Blogger的标签?
花总:我很喜欢Blog的定位,我是最早一批博客。博客是自媒体时代的一个标志,类似于专栏,可以在里面稳定输出。更早的时候你想成为专栏作家门槛很高的,我大学刚毕业,曾经很想成为一个作家,但那时候是传统媒体筛选的年代。
新声Pro:那你会很怀念那个时候吗?
花总:我其实还挺怀念的,有那种特别古典的江湖气。
现在大家缺乏耐心和温和,那个时候面对面交往大家讲体面,因为现实中大家会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善意,有沟通的仪式感。
但你在网上隐藏在IP后面,有些人你不知道他生活中什么样,上网他就敢大放厥词。互联网有时候降低了沟通成本,但也制造了戾气。
新声Pro:作为KOL,怎么面对这种媒介变化?你现在还在做直播,直播比较危险,有时候你没注意哪句话就被人断章取义。
花总:人设不是维护出来的,人设是不断表达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我做两百场直播,只有一次差点翻车,就是因为嘴瓢。后来当天晚上我就公开道歉了。
其实我挺郁闷的,我的粉丝没怎么样,但很多粉丝之外的人冲进来批评我。然后我就也拧巴起来,收回我的道歉了。我本意不是那样,也道歉了,你爱咋咋地。
新声Pro:你之前也提到过直播有很强的饭圈属性。
花总:粉丝文化很有意思。我在微博有很多铁粉,我维持两个交往原则:第一,不跟粉丝线下见面。第二,如果粉丝对我太热情、忠诚度太高,我就不会理他了。因为我发现在互联网过度沉迷一个人,这件事是有问题的。
我经历过这种事,有人会经常给我发私信,不堪其扰。他们会想象出一个我,可能不断自己刷漆、美化。一旦情况和想象不一致,就会开始攻击。
还有一些铁粉,我每次开一个群他们都会出来「占山为王」,后来我就不太敢进群。当你成为一个蠢萌博主,时间久了会这样。
新声Pro:想穿越周期的话要维持稳定人设。那个稳定的东西是什么?
花总:我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花果山总书记,那时候我是PR,精通传播规律,社交媒体刚出来,我想验证我那套洞察,就鉴表。那时候我和记者说,花总不是我本人,是我扮演的角色。
后来,世奢会事件,报纸上登了我的照片,我的现实身份和网络身份一下被击穿了。对我和我父母冲击都很大。那时候我才意识到,他不是我扮演的角色,他就是我,不管我认不认。
所以后来我说,花总是我线上身份的一个延伸,开始认真的把它当成我的一部分。
我们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代同时有线上和线下生命的人。将来有一天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有数字遗产,我希望它是一个ID,而不是一堆ID。
我觉得体面的线上生存方式就是有一个名号,既承载你输出的内容和作品,也代表你的人格,多多少少会反映你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所以不愿意去做特别短视的事情。
不是说我不想赚钱,我也会羡慕嫉妒,但回头看,十多年有多少人消失不见,当然有些人是很勇敢,我也很佩服,但我还是希望它能存活的久一点。不是因为恋战,而是,它就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哪怕他以后再转型,为什么不把他可延续呢?
所以那个最稳定的东西就是我自己。
新声Pro:花总跟自己的差别到底有多少?
花总:他是我的一部分,但在社交媒体上,天然带有一定表演型。有时候你像个艺人,但实际上你又不是,这是比较有趣的地方。我们第一次成为KOL,一个数字生命,要学会怎么去做。也许将来我的小孩也开始在互联网开启数字人生的时候,我才能告诉他,有些地方路不要走,有些选择不要做。
但我们这代人没有人教我们,都是一点点摸索起来的。我1997年上网,到今天翻天覆地。很多人还活着,但他们在互联网上已经消失了。
新声Pro:哪一部分是表演出来的?
花总:卖萌,宜人性。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比较直接、不怎么宜人的人。但我在互联网上就特别通情达理,和蔼可亲。比如我做直播,观众要么就是缺爱,要么就是缺钱,为什么大家愿意来?我像个知心姐姐。
我打开我同理心的那一面,我特别擅长。一个好PR一定是一个情绪的捕手,不单是故事捕手。作为纪录片导演,你也可以感受到那个人情绪的变化和需求。
新声Pro:你现在看到大家的评论还是会玻璃心。
花总:会啊,我天天搜自己,还能看到黑粉。
新声Pro:对你来说会是困扰吗?
花总:不会,这是KOL应该承受的。我会管理自己情绪,表面的情绪我希望越多越好,我就关注在鸡毛蒜皮情绪波动上,内心深处不要有大的波澜。
我真的承受不起或者不愿面对那种起伏很大的、幻灭重生的波动。我不想有世奢会那种经历了。我宁可被人误会,淹没在日常的情绪,喜悦,嫉妒,虚荣里。
3、不想让世界被低级流量玩家所操控
新声Pro:你很喜欢周浩导演,觉得他有一种社会关怀在里面。
花总:我觉得周浩导演很有个性。我喜欢真实的人,真实记录,真实表达的人。周浩导演这方面做的比我好。但我成不了他,我们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我们的战场和环境也不一样。
新声Pro:你会从他的作品里学习什么?
花总:找感觉。很早看过《厚街》《差馆》,我觉得他的视角对我很有帮助。镜头语言背后是有思想和思考的,在他那个年代很多纪录片掌镜人就是一个摄像师,周浩是作者,这对我有启发。
还有《普京访谈录》,手持运镜然后捕捉人物的神态和神情,我就在《出海》里也有大量长焦怼脸镜头。我特别喜欢盯着一个人的眼睛或者注意他手里的小动作,包括用从镜子里反射的机位,这是我的观察方式,周浩作品里也有很多类似镜头。在我没有成为一个影像创作者之前,他对我多少有影响。
新声Pro:影像美学这一块还有哪些对你影响比较深?
花总:美剧,最近的《继承之战》,我在微博给了他极高的评价,是电视美学的巅峰,可以写入影史的。那部美剧也是伪纪录片式的。
新声Pro:提到伪纪录片,我记得你还很喜欢《宇宙探索编辑部》,你有什么感触?
花总:我的感触就是中年人最能理解中年人。所谓中年人就是我这一代人。我这一代都变成中年人了,不可想象,以前我都觉得自己是小孩,不用背负那么多责任,可以去折腾。
忽然有一天发现,你该去承担具体的责任了,连父母最在意的还没有满足。很多人说你做了我们不敢做的,那是因为我放弃了很多类似组建家庭这样的责任和义务。这是真的自由吗?只是逃避或者交换的自由。
所以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还没有找到答案。
新声Pro:你以前特别讨厌被认定为什么人,成了应激反应,别人给你贴什么标签,你就不继续干什么了,那纪录片也只算是你旅程中的一个小部分吗?
花总:但后来你会慢慢折腾不动,你也不想应激了,人是会累的。
新声Pro:之前听说过一个词叫35岁必死。
花总:一直都是,做那么多事情,你觉得能改变或者推动一些事情改变,但发现如果要产生效果,是要留给时间的。
我后来做了很多事情,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率性,有时候还是特别愚蠢。我不能叫理想主义,我觉得我不配说这个词,因为我一直都很鸡贼,越好的公关越鸡贼。
新声Pro:你每次采访都很坦白。
花总:也不是坦白,很简单,如果你说自己理想主义,就是在给自己挖坑。如果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可能2007年支教结束就留在那里了。
新声Pro:这也是另外一种自我保护?
花总:和林栋一样,先主动说出来。核心就是两件事,第一,我是一个没什么野心的人,理想主义者可能还有推动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愿望。
对我粉丝来说,我人畜无害。当时我写装腔指南,被大家想象成另一种人。那样的人设最有商业价值,我比谁都适合经营那样的人设,但不值得。
我今天顶着一个秃头的头像,开自己发际线的玩笑,就是人畜无害嘛。你想活得久一点,才用这种姿态,而不是其他意见领袖,那种对我太简单了。为什么要蠢萌呢?当然我也确实蠢萌,但我也是考虑过的。
活得久一点说明你还没有翻车。
新声Pro:为什么活得久这么重要?
花总:这不是很值得吹牛的事情,只能说明你很油腻或者老江湖。今天遇到什么事情,你让我服软,我马上服软。
我和以前不一样了,十年前世奢会的时候我还充满愤怒,说怎么不去抓真正的坏人?到了今天,我就会先不吃眼前亏。
当时是不是一个很骄傲或者很fighting的状态?所以我才说大家迟早都会变成老王,但你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变成老王之后,心里是一潭死水,还是有个火种?
新声Pro:那你有火种吗?如果我用你问老王那个问题去问你,你觉得你的本心是什么?
花总:我觉得可能还有。我没有特别明确的本心,我只知道自己不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不想变成壳特别重,但里面没货了;以及特别没品,一个爹味儿特别重的人。
我很瞧不上很多聪明的人通过洗粉的方式试图去操控一些东西,来换取一些东西。我在网上很少和人起冲突,但甚至因为这种事和别人起过严重冲突。
新声Pro:你想活得更久,是不是也因为你内心深处还是想像一个知识分子一样影响别人。
花总:没有,真的完全没有。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说话有人听。别人说起来,是个纪录片导演。
新声Pro:那你内心深处的价值感来源是什么?作为内容创作者,总有一些让你感到满足的点。
花总:以前是炫技,维持我内心深处某种优越感——我是那种想红就能红的人,懂网络传播规律。
现在对我来说,我建构的合理性就是不用再去吃流量饭,反过来去做一些不那么流量的事情,我需要有作品,当然最好同时有流量,能取悦我自己。我对于什么是好的作品还是有很清晰的标准。
新声Pro:好作品的标准是什么?
花总:第一,故事的内核。第二,这个故事能不能解决一些问题?对,还是有一点野心的。就是不想让世界变成被低级流量玩家所操控的样子。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