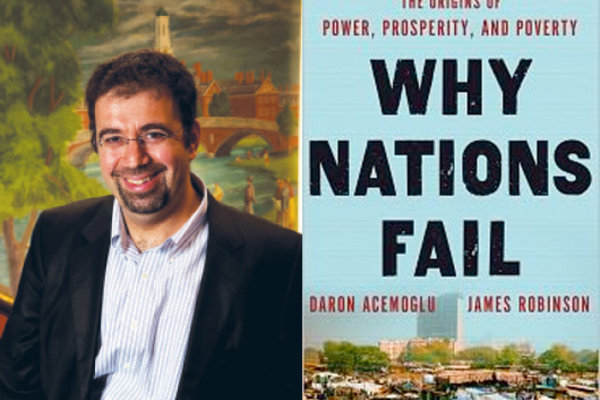
20世纪下半叶,民主的主要威胁是军人。举凡阿根廷、巴西、智利、泰国及土耳其等新兴民主国家,均有军事政变导致专制复辟的情形发生。对于那些羽翼未丰、希望避免军人干政的民主国家而言,西欧及北美的制度体系——其特征是将所有政治权威交予经由选举产生的文官政府——是其效法的对象。正如政治学者胡安·林茨(Juan Linz)和阿尔弗雷德·史蒂芬(Alfred Stepan)的经典论断所言,此为确保民主成为“国内唯一的游戏规则”的不二法门。
至于西方的制度体系中是否潜藏着对民主的另一威胁——即个人统治(personal rule)——则少有思想家去关注,所谓的个人统治,是指文官主导的国家制度体系(如官僚制和法院等)处于行政首脑的直接控制之下,国家利益与统治者利益之间的界限也开始模糊化。大部分人相信,这种情形只存在于那些最坏的独裁体制当中,如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治下的扎伊尔,丹尼尔·阿拉普·莫伊(Daniel arap Moi)治下的肯尼亚,或是萨尼·阿巴查(Sani Abacha)治下的尼日利亚等。根据这种思路,权力的制约与平衡既已深入西方制度体系的骨髓,我们便无需为这种篡夺而烦恼。
然而,如今我们却开始发现,现代民主也有其自身的软肋——这一软肋并不在于它无力挫败某个军官团的政变阴谋,而在于国家制度体系的内部朽坏,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统治的抬头。个人统治的典型案例包括查韦斯治下的委内瑞拉,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和埃尔多安治下的土耳其。但它们与前文所提到的那些赤裸裸的独裁体制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掌握大权的政治强人是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他们在相当一部分本国人民心目中的合法性比其它的一些独裁者要高得多。不过,这几个国家的案例同样表明了个人统治的兴起将会不可逆转地破坏国家制度体系,让民主沦为空头招牌。现在,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也极有可能重蹈这一覆辙。
在政治目标与统治策略上,特朗普与查韦斯、普京和埃尔多安有不少相似之处:一是不甚尊重法治或国家制度体系的独立性,倾向于认为它们碍手碍脚;二是模糊了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界限;三是不善于听取批评,且历来有一套回报忠诚的策略,这可以从他的高层人事安排中窥见。这一切的背后,是对自身执政能力自信爆棚的心态。
令美国对此威胁浑然不觉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思维定势:我们拥有着举世闻名的强健制度体系。美国当然有很好的制度基础和独特的权力制衡措施,这是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土耳其望尘莫及的。不过,面对当前的威胁,这些所谓的优势其实帮助不大。目前,美国的制度不单是缺乏对特朗普的防范,在某些情况下它甚至还可能放纵特朗普。
在美国的制度中,针对个人统治的第一道防线,就是其一贯引以为自豪的“三权分立”。立法机构——议员选举与总统选举相互独立——具有限制总统越权的功能;在总统与国会分属不同党派,议员能够遵循各自选区选民的意愿,及自身所奉行的政治原则时,这种制约的确是有效的。
不过,放到今天来看,情况则未必如此,因为两党之间的政治极化(polarization)程度是史无前例的,而党纪方面亦有重大变化。如此一来,正如诺兰·麦卡锡(Nolan McCarty)、凯斯·波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塔(Howard Rosenthal)三位政治学者在《极化的美国》(Polarized America)一书当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超越本党立场的可能性很小。事不凑巧,这种”党性猖獗“偏偏又出现在了一个最需要国会来约束总统的时间点上。然而,考虑到共和党已在大部分议题上围绕特朗普作了调适,如果现在还期待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能够坚守原则,对特朗普的人事安排及政策动议进行严格把关,可能就太过乐观了。
如此一来,相应地,作为三权分立的另一大支柱,司法权对总统权力的约束也就未必能稳得住阵脚。事实上,美国的司法独立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更多依赖于习惯而非规则。总统不仅可以提名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和联邦上诉法院的法官(这是一项总统的专有权力,特朗普一定会想方设法让它物尽其用),也能通过总检察长的提名来控制司法部。作为制度性的约束,国会原则上可以拒绝不适宜的提名人选,但如前所述,目前来看它几乎没法去动摇特朗普的如意算盘。以此观之,司法部门在特朗普面前同样是软弱的。

话说回来,就防范个人统治而言,美国最大的弱点还是在于总统与一些核心政府机构的特殊关系:这个核心就是官僚制自身。在其它许多国家,如英国和加拿大,大部分行政官僚以及级别较高的司法官员,都是不持党派立场的公务员,国家制度体系的日常运转总体上不会被行政首脑试图确立个人统治的企图所影响。但放到美国就不一样了,举凡民事及司法等部门,共有4000来个职位可供特朗普任命,这从根本上导致官僚制有可能被”量身打造“来为特朗普的个人利益服务。这样的权力可能是连查韦斯、普京和埃尔多安都没法轻易获得的。譬如,埃尔多安就还在绞尽脑汁地推动修宪,想要从法律上确认自己的实权总统地位,尽管他的真实权力已经不算小了。(土耳其目前实行议会内阁制,总统原为虚位,行政首脑为总理——译者注)
美国为何在特朗普的威胁面前这么无力?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父当初就是这么设计的。政治学者伍迪·霍顿(Woody Holton)在其著作《不守规矩的美国人与宪法的起源》(Unruly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nstitution)一书中指出:作为美国立国的重要文献,《联邦党人文集》不只强调了三权分立,汉密尔顿、麦迪逊和华盛顿等诸位国父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削弱《邦联条例》所规定的过大的州权——那让全国几近混乱。就这一点来看,三权分立的意义不过是为了反制总统手中的巨大权力。
在这一点上,国父们成功了,不过只是局部性的。美国总统的权力确实很大,不仅能塑造外交政策,在获得国会支持的情况下更能内政外交两手抓。不过,他还是不能随便侵犯州权,之所以有这一让步,是因为当初立宪时不得不对一些较为强大的州作出妥协,以确保宪法能获得足够的支持。纽约州和加州正是借此开始强烈地抵制特朗普的政策,这两个州的州长都立誓要将特朗普的移民政策拒之门外。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联邦政府的权力逐渐变大,它在国内外事务中都承担了更多的职责,这部分地是由于不可抗力因素,但也有主动选择的成分。比较之下,州权就比18世纪末要弱得多了。就算马萨诸塞和佛蒙特两州不买特朗普的账,勉力维持一些自由派的政策,也没法从根本上阻止包括联邦司法部门以及其它许多要害部门(如涉及商贸、财政政策和外事方面的各部会)在内的政府核心部分被个人统治所腐化。并且,它们也无力改变美国人以及全世界心目中对美国政治新走向的基本观感。
这就把我们逼到了最后的(也是真正的)一道防线上面——国父们当初既没有刻意如此设计,也不是太看好它:公民社会的警觉和抗争。事实上,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美国才会遇到。只有当全社会都愿意行动起来捍卫它的时候,宪法才能够真正成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宪制设计都不可能没有漏洞,还要面对时代所带来的各种新挑战,而这些挑战可能是最初立宪时无法预见到的。
大部分新兴民主国家的一大弊病,是政治参与的缺乏——事实上甚至是主动扑灭政治参与的热情。20世纪,各新兴国家的领袖人物通常都声称自己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但却阻止公民社会发育,打压媒体自由,排斥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在他们看来,这些都不过是动员其核心支持者的手段,用以避免大权旁落。这种做法对本国的民主发展产生了持久的损害。
如我们所见,委内瑞拉、俄罗斯和土耳其都被这些麻烦困扰了好几十年,不自由的媒体和公民社会的孱弱,使得这些国家无力遏制个人统治。在美国的传统中,我们有着自由而不屈的新闻界(以”扒粪运动“为代表)以及充满活力的抗争运动(可追溯到人民党人和进步党人),这对遏制个人统治的滋生有莫大帮助。
当然,所谓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可能会不管用。特朗普正逐渐获得精英和公众的接受,单单”他是下一任美国总统“这个名头就足以令他收获极大的权威和尊重。透过其人事安排、访谈和自媒体,我们密切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时评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们设法去找到那仅存的一线希望,期待着特朗普能以一个温和共和党人的方式来治国。笔者的很多经济学家同行们,也迫切地想要为他提供咨询,以免他真的去实行那些先前所承诺的、灾难性的经济计划。
当之前不可想象的事情变成了常态,很多人就容易丧失或者忽略他们的道德准绳。人们是否会很快地习惯于特朗普的反移民、反穆斯林论调,拍脑袋式的外交决策,以及家国利益不分的倾向呢?这绝不是一个可以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问题。
我们必须不断自警:我们并没有生活在一个正常的时代,我们的那些备受赞美的制度的未来,所倚靠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自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捍卫我们的制度体系。如果我们把它拱手让给了一个意欲成为政治强人的总统,那我们只能够责怪自己。我们自己就是最后的那一道防线。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foreignpolicy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