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传统风俗说,大年三十年夜饭,年初一大拜年,年初二姥姥家……团圆和欢聚少不了美食,味蕾的生长总带着记忆,而“年味”是不是就体现在饮食风俗里呢?你的家乡饭吃起来有什么特色?界面文化(公众号id:booksandfun)今天发布的两篇书摘,分别来自北京作家肖复兴和南京作家叶兆言,让我们看看这一南一北的饮食风俗有何不同。
北京小吃,清真打主牌
北京小吃,绝大多数是清真的。无论是《故都食物杂咏》、《燕京小食品杂咏》等旧书中描写过的那些名目繁多而令人垂涎的小吃,或是新近在什刹海开张的“九城”小吃城,还是传统的隆福寺的小吃店,或者是原来门框胡同旁边的小吃街,绝大多数都是清真的,回形清真文字的招牌,是必须要张挂出来标示的。即使是解放以前挑着小担子穿街走巷卖小吃的,担子上也都要挂着简单的清真招牌。为什么呢?回民,在北京城只是一小部分,为什么却占据着几乎全部的北京小吃的领地?清朝的时候,是北京小吃最红火的时候,旗人并不是回民啊,为什么从慈禧太后到平民百姓的胃口,都被回民改造成清真口味了呢?
那天,我遇到一位高人,他年轻时在北京城南著名的清真餐馆两益轩里当过学徒,解放以后,曾经当过南来顺的经理。没有建菜市口大街的时候,南来顺在菜市口丁字路口南,是当时北京最大的小吃店,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北京小吃。可以说他是一辈子和北京小吃打交道,不仅是知味人家,而且是知底人家。
老先生告诉我,北京小吃,清真打主牌,是有历史渊源的,最早要上溯到唐永徽二年(651年)。那时候,第一位来自阿拉伯的回民使者来长安城拜见唐高宗,自此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与此同时带来清真口味的香料和调料。比如我们现在说的胡椒,明显就是,胡椒的一个“胡”字,说的就是回民,其他如茴香、肉桂、豆蔻都是来自那里。那琳琅满目的众多香料和调料,确实让中原耳目一新,食欲大增。要说改变了我们中国人的口味,最早是从这时候开始,是从这样的香料和调料入味,先从味蕾再到胃口的。
大量西域穆斯林流入并定居中国,是在元代。北京最著名的回民居住的牛街,就是在那时候形成的,他们同时便把回民的饮食文化带到了北京,如水一样蔓延进了人们的喉咙,是比香料和调料还要厉害的一种耳濡目染和潜移默化。写过《饮食正要》的忽思慧,本人是回民,又是当时的御医。《饮食正要》里面写的大多是回民食谱,宫廷里和民间的都有,大概是最早的清真小吃乃至饮食的小百科了。比如现在我们还在吃的炸糕之类的油炸品,在老北京,在汉人中,以前是没有吃过的,那是从古波斯人时代就爱吃的传统清真小吃,如果不是牛街上的回民把它传给我们,也许,我们还只会吃年糕,而不会吃炸糕。


应该说,牛街是北京小吃最早的发源地。
老先生说得有史有据有理,牛街的小吃,到现在也是非常有名的,即使在地下小作坊里没有卫生许可证做着黑小吃的,也要打着牛街的招牌,才好推销。牛街确实是北京小吃的一种象征,一块金字招牌。
过去说牛街的回民,“两把刀,八根绳”,就可以做小吃的生意了,说的是本钱低,门槛不高。老先生问我,知道什么叫做“两把刀,八根绳”吗?我说这我知道,所谓两把刀,就是有一把卖切糕或一把切羊头肉的刀,就可以闯荡天下了。别看只是普通的两把刀,在卖小吃的回民中,是有讲究的。切糕粘刀,切不好,弄得很邋遢,讲究的就是切之前刀子上蘸点儿水,一刀切下来,糕平刀净,而且分量一点儿不差(和后来张秉贵师傅卖糖“一把准”的意思一样)。卖羊头肉,更是得讲究刀工。过去竹枝词说:十月燕京冷朔风,羊头上市味无穷,盐花撒得如雪飞,薄薄切成与纸同。那切得纸一样薄的羊头肉,得是真功夫才行。粉碎“四人帮”之后的80年代初,断档多年的个体经营的传统小吃又恢复了,在虎坊桥南原23路终点站,摆出卖羊头肉的一个摊子,挂着“白水羊头李家”的牌子。一位老头,切——其实准确地应该叫片,片得那羊头肉真的是飞快,唰唰飞出的肉片跟纸一样薄。每天下午五点钟左右,摊子摆出来,正是下班放学时间,围着观看的人很多,老头刀上的功夫,跟表演一样,让老头卖的羊头肉不胫而走。
八根绳,说的是拴起一副挑子,就能够走街串巷了,入门简单,便很快普及,成了当时居住在牛街的贫苦回民的一种生存方式。所以,最早北京小吃是摊子,是走街串巷地吆喝着卖,有门脸儿,有门框胡同的小吃街,都是后来民国之初的事了。
回民自身的干净,讲究卫生,更是当时强于汉人的方面,赢得了人们的放心和信任。过去老北京人买东西,经常会嘱咐我们孩子:买清真的呀,不是清真的不要啊!在某种程度上,清真和卫生对仗工整,成了卫生的代名词。
北京小吃,就是这样在岁月的变迁中慢慢地蔓延开来,不仅深入寻常百姓之中,也打进红墙之内的宫廷,成为了御膳单的内容之一。可以这样说,北京的名小吃,现在还在活跃着的爆肚冯、羊头马、年糕杨、馅饼周、奶酪魏、豆腐脑白……几乎全是回民。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北京最有名的小吃一条街——大栅栏里的门框胡同,很多来自牛街的回民。有统计说,那时候全北京卖小吃的一半以上,都是来自牛街。开在天桥的爆肚满的掌柜的石昆生,就是牛街清真寺里的阿訇石昆宾的大哥。北京小吃,真的是树连树,根连根,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和牛街,和清真,分也分不开。
这样一捯根儿,会发现北京小吃,即使现在有些落伍,还真是不可小视的,它的根很深呢。懂得了它的历史,才好珍惜它,挖掘并发扬它的传统优势。同时,也才会品位得到,别看北京古老,真正属于北京自己的东西,除了藏在周口店的北京猿人的头盖骨,其实并不多,基本都是从外面传进来的。开放的姿态和心理,才有了北京的小吃,也才能够形成北京的性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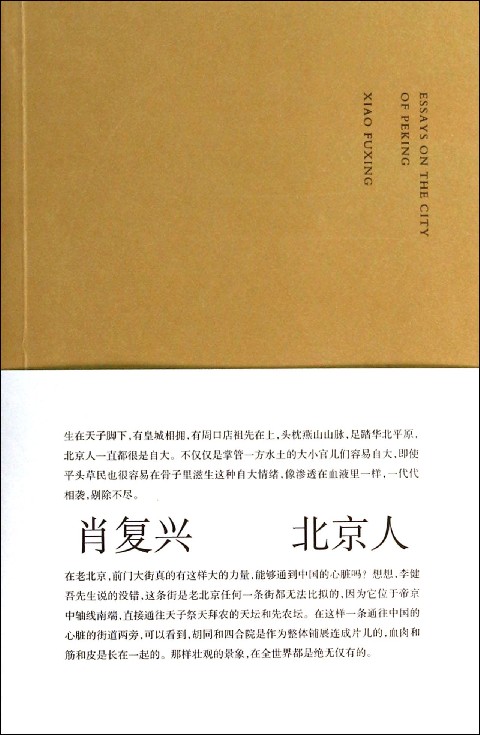
选自《北京人》,肖复兴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版
记忆中南京的吃,不是现在的样子
一
在我的周围,聚集着一大帮定居南京,却并非在这里长大的准南京人。他们都是因为自己的出息和能耐,从全国各地尤其是江苏各地到南京来定居,成为南京的荣誉公民。和他们一起谈到吃,谈到南京的吃,无不义愤填膺,无不嗤之以鼻。南京的吃,在这些南京的外地人眼里,十分糟糕。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感到害臊。我不是一个善辩的人,而且实事求是地说,南京现在的吃,实在不怎么样。事实总是胜于雄辩,我也没必要打肿脸称胖子,硬跳出来,为南京的吃辩护。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反正南京的吃,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差劲、这么昂贵、这么不值得一提过。记忆中南京的吃,完全不应该是现在这样。
今年暮春,有机会去苏北的高邮,自然要品味当地的美食佳肴。8年前,高邮的吃,仿佛汪曾祺先生的小说,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此之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扬州的吃。当时的印象,扬州人比南京人会吃,高邮人又比扬州人会吃。就是到了今日,我这种观点仍然不变。然而感到遗憾的,是今天的高邮和往日相比,也就这么短短的几年,水准已经下降了许多,而扬州更糟糕。
高邮只是扬州属下的一个小县城,扬州似乎又归南京管辖,于是一个极简单的结论就得出来,这就是越往下走,离大城市越远,越讲究吃。换句话说,越往小地方去,好吃的东西就越多,品尝美味的可能性就越大。这种简单化的结论,肯定会得到城市沙文主义者的抨击,首先南京人自己就不会认同,比南京大的城市也不愿意答应。北京人是不会服气的,尽管北京的吃的确比南京还糟糕,在南京请北京的朋友上馆子,他们很少会对南京的菜肴进行挑剔,但是指着北京人的鼻子硬说他不懂得吃,他非跟你急不可。至于上海人和广州人,他们本来就比今天的南京人会吃,跟他们说这个道理,那是找不自在。
还是换一个角度来谈吃。城市越大,越容易丧失掉优秀的吃的传统。吃首先应该是一个传统,没有这个传统无从谈吃,没有这个传统也不可能会有品位。吃不仅仅是为了尝鲜,吃还可以怀旧。广州人和上海人没必要跟南京人赌气,比谁更讲究吃、更懂得吃的真谛。他们应该跟过去的老广州和老上海相比较。虽然现在的馆子越来越多,档次越来越豪华,可是我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承认,我们吃的水平已经越来越糟糕。我们正面临着一个吃的水平的普遍退化的问题。历史上南京的吃,绝不比扬州逊色,同样扬州也绝不会比高邮差。这些年出现的这种水平颠倒,最重要的原因,
是大城市们以太快的速度,火烧火燎地丧失了在吃方面的优秀传统。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用不了太久,在小城市里怕是也很难吃到什么好东西了。
二
说南京人不讲究吃,真是冤枉南京人。当年夫子庙的一家茶楼上,迎面壁上有一副对联:
近夫子之居,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傍秦淮左岸,与花长好,与月同圆。
这副对联非常传神地写出了南京人的闲适,也形象地找到了南京人没出息的根源。传统的南京人,永远是一群会享受的人。这种享乐之风造就了六朝金粉,促进了秦淮河文化的繁荣,自然也附带了一次次的亡国。唐朝杜牧只是在“夜泊秦淮近酒家”之后,才会有感歌女“隔江犹唱后庭花”。《儒林外史》中记载,秦淮两岸酒家昼夜经营,“每天五鼓开张营业,直至夜晚三更方才停止”。由此可见,只要是没什么战乱,南京人口袋里只要有些钱,一个个都是能吃会喝的好手。在那些歌舞升平的日子里,南京酒肆林立,食店栉比,实在是馋嘴人的天下。难怪清朝的袁枚写诗之余,会在这里一本正经地撰写“随园食单”。
南京人在历史上真是太讲究吃了。会吃在六朝古都这块地盘上,从来就是一件雅事和乐事。饕餮之徒,谈起吃的掌故,如数家珍。这种对吃持一种玩赏态度的传统,直到解放后,仍然被顽强地保持着。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名教授胡小石先生,就是著名的美食家,多少年来,南京大三元、六华春的招牌都是他老人家的手笔。胡先生是近代闻名遐迩的大学者大书家,可是因为他老人家嘴馋,那些开饭馆酒家的老板,只要把菜做好做绝,想得到胡先生的字并不难。
过去的名人往往以会吃为自豪。譬如“胡先生豆腐”,据说就是因为胡小石先生爱吃,而成为店家招揽顾客的拿手菜。南京吃的传统,好就好在兼收并蓄,爱创新而不守旧,爱尝鲜又爱怀古,对各地的名菜佳肴,都能品味,都能得其意而忘其形。因此南京才是真正应该出博大精深的美食家的地方。南京人不像四川湖南等地那样固执,没有辣就没有胃口,也不像苏南人那样,有了辣就没办法下筷。南京人深得中庸之道,在品滋味时,没有地方主义的思想在作怪。南京人总是非常虚心,非常认真地琢磨每一道名菜的真实含义。要吃就吃出个名堂来,要吃就吃出品位。南京人难免附庸风雅的嫌疑,太爱尝鲜,太爱吃没吃过的,太爱吃名气大的,一句话,南京人嘴馋,馋得十分纯粹。

南京曾是食客的天下,那些老饕们总是找各种名目,狠狠地大啜一顿。湘人谭延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时,曾以120元一席的粤菜,往六首山致祭清道人李瑞清。醉翁之意不在酒,谭延设豪筵祭清道人,与祭者当然都是诗人名士加上馋嘴,此项活动的高潮不是祭,而是祭过之后的活人大饱口福。当时一石米也不过才8块钱。120元一桌的酒席如何了得!都是一些能吃会吃的食客,其场面何等壮观。清道人李瑞清是胡小石的恩师,清末民初,学术界、教育界无不知清道人之名,其书法作品更是声震海内外。有趣的是,清道人不仅是饱学之士,而且是著名的馋嘴,非常会吃能吃,且能亲手下厨,因此他调教出来的徒子徒孙,一个个也都是饱学而兼馋嘴之土,譬如胡小石先生。我生也晚,虽然在胡先生执教的中文系读了7年书,无缘见到胡先生,但是却有缘和胡的弟子吴伯教授一起上过馆子,吴不仅在戏曲研究方面很有成就,也是我有幸见过的最会吃的老先生。
历史上的南京,可以找到许多像祭清道人这样的“雅披士”之举。在南京,会吃不是丢人的事情,相反,不会吃,反而显得没情调。据说蒋委员长就不怎么会吃,我曾听一位侍候过他的老人说过,蒋因为牙不好,只爱吃软烂的食物,他喜欢吃的菜中,只有宁波“大汤黄鱼”有些品味。与蒋相比,汪精卫便有情趣得多。譬如马祥兴的名菜“美人肝”就曾深得汪的喜爱,汪在南京当大汉奸的时候,常深更半夜以荣宝斋小笺,自书“汪公馆点菜,军警一律放行”字样,派汽车去买“美人肝”回来大快朵颐。其实“美人肝”本身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鸭子的胰脏,南京的土语叫“胰子白”。在传统的清真菜中,这玩意一直派不上什么用场,可是马祥兴的名厨化腐朽为神奇,使这道菜大放异彩,一跃为名菜之冠。当然,“美人肝”的制作绝非易事,不说一鸭一胰,做一小盘得四五十只鸭子,就说那火候,就讲究得不能再讲究,火候不足软而不酥,火候太过皮而不嫩,能把这道菜伺候好的,非名厨不可。
三
如果仅仅以为南京的吃,在历史上,只是为那些名人大腕服务,就大错特错。名人常常只能是带一个头,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人民群众才是真正推动历史的动力。南京的吃,所以值得写一写,不是因为有几位名人会吃,而是因为南京这地方有广泛的会吃的群众基础。民以食为天,饮食文化,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才可能提高,只有得到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才会发展。南京的吃,在历史上所以能辉煌,究其根本,是因为有人能认真地做,有人能认真地吃。天底下怕就怕认真二字。一般人概念中,吃总是在闹市,其实这是一个大大的误会。今日闹市的吃,和过去相比,错就错在吃已经沦为一种附带的东西。吃已经不仅仅是吃了。吃不是人们来到闹市的首要目的。吃变得越来越不纯粹,这是人们的美食水准大大下降的重要原因。繁忙的闹市中,当人们为购物已经精疲力竭的时候,最理想的食物,是简单省事的快餐,因此快餐文化很快风行起来。
吃不纯粹还表现在太多的请客,无论是公款请客,还是个人掏腰包放血,吃本身都退居到第二位。出于各种目的的请客,已经使得上馆子失去了审美的趣味。吃成了交际的手段,成为一种别有用心的投资和回报,吃因此也变得庸俗不堪。吃不纯粹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性循环,消费者不是为了吃而破费,经营者也就没必要在吃上面痛下功夫,于是不得不光想着如何赚钱。
马祥兴是在1958年以后,才从偏僻的中华门外,迁往今日的闹市鼓楼。它的黄金时代,大有一去不复返之势。人们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它并不因为迁居闹市后,就再造昔日的辉煌。马祥兴现在已经很难成为话题,天天有那么多的人,从它身边走过,但是人们甚至都懒得看它一眼。世态炎凉,此一时,彼一时,往事真不堪回首。想当年的马祥兴,酒香不怕巷子深,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装潢,也不成天在报纸上做广告,生意却始终那么火爆。到这里来享受的,不仅仅有那些达官贵人,身着短衫的贩夫走卒也坐在这里,和显赫们一样一杯接一杯地喝酒。人们大老远地到这里来,目的非常纯粹,是想吃和爱吃,就冲着马祥兴的牌子,就为了来这里来吃蛋烧卖,就为了来这里吃凤尾虾、吃烩鸭舌掌。“美人肝”贵了些,不吃也罢。
南京吃的价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昂贵,这么不合理。南京今天的餐饮费绝对高于广州和上海,而南京人的收入,却远不能和这两个地方的人相比。
想当年,大三元的红烧鲍翅,只卖2.5元,陈皮鸭掌更便宜,只要8角。抗战前夕的新街口附近的瘦西湖食堂,四冷盘四热炒五大件的一桌宴席,才5元钱。人们去奇芳阁喝茶、聊天,肚子饿了,花5分钱就可以吃一份干丝,花7分钱,可以吃大碗面条。卖酱牛肉的,带着小刀砧板,切了极薄的片,用新摘下来的荷叶托着递给你,那价格便宜得简直不值一提。
就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四川酒家聚一聚,有个10块钱已经很过瘾。那时候的人,在吃之外,不像今天这样有许多别的消费,人们口袋里不多的钱,大啖一顿往往绰绰有余。吃于是变得严肃认真,既简单也很有品味,人们为了吃而吃,越吃越精。
今日之人,很难再为吃下过多的功夫。和过去比较,大家生活富裕了,吃似乎不再成为问题。不成问题,却又成了新的问题。今日的吃动辄吃装潢,吃档次,吃人情,吃公款,吃奖金,吃奇吃怪,唯一遗憾的就是吃不到滋味。但是人们上馆子终极的目的,还是应该为了吃滋味,否则南京的吃永远辉煌不了。事实上,南京今日的吃,已得到了狠狠的惩罚。我住在热闹的湖南路附近,晚上散步时,屡屡看见一排一排的馆子灯火辉煌,迎宾小姐脸色尴尬地站在门口,客人却见不到一位。如果开馆子的人,仅仅是想算计别人口袋里的钱,人们便可以毫不犹豫地拒绝。真以为南京人不懂得吃,实在太蠢了。
忘不了小时候的事,20多年前,我住的那条巷口有卖小馄饨的,小小的一个门面,一大锅骨头汤,长年累月地在那煮着,那馄饨的滋味自然透鲜。当年南京这样普通却非常可口的小吃,真不知有多少,今天说起来都忍不住流口水。

选自《南京人》,叶兆言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6月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