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拜和ofo的成功带动了一轮共享单车的创业热潮,写字楼、地铁站、住宅区周围的一排排小红车、小蓝车、小黄车,方便了城市的短途出行。然而,近日一篇名为《共享单车,真是一面很好的国民照妖镜》的文章在朋友圈持续刷屏,其中曝光的对共享单车的“花式损毁”,再次引发了一场关于“国民素质”的大讨论。
“素质”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再常见不过的一个词了,它的意涵也十分宽泛——父母带着小孩子在公共场合便溺,我们会说他们素质低;间谍被敌方抓获没能抗住审问,我们也可以说他素质低。那么,当我们在讨论“国民素质”的时候,是否需要先定义一下:素质,指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素质”在今天的常用义,是较晚才被列入“素质”一词的解释之中的。在古汉语中,“素质”本义是“白色的质地”或“白皙的容色”,引申为“事物本来的性质”或“人的先天资质”。直到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划生育和素质教育的推行,“素质”一词的意涵才开始向后天的教养倾斜。而在当代语境下,素质几乎可以涵盖一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思想与行为的全部体现,随着其意涵的不断丰富,它所指涉的内容也变得模糊和抽象起来。渐渐地,它似乎变成了一个空洞而有遮蔽性的能指,一种强有力的、无法辩驳的话语,和一种公开的、去政治化的阶级区隔策略。
从对“素质”一词的谱系学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官方创造并率先使用的语言是如何渗透到民间,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变更其意涵的;也可以从大众对一个词语的使用中窥探中国社会整体的变迁:从人种改良到计划生育,从改革开放到消费社会,从城乡差异到阶级区隔……
从官方到民间:“素质”如何进入日常话语
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素质”一词在中文里通常指“事物本来的性质”,有“天然、未经雕琢”的含义。《管子》有云:“正静不争,动作不贰,素质不留,与地同极。”用以指人的素质时,也更侧重于先天的特性。为了符合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1979年版《辞海》在“素质”词条下还特意加了一则注释,称“对于一个人全面发展而言,先天素质并没有后天的社会环境重要”。

从80年代开始,“素质”的含义和使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素质”开始专门用来指人自身的素质,如涉及非人的实体,比如事物或者机构时,一般不再使用“素质”,而使用“质量”;其二,“素质”的先天意涵被显著削弱了,在当代语境中,影响一个人“素质”的主要是后天的教育和培养;其三,除了个人的素质之外,“国民素质”这一概念开始进入大众语言,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环境变化,也使得高素质和低素质之间的道德区隔开始显现出来。
这些变化产生的主要原因,与两项国家主导的政策——计划生育和素质教育——对日常生活的高度渗透有关,它使得一种官方创造和率先使用的语言,成为了一种强有力的民间话语。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关于计划生育的著作和文章几乎清一色使用“人口质量”一词,而非“人口素质”;1982年《人民日报》首先开始将“人口素质”和“人口质量”当做同义词不加区分地使用,直到1986年,“人口素质”开始全面替代“人口质量”,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口号,则将“人口素质”这一词组作为专有名词固定下来,并在政策的基层宣传和推行中使之深入人心。

而“素质教育”这一说法最早出现在80现代后期。1985年,国家开始推行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提高国民素质,于是“素质教育”作为与“应试教育”或“升学教育”相对的教育理念,作为教育改革的目标和方向,第一次出现在官方话语之中。1999年,“素质教育”被正式写入国家的教育政策。此后,几乎所有关于教育改革的提议,都打着“素质教育”的旗号,尽管其实际内容很可能与素质教育的理念背道而驰。
90年代以来,“素质”不再局限于官方文件和学术著作之中,它开始进入通俗文学、商业广告和日常用语。如2000年的畅销书《哈佛女孩刘亦婷》就以“素质培养实录”作为副标题,这本书一共印刷了63次,创下了超过200余万册的销量奇迹,成为了世纪之交的一本现象级图书。
民间的广泛传播和使用,也丰富了“素质”的意涵。“素质”这一能指在不同语境下,可能对应着不同的所指:在一些语境下,它可以指某一项具体的素质,比如穿衣风格、说话口音、餐桌礼仪或者某一门考试的成绩等等;而在另一些语境下,它也可以指某种抽象的素质,它包含了身体、心理、道德等方方面面,是对一个人的整体评价。而这两种所指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相反,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通过一些细微的观察而断言一个人整体素质的高低,这样所谓的“以小见大”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我们评价一个人素质高或者素质低的时候,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素质”是不是因为含义过为宽泛而变成了一个空洞而有遮蔽性的能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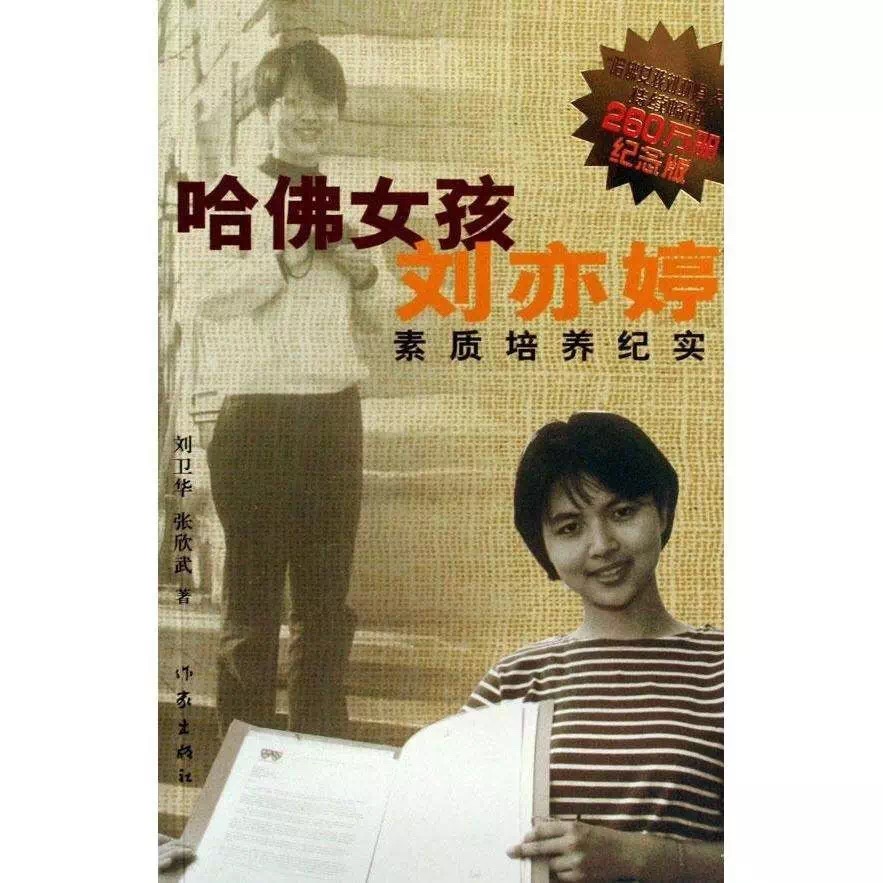
进一步讲,在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竞争越来越激烈,社会上升阶梯越来越狭窄而对于落后的焦虑越来越普遍的今天,素质话语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阶级话语?如果说新自由主义话语是对社会等级和结构性差异的否定,那么素质话语是不是对它的肯定和合理化,素质是不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公开地、去政治化地谈论阶级,甚至进行阶级区隔和歧视的方式
流动人口与独生子女:“素质”是否成了一种新的阶级话语?
在人类学家Ann Anagnost看来,围绕“素质”的话语在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自我形塑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提高人口素质”和“素质教育”这样的口号中,素质主要指的是“国民素质”,甚至带有一定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国家落后屈辱的历史和发展复兴的使命相关;而在当代中国,素质则主要指“个人素质”,它在新兴中产阶级向上追求阶级跃升和向下巩固阶级边界的空间和话语实践中获得了新的意涵。这里涉及到两种人的素质,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外来务工人员)和城市中产家庭中的独生子女——实现向上的阶级跃升,关键在于提高孩子的素质;巩固向下的阶级边界,关键在于隔离“缺乏素质”的流动人口。当代中国关于“素质”的政治,始终在围绕这两个人群展开,Ann Anagnost将他们称为“幽灵般的对应”(Ghostly Double)。
社交网络上很多对于“低素质”的指责都针对于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比如他们身上令人不适的气味,以及毁坏公共财物、乱丢垃圾、大声喧哗等行为。对于这一群体“瘟疫般”的恐惧,主要出于两个原因:首先是农村流动人口庞大的基数和相对较高的生育率,他们是这个国家的“多数”,并且相对于城市人口的负增长而言,这一群体的比例可能会越来越大;其次是他们对城市空间的“入侵”,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进入你上班的写字楼、你吃饭的餐厅、你居住的封闭小区、甚至你的家里,他们是快递员、网约车司机、厨师、保安、月嫂,不仅如此,我们吃的、用的、消费的每一件商品,都经过了无数双他们的手,即便我们看不到他们,他们也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我们陷入了当代城市生活的两难:他们的存在本身,既是便利也是不安的来源,我们很享受快递员每天上门送快递,却不想跟群租的快递员住在一个小区。

很多关于封闭小区的研究都发现,封闭小区的居民通常将“安全”作为选择居住地点的首要关切,然而所谓“安全”并不单单意味着“没有犯罪”,标识清晰的阶级边界、常住人口的稳定和阶级同一性是安全感更重要的来源。因此,作为一种与城市中产同时兴起的新的空间形式,封闭小区的建立和维系有赖于一种“道德空间秩序”,它通过在意识形态层面将流动人口刻画为“肮脏的、低素质的、危险的”,来对他们进行道德上的他者化。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到素质话语替代阶级话语的策略在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机制,通过“素质”的中介,听起来很刺耳、很政治不正确的“我不想和穷人住在一起”摇身一变,成了更中性、更合理的“我不想和乱丢垃圾的人住在一起”。
事实上,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是中国财富积累和经济起飞的主要助力,然而在很多时候,他们都被视为国家进步和发展的障碍和包袱,原因正是他们“素质低”。与此相对,我们的下一代则被视为国家的未来,和家庭向上流动的希望。在Ann Anagnost看来,这似乎可以反映出中国人的某种价值取向——如果素质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价值”的话——孩子的价值体现在他身上的教育投资,而进城务工人员的价值则体现在从他身上被攫取走的剩余价值,而我们对前者的重视和对后者的低估,似乎也从侧面佐证了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的观点:在这个时代,劳动的价值远远低于消费。
在城市中产家庭的独身子女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素质积累的方式:通过不计成本的教育投资和“虎妈式”的“残酷养成计划”,上一代人的经济资本(economic capital)正在通过一种价值转码的方式转化为下一代人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也就是素质。同样在他们身上,我们也看到了素质量化的方式:要么通过官方认可的考试系统量化为分数和学历,要么通过在市场上参与交换量化为金钱或者所谓“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同样是交换、挣钱和谋生,也存在微妙的高下之分,正如社会学家Carolyn Hsu通过对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研究就发现,有两种称谓可以用来指代以做生意为生的人——个体户和商人——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素质”:个体户通常指的是出身农村、教育程度和道德标准较低的人,而商人则被认为是对双商高、有文化并能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的褒扬。在当代语境下,类似“个体户”和“商人”这样的区别称谓依然很常见,最典型的莫过于对“暴发户”的污名和对“创业者”的神化。

而在所有围绕素质的话语中,最值得警惕的莫过于优生学在当代的重临。在民国时期,优生学曾嵌套在民族救亡的时代主题中,一度十分流行,它的基本主张就是一种朴素但十分危险的人种改良计划:鼓励社会上层(优质人种)生育,同时限制底层(劣质人种)生育。
在当代中国,虽然缺少了民族主义的背景,类似的优生学观点却没有失去土壤。在去年轰动舆论的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子自杀事件中,就有很多人摆出“责备受害者”的论调,认为是因为这位年轻母亲“素质低”、“越穷越生、越生越穷”,才最终不堪重负,酿成惨剧。殊不知,这种“多生散养”的模式对于很多农村家庭而言,本来就是一种更有利的生存策略,它与城市中产家庭集中资源、“优生精养”的模式没有可比性,“赚够了钱再生孩子”在个人层面是一种不失理智的选择,而在公共层面却是一种可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对穷人权力的剥夺。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