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以时间与精力来衡量成本,但说到底还是钱。时下流行的生活方式要求人们投资自身潜能,甚至视其为风险管理对象。千禧一代(1990年代出生)的人们的人格正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产物。鉴于各路评论家与分析师甚少参照上述指标来考量年轻人生活,关注经济成本自有其重要性。然而其它类型的成本也不可忽视。原因很简单:经济学家不太会考虑人们竭力与当代资本主义保持同步时所需付出的心理成本,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轻易忽视这种成本。
年轻人之间竞争日益加剧——无论他们是想要当鼓手、大前锋、科学家,还是仅仅不愿荒废人生——这自然会带来更高的经济成本,但也会牵涉到精神健康与社会信任等方面的成本。当人们愈发擅长于变着花样为自己牟利,互信就变成了傻子才会做的事。随着此类风险的升高,我们也在慢慢学会如何“不当傻子”。
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3月发表的“人口与社会趋势调查”显示:自1987年至2012年,美国人对“大部分人都可以信任”这一命题的认可度一代不如一代。20世纪初出生的沉默一代几乎原封不动地将其高信任传给了战后的婴儿潮世代,然而90年代上半期的X世代却并不好过,他们对上述命题的认可度一度降到20%,直到调查结束的时间点才慢慢回升到30%左右。话说回来,X世代较其父母而言还只是变得更加谨慎,千禧一代则怀疑一切:在4年当中,除了奥巴马当选的轻微鼓舞作用之外,这群人对信任他人的认可度始终在20%左右徘徊,2012年时更降到19%。而这也就意味着:25年来,甘做“傻子”的美国人数量几乎少了一半。(按美国流行语中的世代划分,沉默世代指30-40后,婴儿潮世代指50-60后,X世代指80后,千禧世代则大致指95-00后——译者注)
考虑到这代年轻人的成长环境,缺乏信任可以理解为一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适应性举动。一个愈发只讲究个人成功的市场环境,显然难以培育出高水平的社会相互依赖(social interdependence)。年轻人从事的一切活动都要围绕着积累自身人力资本这个中心打转,许多团队竞技活动甚至也因之而沦为个人秀。再加上当代各种育儿经当中厌恶极端风险的倾向(intensive risk aversion),以及主导着学校与街区的“风险零容忍消除政策”,千禧世代要能够安心出门那反倒才是怪事。
市场及受其影响的各种制度——从家庭、学校一直到警察,对竞争性的大力倡导,本身就在鼓励一种精打细算的不信任倾向。家长和老师们如果把孩子教得太愿意信任别人,那等于纵容他们沦为人生输家,毕竟这个社会里,背叛信任的人太多了;维克多·利奥斯(Victor Rios)的《被惩罚者》(Punishied)描述了这样的情形:非裔和拉丁裔男孩很快就学会了对权威表示不信任,并对之加以提防。普遍信任是少数有钱人的把戏,对他们来说这样做的风险不高,哪怕身处你死我活的激烈竞争中,他们也能保持安定感。对其他人而言,妄想与焦虑状态并非不可理喻,也没多少人表示抱怨,毕竟它们已经是当代美国生活的常态。那也是一种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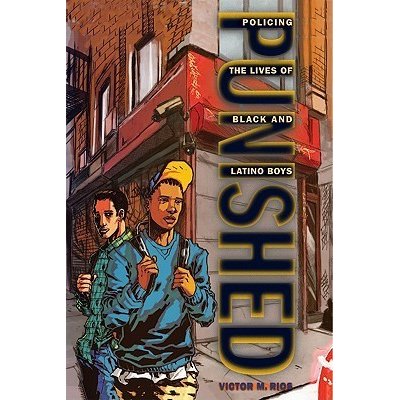
感到他人可信者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从40%跌到20%,其影响可想而知。这当中固然有量的变化——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令信任率减半——但质的区别恐怕更加紧要:生活在一个有四成人信任他人的国家,和一个只有两成人信任他人的国家,体验显然不会一样。在后者,人们彼此互动的方式以及看待邻人的眼光,都是高度不确定的,它会随着一个社会的物质条件而变化。我们并非呆若木鸡,而是具有很强的适应性——但去设法适应一个混乱的世界,只会让自己也变得一团糟,无论你自己是否还能保持工作状态。这种让80%以上的美国年轻人都感到他人不可信任的环境,几乎肯定会诱发更多的精神疾病,若缺乏制度性屏障来给市场“踩一脚刹车”,它只会让越来越多的人疯掉。

论起研究美国人的精神健康状况,圣迭戈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简·特文格(Jean M. Twenge)是其中首屈一指的权威,她在这方面的论著已经汗牛充栋。特文格最有意义的洞见,来自于她基于数十年中的性格调查而进行的历史元分析(historical meta-analysis,元分析是一种定量分析手段。它运用一些测量和统计分析技术,总结和评价已有的研究,例如特文格的论文便对收集来的各种人格量表再次进行统计分析——译者注)。其方法基于“一个人所处世代对其精神状况有重要影响”这一假设,且这方面的影响并不亚于另两项公认的影响因素:基因与家庭环境。在2000年的论文《焦虑时代来临?焦虑与神经质的同期群变化,1952-1993》(The Age of Anxiety? Birth Cohort Change in Anxiety and Neuroticism, 1952–1993,所谓的同期群研究,是指针对特定时期内出生的一组人群,考察其某项生理或心理指标的历时性变化——译者注)当中,特文格指出:
“每一代人都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这些社会世界在其态度、外部威胁、家庭结构、性习俗以及其它诸多方面各有不同。许多学者认为,同期群——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环境的代理变量——对人的性格有实质性影响。”
在这篇论文中,特文格收集了大量1952-1993年间的调查报告,这些自我报告反映着大学生与中小学生的焦虑状况。报告显示,上述两类学生的焦虑度在研究中均随时间变迁而线性增长。增长是实质性的——有一整个标准差那么多。“该同期群的焦虑程度变化相当大,1980年正常小孩的焦虑度,居然比1950年患有精神疾病的小孩高。”特文格如是说。她以及其他的研究者都发现,短时性的历史事件(如战争和萧条)对长期中的精神健康其实无甚影响。大萧条是个经济现象,而非心理现象。另一方面,从长期趋势看,实质性的变化仍然十分显著:作为同期群的代理变量,社会文化环境的确加剧了焦虑。
成长在这种普遍的不信任气氛中,美国的孩子和年轻人们几乎天天都要经受精神上的不安。就目前美国这个社会文化环境而言,年轻人不焦虑才算反常。他们的生活完全围着生产、竞争、监控及追逐个人成就打转,这在几十年前还远非常态。这种人人力争上游、不甘落后的状态——几乎必定会有某些心理上的后果。
作为生产力提高与劳动力成本降低所引发的副现象,“焦虑综合症”绝不是不小心为之或单纯的不幸,事实上社会用它来达到某些效果。心理学家罗伯特·耶克(Robert Yerkes)和约翰·道森(John Dodson)提出了“耶克斯-道森法则”,以刻画唤醒状态(arousal)与工作绩效之间的关系。随着唤醒程度的提高,被试者的工作绩效亦随之提升,但一旦过了某个临界点以后,继续保持唤醒反倒会影响绩效,降低分数表现。我们这个过度竞争(hyper-competitive)的社会固然提高了小孩子的各方面表现,但同时也提升了他们日常的焦虑度。想要小孩发挥出“产能”,注意力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多多益善。这种大环境在其每一个层次上,都倾向于选择那些可以保持一个最佳的唤醒-绩效比,同时又不走极端的小孩。这种操作风险极大,它将整整一代人的心理健康都押作赌注,透过特文格的研究,我们不难体会该模式所引致的沉重代价。
心理变化之巨远不止于焦虑度。“明尼苏达多维人格测试表”(简称MMPI)是一项著名的人格测试,其优点之一是沿用时间非常长,研究者可藉此比较不同的同期群。特文格及其研究团队分析了1938-2007年间的大、中学生测试结果。明眼人一望即知:“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文化变迁令年轻人精神状况日益恶化,且滋生出诸多负面心理倾向,”例如忧虑、沮丧与不满等等。整个社会都在鼓励病理性的行为,且视之为理所当然。
躁动不安、不满、反复无常(这些症状在千禧世代身上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严重)等有助于强化灵活性及自我调节能力的消极方式,正日益受到雇主的青睐。过度活跃(overactivity)的始作俑者正是市场自身;凯文·茹斯(Kevin Roose)的《年轻就是资本》(Young Money)一书考察了金融从业者的众生百态,发现毫无躁狂行为的人无法在业界保持顶尖状态。最优秀的情感劳动者可以敏锐地察知他人的感受与动机,这在老一辈人眼里可能反而是偏执狂的症状。特文格没少批判美国年轻人的自恋倾向,但过度竞争的社会文化环境,肯定会让孩子变得无可救药地自我中心。种种负面心理倾向,无非都是适应大环境的结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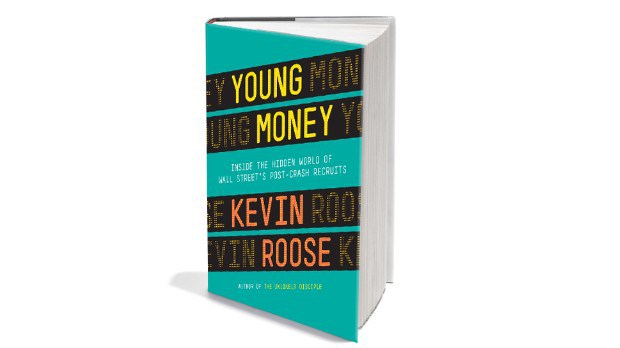
当我们的社会想要从“追求卓越成就”转向“安于平凡”时,它明显陷入了矛盾:要求一个资质平庸的人做到卓尔不凡当然不可能,但作为个体而言,小孩子并不能以此为借口而甘于平庸——更不允许(绝不!)落到平均水平之下。美国人的生活前景差距越来越大,希望与现实之间的鸿沟愈发难以填补,这进一步激发了(并且被认为理应激发)焦虑。适度焦虑当然有助于生产力,但总归也有其限度。较高的职员流动性,意味着大部分企业缺乏在人力资本积累上作长远打算的动机。雇佣那些创造力处于巅峰的职员,一有下降就炒掉——这比起设法为雇员保持一个心理上可持续的唤醒程度而言成本要低不少。毫不意外的是,当前这种生产关系几乎必然会以一代人的精神健康为代价,而这些成本大多又被转嫁给了年轻职员。
焦虑度与绩效的关系是显著的,但另一些心理疾病也与这种高度集约化的生产方式有关。例如,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简称ADHD)与认知节奏迟缓(简称SCT)日渐被诊断为一种不利于提高小孩竞争力的身心状态。对此心理学曾有过争论,有论者怀疑这两个诊断是否彼此独立,不过它们确实能够指代两种小孩无法安心上课的基本表现:一个认知节奏迟缓的小孩会一直盯着窗外看,而患有注意力缺失过动症的孩子则会在自己的座位上扭个不停。该描述有一定简化成分,但对此处的论证目的而言已经足够。它们都是“注意力紊乱”的表现——作为一种脑力劳动的注意力维持,在美国的(自动化)生产方式中正变得愈发重要。
未能在指定时间内保持必要注意力的学生将会被诊断为注意力紊乱,并接受药物治疗,在考试时还会有一些优待措施,以提升其成绩。毫无疑问,有些学生可能会对医生谎报自己患有注意力缺失过动症,以便为SAT考试赢得更宽松的时间——但现实是,某些孩子就是比别人更能坐得住,注意力也更集中,接着,我们的文化便把做不到的孩子通通认作有病,因为病总归是可以治好的。家长和老师——传统上跟小孩子接触最频繁的成年人——都有充分理由去为注意力不佳的孩子寻求治疗,使其能保持高度专注。孩子们的生活前景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此。
随着对专注度的要求日益高企(课堂任务、家庭作业、研究、实践),“掉队”的孩子也越来越多。被诊断为患有注意力缺失过动症并接受治疗的美国儿童数目节节攀升:1987年还不足1%,1997年有3.4%,2007年达到4.8%,2011年则上升到6.1%。尽管这两项研究所涉及的年龄段稍有不同,但总体趋势对用心观察之人而言仍然显而易见。1987-1997年间,由于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占比越来越高,诊断中的社会经济鸿沟缩小了;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越穷的孩子就越有可能被贴上“注意力紊乱”的标签。1991年,美国教育部发表了一项备忘,以确定注意力紊乱的孩子在教育方面应受何种特殊服务,自认为符合诊断标准的学生们因此而纷纷去寻求医疗专家的背书。
最流行的注意力缺陷多动症治疗药,是诸如Adderall和Vyvanse这样的兴奋剂,它们能够以化学方式提高使用者的注意力和工作效能。数以百万计的小孩子和青年人都在使用它,一个二级市场悄然而生,想要提高工作绩效的人们彼此交易药物,这样就不用浪费时间找医生要处方。一项研究表明,约有25%的大学生曾有过非医疗用途的药物使用记录,而滥用最为集中的群体,是那些在竞争激烈的研究型大学里成绩较为落后的学生。从合法处方流出的药物总归难以避免私底下的非法使用。无论官方就药物大量外流这一现象给出何种解释,许多年轻人——不管有病没病——的确会经常使用安非他命来维持工作状态,为自己积累人力资本。这种药俗称“速度”,可谓名不虚传。
在学校的零容忍政策,严格执法与父母照料密集化的推动之下,以药物来治疗注意力缺乏的做法日趋流行,成为一种新式少年管控措施:确保小孩子安静、专注并且有生产力,以便让大人有更多时间来料理他们自己的工作。当然,个人改变不了大趋势。重复一遍,我们面对的两难是: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这是个社会问题(有太多小孩诉诸药物治疗来提高成绩),但落实到具体决策上,大家的考虑就变得很现实了(我家孩子确实注意力不集中,明年就要大考了!)。当前的体制对小孩子要求过高——这一点无须多言——如果靠吃药能提高成绩,每天能少受一点苦恼,甚至还能因之而拥有更美好的人生前景,那家长和老师们何乐而不为呢?情况也的确如此,坚持不给孩子吃药的家长和老师,几乎是凤毛麟角。在目前被诊断患有注意力缺陷多动症的美国孩子当中,有三分之二都接受过药物治疗。
病号有增无减,治疗措施花样繁多,不同人群各有自己的一套因应之道:对个体家长来说,独力协助孩子对付一个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文化环境是不大可能的。对老师来说,学生成绩就更是压力了(请回想一下教育改革对老师们的严峻考验),让那些不太行的学生去接受治疗,会为自己赚到不少闲暇。老板们希望员工拥有丰富的人力资本,时刻保持专注,并尽可能打消睡意。至于用什么手段来达到,老板是不大关心的。小孩子如果想要提高自己对周围世界的认知能力,也可能会主动要求服药——事实上他们别无选择。(个别学生更是心思活络起来,开始倒卖药片给想提高成绩的同学。)担忧青年滥用药物的呼声向来不弱,但无人知道不嗑药的美国还能否维持必要的生产力水准,而我们似乎也找不到有效的替代方案。经济运行基于注意力,而无休止的增长意味着我们将始终处于赤字的危险当中。在这种环境之下,有助于提高专注度的药物自然不会缺买家。
考虑到千禧世代承受的心理压力比前人要大得多,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更加严重的抑郁状况。依竞争性体制的设计,每个人其实都是潜在的输家;这种体制就像精炼厂排烟一样,不断制造低自尊。很难想象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这些变化不会让更多人染上抑郁症。特文格参与的另一项研究清楚地表明:上世纪以来,美国的抑郁症患者数量翻了10倍,而新增部分当中又有一半来自80年代末至今这个时间段。认真计算一番成本,我们将不难发现,抑郁人数翻十倍的代价对美国人而言极为可怕:据《纽约时报》记者凯瑟琳·兰佩尔(Catherine Rampell)的估计,抑郁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每年5亿美元。
这又是一个把生产成本转嫁给职工的案例,抑郁症致使各种隐形社会成本节节攀升,个体的精神焦虑与无力感则是其典型表现。不过,正如特文格提醒我们的那样,同期群是社会环境的一个代理变量,而抑郁人数的历时性增长也告诫我们:该问题绝不只是个体身上偶然的心理波动。这些情感成本都是实实在在的,千禧世代背负的压力比以往任何一代人都要大。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