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瓦格纳的歌剧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阿兰·巴迪欧的这番表白,将德国音乐家的音符,与法国哲学家自己的人生联系在一起,他依然清晰记得年少时“在唱片的电流中,听着来自西格弗里德的森林细语,或者魁梧女人的骑马远行,抑或伊索尔德死亡的交响乐……”
哲学和音乐,常常有一种奇妙的双生关系。我们知道,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同时也是一位音乐家。在当代哲学领域,齐泽克和巴迪欧,不约而同的,都是瓦格纳的爱好者。他们诚心诚意地参加研讨会,将瓦格纳从“原法西斯主义者”的泥沼中打捞出来,并赋予其更深厚的内涵与意义。
《瓦格纳五讲》是巴迪欧参加一场关于哲学与音乐关系研讨会的讲稿,并最终汇聚成一部思想文化著作。全书以瓦格纳的音乐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探讨了作为特例的阿多诺与普遍意义上的当代哲学,以及普遍意义上的音乐与作为特例的瓦格纳的关系,是一部关于音乐与哲学的心灵之作。
经出版社授权,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选出书中前言部分与读者分享。在这一部分,作者以歌剧《唐豪塞》为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瓦格纳如何通过音乐呈现苦难主题。
瓦格纳的音乐与苦难(节选)
文 | 【法】阿兰·巴迪欧 译 | 艾士薇

所有这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途径,使我们得以讨论第二个问题,即认为瓦格纳通过怜悯的修辞学将苦难变成一种工具,而且从未将其恢复为现时经验的论题。
我的主张完全相反。事实上,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苦难在场——当然不总是这样,但却很常见——而且可能以一种比较特殊的方式在场。事实上,在歌剧史中,我只看见一个瓦格纳的真正继承者,那就是伯格。在伯格的作品中,的确存在某些特别具有瓦格纳风格的东西,这在问题的技术层面可能不是很明显,但在戏剧与音乐的联系概念上却非常明显。
瓦格纳是如何创造出在场的苦难的呢?为此,他在音乐中引入了主体的分裂。在他之前,歌剧中的主体身份通常要么从属于典型的传统人物形象,要么从属于这些形象的不同组合:这些人物形象通过各种主体类型的不同结合而获得一种身份。即使在莫扎特的作品中,相对于瓦格纳的作品,其人物形象的标准化也显得更为坚定不移,不过这种标准化会根据情节与人物形象相互结合的方式而发生变化。此外,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整体演奏(les ensembles)才显得如此重要。在莫扎特那里,每一幕剧的结尾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正是在那里才揭示出了源自人物类型合并的主体身份。
主体身份在瓦格纳的作品中则不相同,因为在那里,主体并不是从各种类型身份的结合中,或者,如有必要,从情节中提炼身份,而主要是通过其自身的分裂、其自身内在的分化来获取其身份。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对主体身份概念的重构,主体身份不再是各种结合的计算,正如我之前所说的瓦格纳之前的歌剧的情况。我认为,对瓦格纳而言,苦难的主体不过是一个非辩证化的且不能治愈的分裂。主体的分裂产生了一种真正的内在异质性,而且这种异质性是不可能被战胜的。
在瓦格纳的歌剧中,存在着和解的片段,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分裂不以在场的形式进行表达。它没有在它得以显现的情节片段中,以在场的方式进行表达,但却作为绝对苦难的现时,以在场的方式进行了表达。事实上,瓦格纳那些苦难的伟大人物形象其实就是其自身苦难在场的全新且具有创造性的证明,即使故事后来有了新的转折。无论是唐豪塞、特里斯坦、西格弗里德、安福塔斯还是昆德丽,所有这些人物形象都是极度分裂的牺牲品,这一分裂既不可能被辩证化也不可能被治愈,只能通过我所说的一种分裂的音乐加以表现,而瓦格纳正是这种音乐的真正发明者。这种分裂被运用在了甚至是对音乐的创作中,因为通过对主题潜在异质性的使用,瓦格纳激起且传达了一种尤为严重的分裂感,这是一种真正的主体分裂,它具有一种无法平息的苦难形式。
唐豪塞:无法在同一个地方逗留
我将在这里选取《唐豪塞》这一经典范例。这一歌剧由三种不同的分裂贯穿甚至组织,这三种分裂相互交叉,同时甚至可以算作同一种分裂。
首先,唐豪塞,这是一个因爱情而被深深分裂的人物形象。唐豪塞被两种不同的爱情概念撕扯着,尽管这两种概念,不论在社会阶层关系上还是在表象上,都是无法兼容的,但他无法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我们可以轻易地发现,它们的基础都是严格意义上约定俗成的:一方面,是由与维纳斯山(Vénusberg)和维纳斯之间关系所象征的肉体之爱、异教之爱;另一方面,则是谦恭的爱,几乎可以说是宗教之爱,那是中世纪骑士世界中的爱情。因此,我们被悬在了古代与中世纪之间,悬在了爱的异教概念和基督教概念之间。不论唐豪塞做出何种选择,他都被撕扯着,因为他曾深刻体验过这两种爱的形式。
此外,唐豪塞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伟大的音乐家,这不仅让他征服了伊丽莎白,这位倾心于圣母玛利亚,并代表着基督教贞洁的人物,还让他征服了维纳斯,这一异教徒性欲的代表。
私下说来,这几乎就像是瓦格纳在说:“作为伟大的音乐家,我具有享有所有女性的权利,享有所有爱情形式的权利!”如果像瓦格纳那样,我们赞美唐豪塞,将他视作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那么,我们会碰到这样一个有趣的主题:就算成为一位伟大音乐家又能做什么!相反,如果我们从人物形象被建构的方式出发对他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这里呈现出了一种完全无法忍受的分裂。因此,这就是主体的第一层重要分裂。随即便是历史的分裂,即骑士阶层严格有序的世界与个人飘泊的无序世界之间的分裂:那么实际上,欲望如何能够与骑士阶层的秩序相调和呢?
第三,在诸神之间,存在着根本的象征性分裂。对于瓦格纳而言,这涉及到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因为他在以维纳斯和维纳斯山为代表的异教诸神和基督教神之间被撕扯着。最后,与之相关的是女性特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维纳斯与玛利亚之间被分裂,她们分别是两种爱情的象征,同时也代表了两种不同的象征背景与文化语境。无论如何,这种分裂在唐豪塞这一人物形象中表现了出来,事实上,这一人物就是这个分裂,因而他绝对无法只在一个地方停留。

无法在同一个地方逗留的主题业已在《幽灵船》中得以展现,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指环》中的众神之首沃坦(Wotan),最终也是以“流浪者”的形象出现的。他同样也无法停留在某一个地方。最后,我们看见沃坦头戴硕大的帽子,穿梭在人间,作为一切事物的旁观者,同时也作为其自身衰落复杂展现的目击者。这就是瓦格纳式的典型人物。瓦格纳是一个塑造人物形象的伟大诗人,这一形象无法驻足于某地,注定流浪。此外,毫无疑义,他自身也是一个不断流浪着的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由于瓦格纳曾参与革命活动,他被德国众多州驱逐数年。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歌剧的第二次死亡》一书中涉及过该主题。我觉得他对瓦格纳所采用的拉康式的阐释性思考类型非常有意思。关于瓦格纳的反犹太主义,齐泽克提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谁是犹太人?究竟谁是流浪的犹太人?”因此,他并不满足于“谁是犹太人”这一问题,这个问题一般是由瓦格纳那些关于犹太人在社会中所扮演角色的愚蠢甚至是致命的申明所引起的。流浪的犹太人实际上是瓦格纳非常自我认同的人物形象:他是唐豪塞,或者荷兰人,又或者沃坦。瓦格纳,这位神圣罗马帝国和纽伦堡珍贵城邦曾经的歌颂者,这位曾经只想着可以安居某处并且在拜伊罗特建立自己圣殿的人物,事实上一直为其隐藏的身份所折磨,这一隐藏的身份表现为一种流浪的冲动,以及无法在同一个地方逗留的事实。瓦格纳投射到一系列苦难的人物形象中的,正是这一身份,这些人物身上的分裂禁止他们停留在某一个地方。
这一流浪的冲动在《唐豪塞》中引发了某些极为震撼和令人心碎的场景。比如,在男主角定居维纳斯山,整日投身于肉体与性的欢愉中期间,出现了这样的一幕:他哀求维纳斯允许他告辞,因为他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只有神才能永远地活在欢愉之中。总之,第一幕的这一场景是极其宏伟、炽烈,但同时也是极其痛苦的。在第二幕,维纳斯终于允许他离去,她并不是没有警告他,但所有的一切依旧迅速变糟。他被一群骑士邀请参加一场诗歌比赛,主题是必须赞颂关于圣母玛利亚和贞洁等方面的理想爱情。就在这个时候,他立刻发问:这种荒唐的故事究竟有什么意义。他宣称,这些骑士们对爱情根本毫无概念,只有他才知道什么是爱情,他炫耀着,然后肆意地唱着颂扬肉欲之爱的歌曲。所有的人都想杀死他,他之所以被拯救,仅仅是因为伊丽莎白深深地爱着他。拯救他,更确切地说是因为,他与谦逊骑士们的完美不同,拥有某些阴柔的东西,他可以将这些表述出来。因此,他离去再次流浪。
这里我们所接触到的,本质上是对“无法在某一个地方逗留”的戏剧化:“位于两个世界之间”构成了作为分裂的主体性,并且永远以苦难或者分裂的形式自我表达。但是,唐豪塞和其他所有由于心灵上被撕扯而精疲力竭的人一样,尝试着寻找一种可以超越这种分裂的方法,并调和两者。有人建议他去寻找教皇——今天,我们看到人们将教皇视为人世间的某种超级巨星,这看来再正常不过了——因此,他走上了罗马朝圣的道路,寻求罗马教皇的赦免。
整个关于教皇的故事确实有些奇怪。瓦格纳与天主教没有任何关系,这让人不禁发问,他为何又觉得有必要将罗马教皇引入戏剧呢?然而,围绕教皇的尝试最终依旧无用:教皇——这个明显教条主义的教皇——宣判唐豪塞永远堕入地狱,没有任何赎罪的希望。他让唐豪塞堕入了最为彻底的绝望之中,因为,推荐给他的唯一方案,这唯一能够治愈一直困扰他内在分裂的方法,并没有起作用。因此,他颓废地从罗马朝圣回来,教皇的判决将其抛回本质上的分裂状态,他自然而然地尝试着回到歌剧开篇他曾乞求维纳斯让他离开的维纳斯山。
歌剧进行到这里,我们面临的是苦难的绝对在场,没有任何宽恕的可能。以《罗马记事》之名为人熟知的片段,记载了唐豪塞罗马旅程的游记。在讲述过程中,他将一切都告诉了霍夫曼,这位骑士友人。这位友人曾经秘密且贞洁地爱恋着伊丽莎白。诚然,霍夫曼眼见唐豪塞占了上风,可是他依旧对唐豪塞很友好,并愿意倾听他那苦难的故事。这一讲述是对不可克服的主体分裂所导致的彻底毁坏的表达,且该表达是公开的、现时的。这可能是一个品味的问题,但个人认为,在戏剧中,不可能再找到另一个被强迫受尽苦楚、无处容身如此这般具有破坏力的例子了。
我一直记得70年代《唐豪塞》的一次演出,当时的舞台展现了一个被毁掉的德国。“我们的德国”被瓦解了,同时瓦解的还有沃夫兰(Wolfram),这个与布莱希特有些相似的人物。在这个人物身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个东德的代表,其出现的目的是见证唐豪塞的苦难。我只是想指出——正如我之前将其与萨赫斯的对白联系起来——在分裂主体的音乐建构中,存在某些特别的瓦格纳式元素。至于对文本的处理,整个故事虽然一开始是纯粹的叙述,但后面叙述逐渐淡化,好像整个故事在音乐的压制下逐步地被主观化了。
在瓦格纳的作品中,苦难实际上就是一个此在
分裂的主体通过某种交错被展示出来,如果仔细考虑,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瓦格纳式的方法。这是四种措辞的交错,也是四种技术的交错。
——首先,是一种跨越普通语言界限的宣叙调,它并非真正依靠某种特别的曲调模式,而且总会时不时出现。
——接着,我们还发现一些使人心碎的抒情片段,如同渐强段落中声音的推进,这些片段围绕着某些词汇展开音乐,而不是围绕某些段落。因此,与其说我们要研究的是文本的力度,倒不如说是一些处于叫喊界限的孤立词汇的力度。
——接着,至于管弦乐,我只想描述一下管弦乐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从技术分析层面进行的——而不将主题纳入考虑范围。有些现象如同隐藏的秘密,要同时通过铜管乐器或者低音弦乐器,以及上行分解和弦得以保障——如果人们愿意,也可以说是一种建立在低沉、深厚的音乐上的海洋维度空间。随即,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双簧管尖锐的震音。这两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是极为典型的,它们交错在一起的方式,实际上就是主体分裂、撕裂或者苦难存在的标志。
——最后则是中间的冗长乐章,就其本质来说,它比旋律更具主题性,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它们不过像低音管弦乐中隐秘海洋中的波涛一样,被倾覆与破坏。
所有这些分析都非常独特,并且在我看来,再一次验证了这一事实:确实是音乐建构了主体的分裂。当然,戏剧情景已经确定了,但是,使场景真实呈现,使唐豪塞的苦难在台上完全恢复到现时,而不是在其未来被消解的,正是这些特别的运作方式,而不是唐豪塞所讲述的整个故事。

当人们听到这个版本的《唐豪塞》,会有一种厚重的奇特感——一种主体的厚重感显示出来——同时,也会感受到破裂和非整体的奇特感,就像一栋有裂口的大厦。这只是一种类比,但我认为,瓦格纳所使用的技巧,都用在了创造这种非整体的厚重感,或者这种有裂口的声音大厦的感觉。很明显,这种感觉只有在被摧毁的情况下,才能被修复。当然,大厦就伫立在那里,但它的裂口如此明显,我们知道它不可能继续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版本的背景与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全然相符,隐喻得恰如其分。这一背景展示出了一幢位于废墟之上的大厦,也就是说,唐豪塞自身就是一栋位于废墟之上的大厦,随时都可能坍塌,都可能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毁灭。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唐豪塞的崩溃与死亡。
我认为,在瓦格纳的作品中——尤其是这部作品——苦难实际上就是一个此在。苦难被整合到了叙事里面,叙事同时也在探讨着非辩证分裂的破坏性结果。以下是我对瓦格纳式苦难的抽象界定:它是对非辩证分裂破坏性结果在文本和音乐上的建构。总体而言,在我看来,说我们只是单纯、简单地研究用于调和的诡谲手段,这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我认为,这并不是其中产生的印象。相反,大厦的印象是不可否认的;在我看来,这是用大厦的形式展现苦难效果的一个非常罕见的例子。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大厦属性,我们被导向去支持这样一个观点:这里涉及到的不是苦难,而是毁灭与赎罪。但是,真正涉及到的,是一个体现苦难自身的大厦。对主体而言,苦难在某种意义上是具有大厦属性的:它本身就是做好坍塌准备的有裂口的大厦。我们可以想象关于苦难其他可能的表现方式,但是在瓦格纳处,它的存在,的确等同于人物形象反辩证分裂的破坏性结果。
(本文选自《瓦格纳五讲》前言,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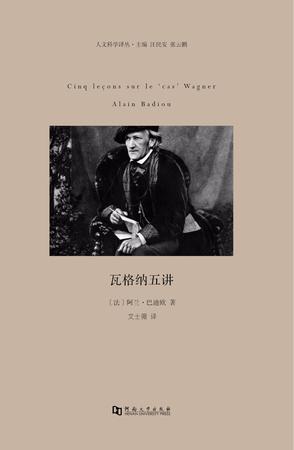
【法】阿兰·巴迪欧 著 艾士薇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7年11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