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正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的何柔宛(Karen Ho)决定休学一年,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工作,同时深入这一美国金融腹地进行田野调查。对于习惯于“向下研究”(“study down”,即研究弱势者的文化)的人类学家来说,能够研究美国最有权势的一群人——投行家(investment bankers)以及他们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一个难得的突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通过一年的参与式观察,和100多份对华尔街投行家的访谈,何柔宛在《清算》一书中描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华尔街——既不同于局外人的想象,也不同于局内人的自我认知。在她看来,华尔街所崇尚的那种聪明和努力工作的文化,建构起了一个极端精英主义的圈子,将投行家们和从事“普通工作”的“碌碌庸众”区隔来开。而这种认为自己是“最聪明、最努力、最有价值”的劳动者的自我认知,加之华尔街特有的工作不稳定性和高薪酬,催生了一种在交易决策中将短期“受益”视作首要、甚至唯一追求的特殊利己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恰是金融危机周期性爆发的必然因素之一。同时,这种表面上“唯利是图、唯才是举”的“金钱精英制度”(Money Meritocracy)也巧妙地掩盖了招聘过程中的名校特权,以及工作场域内的种族、性别歧视。
聪明的文化:投资银行的招聘鄙视链
在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何柔宛发现,他的受访者经常标榜自己“聪明”。他们声称,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来华尔街工作,华尔街创造了迄今为止全世界最精英的工作环境。这种话语对于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来说仿佛具有魔法,对于他们来说,华尔街最吸引人之处,就在于一种置身于全世界“最聪明和最野心勃勃的人群”之中的体验。
当何柔宛试着去破解“聪明”的含义,她发现,在华尔街,“聪明”(smart)并不只意味着智慧或者智力出众(intelligent)。在英文语境下,smart的意涵本来也比intelligent丰富得多。“聪明”是一种混合的感觉,它包括精英感、专业性、长相不俗、穿着得体、充满进取心和活力等等。总的来说,它是一种自然而然又令人印象深刻的感觉,这种感觉参考了那些典型的上层阶级、白人男性投行家的完美形象。
那什么样的人才够得上“聪明”呢?首先,他得从顶尖的名校毕业。对于华尔街而言,顶尖的名校只有两所:哈佛和普林斯顿。何柔宛就来自普利斯顿。根据她的观察,不仅大多数投行家只来自少数几所精英学校,而且,她的校友们也普遍认为,从普林斯顿毕业后唯一合适的职业选择,或者说,唯一配得上普林斯顿毕业生身份的工作,首先是投资银行,其次是咨询管理。而如果有学生在毕业后没有选择华尔街,那么他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不聪明”的,因为“聪明”的定义还包括了一种对精英地位的渴望以及为其付出的最大努力。

精英大学批量生产投行家的原因有很多:独特的校园文化,校友和同辈网络的影响,聪明、成功以及华尔街之间的文化关联,以及职业选择的等级化和鄙视链等等。但也许对华尔街的招聘霸权地位最显而易见的解释是,它几乎主导了整个校园生活。华尔街的招聘者每周都会造访学校,他们频繁地出现在校园论坛、研讨会和社交活动上,免费发放饮料和精致的食物,关于他们的新闻占据了每天的校报版面,印着这些公司logo的冰箱贴、马克杯、飞盘、水壶、棒球帽和文化衫充满了校园的每个角落,领取了这些免费礼物的数以千计的学生,成了它们行走的广告牌。
招聘季的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活动,通常是以一场奢华的“签约日”活动作为结尾的,它的作用在于敦促那些大四的学生们接受这份工作。“签约日”的特殊待遇包括:豪华酒店两晚的住宿、犹他州的滑雪之旅、SoHo夜总会的VIP包厢等等……投行向应聘者们展示了一整套生活方式,并暗示他们:只要签下合约,他们也可以立刻拥有这种生活。
在何柔宛看来,这种将精英学校、投资银行与“完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方法对整个招聘流程而言非常关键,在某种程度上,招聘再现了华尔街的日常实践,在华尔街的鸡尾酒会上,投行家们也是用同样极为慷慨、无可挑剔的方式来“奉迎客户”的。在这样的示范下,学生们很快就学会了这一整套行为规范,并了解了华尔街的商业成功是怎样以出身、竞争性消费和父权规范为前提的。

华尔街在常青藤学校的“高调”招聘,是上世纪80年代才兴起的。在那之前,大多数美国企业还没有公开招聘的传统,常青藤的毕业生们更多地依靠家庭的财富和社交圈子进入研究生院,或者被有前途的企业录用,重点培养,迅速晋升。1980年代以来,由于华尔街攫取了巨大利润,投资银行开始大规模地从精英学校招聘,这些新的员工骨干,不再是从家庭、朋友和亲密商业伙伴的小圈子里挑选出来的,替代精英家庭的是更加精英的哈佛、普林斯顿家族,校友构成了一种新的亲属关系。在“聪明”和“名校学历”之间建立起的这种貌似必然的联系,则掩盖了招聘过程中的“排他性”操作。
例如,白人男性副总裁往往会选择白人男性分析师进入他的团队,哈佛毕业生也会寻求与其他哈佛校友一起工作等等。在“前三”梯队之内的耶鲁也是一个有趣的例子,虽然与哈佛和普林斯顿齐名,但耶鲁在华尔街的口碑却落后于前两所学校。原因在于,耶鲁被认为是更加自由散漫和“艺术家气质”的,在某种程度上缺乏自由市场导向,甚至被认为是被纽黑文(耶鲁大学所在的城市)——这座充满了大量工薪阶级和有色人种的城市所“污染”了。
同是常青藤大学,在华尔街的地位却相差甚远。哈佛和普林斯顿的毕业生甚至不需要任何金融专业背景就可以进入华尔街工作,在与那些潜在的华尔街雇员交流的过程中,何柔宛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甚至不清楚“金融服务”是什么。而对于其他学校的毕业生来说,金融知识则是应聘的必备条件。在投资银行眼中,前者具有一种毋庸置疑的、普遍意义上的、自然化的聪明,而后者的聪明则必须通过专业技能来证明,通过区分这两种“聪明”,华尔街在精英主义内部也筑起了等级的高墙。
投行为什么需要“最聪明”的雇员?因为它们知道,当投行试图拿下一项业务或者与客户达成交易的时候,让那些常青藤毕业生去主持谈判往往是最有效的,即便他们毫无经验可言。但当企业得知一个哈佛或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将参与项目时,他们通常更愿意做这笔生意——因为,投行会告诉他们:“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在为你服务。”
可以说,投行和精英学校之间建立了一种可以互相强化的联盟。利用精英学校和精英雇员的光环,投行将自己标榜为比其他美国企业更聪明、更先进、更具全球视野的机构:因为我们拥有全世界最聪明的雇员,我们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简介就一定是正确的、值得被信任的,因此我们设想的交易就必须被执行。同时,这种内化了的“聪明”也可以抹去华尔街在金融实践中可能导致股价崩盘、企业破产和金融危机的事实,换言之,聪明可以掩盖华尔街不负责任的短期决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白领血汗工厂:努力工作是华尔街的唯一信仰吗?
“我这个星期已经熬了三个通宵。”
“过去两周我每周工作110个小时。”
“我凌晨三点回到车里睡觉,因为我不得不在早上六点回去继续工作。”
在华尔街,过度工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投行家甚至以此为傲,认为自己和朝九晚五的上班族是两个物种,后者自鸣得意但能力低下;而从制度文化的角度来看,“过度工作”被视作是华尔街金融市场主导地位背后的驱动力和合法性的来源。
何柔宛采访到的投行家们几乎全部认为,美国企业是非常没有效率的,而低效的原因是员工过于懒散。他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带有明显的道德优越感,偶尔也流露出一丝嫉妒。事实上,今天美国企业的效率以及对效率的理解,完全是依据华尔街的意识形态和重组手段(投行的工作之一就是通过重组和裁员帮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建立起来的,这一过程发生在1980年代。投行家们经常将聪明、富有上进心和工作伦理混为一谈,并将他们的行业当做效率的表率,认为自己的工作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其他企业的平庸。换言之,华尔街对其外部世界的判断,帮助他们合法化了“用更少的人做更多的事”的裁员叙事,并建议美国企业根据这一原则改革它们的雇佣方式。
但这种判断显然是带有偏见的。事实上,由于员工过于懒散而效率低下的企业,并不能代表美国的普遍情况。还有大量中低阶层的劳动者同样在过度工作,同时,他们薪资微薄、工作不稳定性很强、安全和权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更不要提血汗工厂和很多非正规的劳务关系。因此,投行家们对于朝九晚五的“科层制”工作的批判,也不过是给自己树立了一个假想敌。
努力工作不仅是投行家们证明和内化自己“市场代言人”地位的工具,更在投行内部,缓和或者说遮蔽了种族和阶级的矛盾。
“金钱精英制度”(money meritocracy)是华尔街正当化自身的职场秩序和员工构成的核心叙事,当然,这种叙事也是极富争议性的。“金钱精英制度”假设绿色(美钞的颜色)是华尔街唯一可见的颜色,认为华尔街对于金钱的强烈欲望超过大多数其他机构,因此,它会存在更少的种族和性别歧视。换言之,华尔街对于金钱的贪婪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会互相抵消——无论来到华尔街的人拥有怎样的背景和身份,只要他能给华尔街挣钱,就会被接纳。

何柔宛认为,华尔街的口头禅“金钱不歧视”(money doesn't discriminate)本质上是一种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假设,它认为种族主义和其他偏见构成了有效市场交易的障碍,因此会被创造利润的迫切需求推翻。因此,华尔街坚称自己“唯贤至上”,种族、阶级、性别都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外部性因素。
然而在田野调查中,何柔宛发现,“金钱不歧视”不过是一个脆弱的神话。事实上,种族和性别歧视在华尔街的日常实践中随处可见。例如,一些亚裔分析师在职业生涯的早期就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被邀请到乡村俱乐部或高尔夫球场,而这些地方,恰恰是白人男性的特权场所。因此,许多亚裔分析师致力于将自己打造成金融产品专家,因为有色人种很难想象自己能够不依赖技术上的核心竞争力获得认可。在华尔街,有色人种需要采取一种策略,即通过绘制不同职业特长的种族地形图,来延缓或避免与种族主义的正面对抗。
而在种族和性别两个维度上都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女性,则经常陷入一种“阶级下滑”的处境,这种处境被何柔宛称作“短袜和长筒袜现象”。许多华尔街的女性雇员在上下班通勤时穿着短袜和运动鞋,到办公室才换上高跟鞋,于是,她们不得不在短袜里再穿一条连裤袜。但两个非裔女性高管则对何柔宛表示,这样的打扮非常“俗气”,而且“不专业”。因为在华尔街,长筒袜和短袜叠穿是一种标识,它暗示了更低一级的职场地位。
大多数“前台”(投资银行的工作分为“前台”、“中台”、“后台”,其中“前台”是给公司赚钱的部门,最风光也收入最高)职业女性住在曼哈顿岛上离华尔街不远的地方,她们开车或打车到华尔街;但“后台”女员工与行政助理大多住得很远,因此她们的通勤时间更长,也更需要一双舒服、方便的运动鞋。
除此之外,行政助理们(通常服务于男性高管)一般会穿鞋跟更高的鞋子,而“前台”女投行家一定要在着装上与行政人员区分开来:她们的套装不能太紧身,鞋跟是安全的中跟,头发不能梳得太高,也不能涂过多的发胶。因为在华尔街,女性通常会被认为是“行政人员”,女投行家不得不时刻警惕这种“阶级下滑”,这种担忧在有色人种女性中更为明显,种族偏见会进一步导致她们的“去职业化”。
女性和少数族裔雇员在华尔街的处境说明,即便在一个“金钱精英主义”的制度下,职位、薪酬和工作性质也常常被种族、性别所区隔——等级和偏见无处不在,努力工作并非是唯一的晋升阶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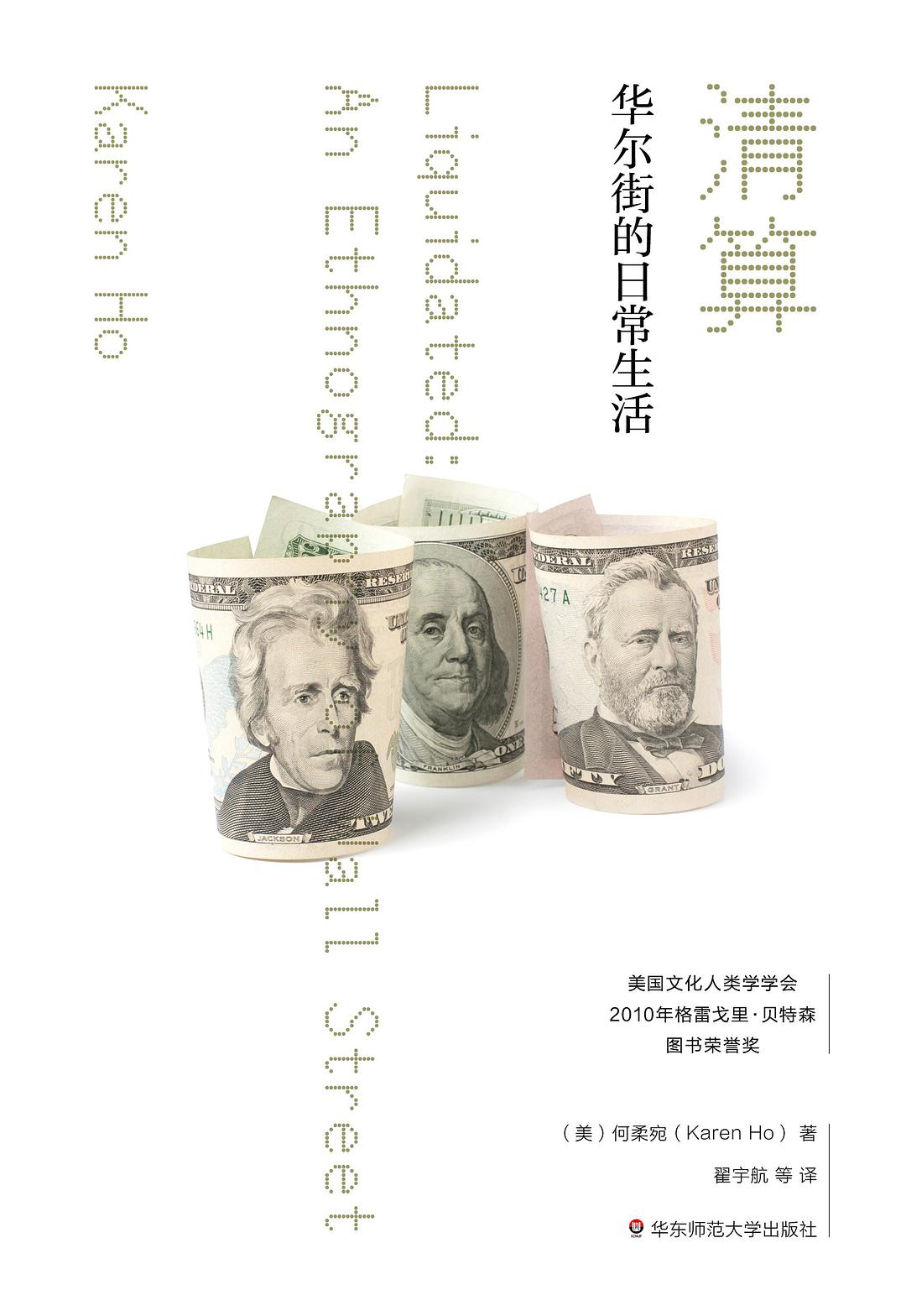
何柔宛 著 翟宇航等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