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宏志戴一副黑框眼镜,留着黑白夹杂的半长的披肩发,表情是一副天然的苦脸,但又不失幽默和风范。“要想完整地介绍他,我们就要在这里过夜了。”在日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活动中,主持人梁文道笑道。他曾经是知名的出版人,还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推手,侯孝贤《悲情城市》和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电影的策划监制,还曾担任“滚石唱片”总经理,为罗大佑策划唱片,此外,他还是互联网商城Pchome创办人。
而在这场以詹宏志新书《旅行与读书》为主题的交流会上,詹宏志只带了一个头衔:读书人。读书人詹宏志讲的是自己热爱的旅行,旅行本应是一种磨砺和学习,在今天服务周到的舒适化的旅行中,旅行的意义何在?而被房价和现实所困的青年人,又如何安放自己的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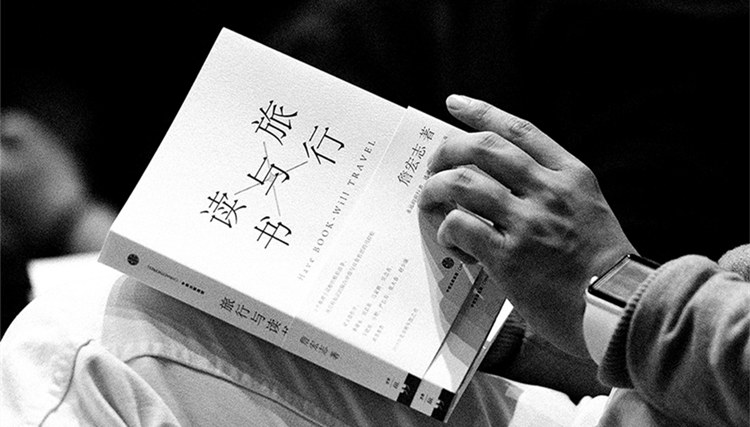
旅行的原始意义是折磨
旅行是把自己从熟悉的环境放置于陌生地,花掉一些钱,没有没有特别的目的,也不许诺以明确的回报,但我们为什么会相信这样的事情对人生是有意义的?詹宏志拿《格列佛游记》的开篇作例,17世纪末的学习者接受教育要分为三个环节:修业、学徒、漫游。旅行是大学教育必需的一环,旅行结束之时也是教育完成时。这个制度不仅限于大学生,职业教育也是如此。学完所有技能的工匠必须离开家,到语言不通的异地人家工作、生活,只有顺利完成这一年的历练并安全回来的人才有资格加入当地工匠组织。
在没有旅行服务业的时代,没有一张印着目的地名字的车票,只能一天一天不断地走,一路摸索、问路、搭车,借住在人家甚至柴房、牛棚里。“如果旅行条件是这个模样,就会知道旅行是多么严重的事”,詹宏志说,“等于要把你全身一切对世界的了解拿来对付可能有的种种实验跟考验,也就是说,旅行的意思是使你离开了你熟悉的支撑系统,必须想办法在陌生困境里活动。”
“travel”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本是一种刑具,所以旅行本来有折磨的意思,“让身体同陌生环境摩擦、纠缠”;詹宏志认为,现代充满保护跟照顾的旅行就失去了原意。飞机火车、旅行社、高档酒店、随行翻译和向导愈加把旅行标准化、同质化,安全舒适性提高的同时,人们也丧失了同目的地身体接触的机会。人们要看到巴黎铁塔并且在下面自拍,才证明自己来到了巴黎。“旅行的身体体验变成了地标目击,如果旅行缺少了跟目的地的摩擦,经验就只好全部符号化,你的经验用时间表定了,用行程记录了,用符号记录了。”


詹宏志称这种新的旅行经验为“太空式的旅行”:“ 太空人穿着太空衣来到月球,他没法五感并用,他的身体无法承受这个经验,所以是穿着一层地球去了,衣服里空气成分、湿度都跟地球相似,他来到了异地,但带了一层家乡来。”团进团出的旅行就像是穿着家乡太空衣,耳朵听到的是自己熟悉的普通话,吃到的是自己熟悉的饮食,所有经验都不需要跟当地的差异性为伍。“当照顾愈多时,旅行的原始意义—— ‘折磨’就愈少了。”
实际上,传统意义上在磨难中自我提升的旅行在今天仍然存在,也依然可行。詹宏志讲起一名只身来到中国某小城镇的荷兰学生的故事,他曾对詹宏志说:“把地图摊开,没人去过的地方就是我要去的地方“。就像今天很多年轻人的“穷游”,“今天欧美很多大学生出国旅行,强调的是用一点点钱想办法撑愈久愈好。撑得愈久的人是在旅行上收获愈多的人。”要能够用能力“贫穷”地旅行,“如果你是个年轻人,要旅行有丰富的回忆,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更艰难的地方,用很少的钱走很远的地方、走很多的时间,这个时候为了寻找答案,才真正激发你对每一个地方的理解和对每一个地方的想象力。”
詹宏志看来,旅行应该是一种人生的扩大,将自己完全暴露在陌生的环境中,“绝对不放弃任何一个跟异乡纠缠的机会”。 人一被抛入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身边的环境,家庭、国家、时代都已经决定了,旅行和读书都是去经历另一种生活。“我的旅行目的是短暂地脱离我自己,脱离我的家乡、我的社会、我所熟悉的体系,希望能够短暂的变成另外一个人,让我有机会窥见或者接近别人的生活,或者真的活在别人的生活里。”
每一个“小确幸”里隐藏着一个“小革命”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理想所在,也是他们的一种情怀。然而生存的焦虑、高昂的房价,年轻人如何在现实中安放自己的理想呢?有年轻观众在现场请求得到建议。
詹宏志认为,这不光是现在大陆和台湾年轻人的困难,而是全世界的困难,全世界通过自由贸易和全球化手段带来的经济繁荣结果,并不是所有人都共同享有的,当中的富裕意味着是极高的房价和地价。“最近两年全世界对自由贸易有严重的质疑,甚至可以把特朗普的当选跟英国脱欧当成这种心理状态的一环,这个经济发展的成果不是平均的所享有,而是这个造就了一部分人有财富的人,却变成了多数人的生活压力。”詹宏志不认为自己能给这个事情一个社会性解决的答案,但是每个人可以出一小块力。

詹宏志觉得今天的年轻人也不是只被房价跟物价逼着跑,“因为房价有一个办法可以鄙视它,即如果你不要房子,这件事就不会到这个地步。房价拦不住是因为你对资产有一种迷信。”现在台湾大企业家批评年轻人没有追求、没有狼性,只有“小确幸”,詹宏志觉得这样想是小看了这些年轻人,他要为“小确幸”做一些辩护。“‘小确幸’的意思是我不要那个主流价值,不要变成大企业家的那种价值,我回到家乡开一个小店,把我的力气全放在照顾自己家乡的老人小孩上,重新把当地地方的文史工作做起来,这不是一个‘小确幸’就可以解释的,而是跟现有主流价值要更多钱、要更快经济发展对抗的想法,每一个‘小确幸’里隐藏着一个‘小革命’。”
如果年轻人下定决心不遵从社会的主流价值,社会就会有多元的机会出来,选择分散了,这个社会给彼此的压力就降低了。如果人们不追求大城市,回到家乡去,不只是做传统的工作,而是把传统的工作赋予意义,詹宏志认为很大一部分被批评为“小确幸”的是这样的事,这是对今天经济情境的一个最大反抗,这件事对台湾意义重大。
所以詹宏志表示,“我建议年轻朋友努力存钱旅行,这样的话就不用买房子了,哪里都有地方住,到处去其他地方,干嘛要有房子?”
台湾80年代新电影的气氛在今天很难复制
说到自己“跨界”的生涯经历,詹宏志有点惭愧,看起来风光的履历,他说只是反映了他的生涯坎坷,而不是反映了他的能力。是因为在出版社不得意,詹宏志才跑到唱片公司,而他去做电影也不是因为“有多大本事”,而是那些现在看上去是电影史上的大师的导演,当初只是他潦倒的朋友。詹宏志回忆起当初奋斗中的台湾电影人。他之所以去做杨德昌、侯孝贤电影的监制,是应为他“是古时候的人”,“ 古时候的人朋友有困难就得干,有人敲门就得做。”
詹宏志回忆道,那个年代是一个天真的时期,台湾80年代新电影的气氛在今天很难复制,因为今天大家懂太多事了,当年什么都不懂所以才会去做。“《悲情城市》我不只是做监制和筹资者,各位在里面也会看到我的演出,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不要钱的,只要我、吴念真、张大春去,就省了很多钱,找临时演员都要几个便当几百块钱,我们去,连这个都省下了。所以我们当时所处的是一个没有计算的时代。”

现在回头看当年拍的那些电影,有时觉得很难想象。“当年做杨德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简直快被钱逼死了,因为一再的超预算。最后花了大钱好不容易才把电影拍完。”但那部4个小时的史诗电影,总共只花了100万美金,而《悲情城市》当时总共花了不到2000万台币,也就是400万人民币。就是这些钱对他们也很困难。
“我做很多事是因为遇到很多情境,这些情境一再的逼迫你,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电影工作,我是喜欢我的朋友,我作为他们的朋友,不能忍受他们坐困愁城,我会觉得难过。我也不是能做多少事的人,但能帮一点忙,所以我就参加一点工作。今天回头看,我是沾光了,超过了我应得的名誉。”
所以詹宏志说,“要创造新的文艺复兴氛围,从我的角度来看也不难,是一群傻瓜在一起毫无心机,不知道未来,也不知道能成就什么事情,只是傻傻的做。”但那样天真的时代离今天已经很远了。
摄影:杨明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