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历史学家罗杰·克劳利的“地中海三部曲”结束在欧洲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葡萄牙人已经绕过好望角,在东非穆斯林水手的带领下来到印度西海岸,开始染指香料贸易,欧洲的经济重心开始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转移。葡萄牙这个偏居欧洲边陲、被排除在地中海贸易和文艺复兴外围的小国,终于将要迎来属于它的时代。
在这本名为《征服者:葡萄牙帝国的崛起》的新书中,克劳利截取了葡萄牙历史中至关重要的三十年,以1483年为起点,葡萄牙在几位非凡的帝国缔造者的带领下,企图摧毁整个伊斯兰世界,控制印度洋和世界贸易。在帝国雄心、圣战狂热、骑士精神以及世俗财富的驱使下,他们一面入侵北非,企图夺回耶路撒冷,一面沿着西非海岸南下,1498年抵达印度洋,1500年登陆巴西,1514年来到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影响力遍布全球的航海帝国,开启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时代和欧洲殖民扩张的500年。
当我们站在500年后的今天,回望全球化的起点,似乎有着特殊的意味。随着欧洲难民危机的加剧、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全球化的潮流将会被逆转吗?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全球化的未来时,克劳利表示,全球化正从一个正面词汇变成一个负面词汇,即便如此,强行设置贸易和移民壁垒依然是非常困难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经济事实,而且关系到每一个人,如此具体而紧密的连接是几百年历史积累的结果,并非一朝一夕可以改变。而当谈到欧洲的难民危机时,克劳利的看法是,难民危机不是宗教战争的延续或者遗产,当前的中东问题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与十字军东征时已经完全不同,在911之后重提十字军东征是愚蠢的。

叙事史是关于个人经验的,我渴望听到人的声音
界面文化:你之前一直在写地中海国家的历史,最初是什么让你对葡萄牙历史感兴趣的?
罗杰·克劳利:我写的上一本书是关于威尼斯人的,这本书结束在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那就是葡萄牙人已经完成了环非洲大陆的航行,到达了印度,并且开始直接采购大宗的香料。威尼斯人一直是通过埃及获取香料的,这时他们忽然意识到,他们的商业模式已经岌岌可危,这条香料的商路很可能会被葡萄牙人夺走。这是欧洲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欧洲的经济重心从地中海沿岸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先是葡萄牙,再是荷兰和英格兰,我对这段历史非常好奇。
我开始写作这本关于葡萄牙的书还有一个非常私人的原因,那就是当我正在考虑这本书的题材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个葡萄牙读者的电子邮件,他也是我的邻居,他说他非常喜欢我的书,并邀请我去他家喝一杯。于是我就去了,他非常有说服力,我们聊到了很多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内容。如果不是这位葡萄牙朋友,我可能不会写这本书。
界面文化:在选择、组织和呈现材料方面,叙事史和史学研究有什么不同?
罗杰·克劳利:叙事史是关于个人经验的,它更接近故事,我渴望听到人的声音,因此会选择日记、书信这样的材料。我喜欢写戏剧性的事件,主要是战争,因为关于战争的史料对人的呈现最为鲜活。我希望能够书写类似1453年这样的特殊时刻或是历史转折点。相对于纯粹的史学写作,叙事史的写作策略更接近文学,当然前提是它必须真实、不能虚构。我会用很长的篇幅更细致地描写故事的一部分,其他部分则一笔带过。如果你仔细阅读 ,可能会发现书中的某一章节涵盖了十年的时间跨度,而另外四章则用来描述一周内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拍电影一样,镜头会随时变焦,时而推近时而拉远。用一句话说,我希望能够写我自己会愿意读的历史。
界面文化:为什么你喜欢选用第一手资料?根据第一手材料重构历史有什么困难?
罗杰·克劳利:我很喜欢第一手材料,喜欢听到人们说“我曾经在那里,我做过什么”。它可以使我与历史中的人物建立很直接、很紧密的联系。困难可能有两方面,一方面,我需要反复查验个人的叙述是否属实,但是很多时候,材料的真实性很难确认。有时候,关于同一件事情,会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在书中同时呈现所有人的说法是不可能的,即便真的这么做了,读起来也会非常乏味,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选择最为接近真实的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在我写作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时候尤为突出,因为在18世纪之前,伊斯兰国家普遍没有印刷文化,因此他们对历史的记载也比较少,即便有也非常乏味。因此对我来说,想要平衡双方的立场,从他们各自的角度去讲述历史就变得很困难,因为穆斯林的记载实在太少了,通常我都需要从基督教一方的记载中试图寻找一些穆斯林的观点。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书写战争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罗杰·克劳利:如果写太多战争,书读起来就会非常乏味,因为那些战斗可能都是差不多的。我会想要从亲历者的角度来写,因为战争最有趣的地方就在于人的行为。很多关于战争的故事,都是从指挥者的角度写的,是关于策略的,我想要写战争的细节,而且是真正在战场上拼杀的人讲述的细节。但是困难在于,当你处于那样紧张激烈、刻不容缓的环境中时,当非常残酷的场景就发生在你眼前的时候,人们是很难清晰地记忆当时的情况和感受的,那种极端的经验经常让我们不知所措。

就战争的动机而言,上帝和金子同样重要
界面文化:你曾经在谈到争夺君士坦丁堡的战争时指出,就战争的动机而言,上帝和金子是一样重要,那么葡萄牙对穆斯林的进攻呢?经济和宗教哪个是更重要的原因?
罗杰·克劳利:两者都有。圣战依然很重要,葡萄牙国王的梦想就是要夺回耶路撒冷,从战略上讲,他们认为只要绕过好望角,就可以从背后打击伊斯兰世界。但是对于葡萄牙人来说,获取财富也非常重要,首先是撒哈拉以南的黄金,最终他们想要控制香料的商路。一些人想去东方传教,另一些人只想得到尽可能多的商品和财富。最重要的是,这两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关联,对于葡萄牙人来说,如果他们能从印度获取巨额财富,就说明上帝认可他们的讨伐是正义的。这种内在逻辑在今天仍然存在,比如在美国,财富就是虔诚的标志,而虔诚也会带来财富。
界面文化:你曾经提到,你从20世纪英国的旅行写作中汲取了很多灵感,不仅在于写作风格,而且在于向历史书写中尝试引入一种“场所意识”(a sense of place)。在你的书中也有很多地理相关的内容,你为什么认为在历史中加入“场所意识”是重要的?
罗杰·克劳利:这可能源于我的个人经历,我对一些地方历史的兴趣,是因为我去过那里,被那里的历史遗迹深深吸引。地理环境,气候,城市的布局都对战争的结果、历史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葡萄牙人的远航和地理大发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洋流风带规律,而伊斯坦布尔的包围战也与城市的空间结构、地形的起伏紧密相关,这些微观的地域知识非常重要,你必须了解这座城市的地理,才能理解这场包围战,为什么防御的一方会处于劣势。
对于威尼斯人来说也是一样,心理和贸易的动机都与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分不开。威尼斯人生活在泥滩上,从生态学的角度看,泥滩是非常不稳定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心理和行为,比如他们通常都非常自律,或者他们会齐心协力一起开凿运河等等。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土地这点也很关键,这就意味着这里不可能孕育出那种传统的中世纪社会——由在地劳动的农民阶级和坐享其成的贵族阶级构成的中世纪社会,在威尼斯,每个人都必须成为一个商人。威尼斯位于亚得里亚海的北端,占据着地中海重要的枢纽,通过海路从东方来的货物会从这里进入欧洲的腹地。事实上,不仅地理知识和场所意识是重要的,我还想补充一点,颜色,有时很也很重要,比如说,你知道在莫尔塔城穿阿尔玛绸缎有多热吗?热极了!这些都对我们重构历史,理解动机和战略有非常大的帮助。
界面文化:在中国,我们经常把郑和下西洋与达伽马和哥伦布的航行做比较,很多学者都试图去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成为一个海洋帝国,开拓商路,建立殖民地,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罗杰·克劳利:在西方我们把这个问题称作“李约瑟难题”。在我看来,在某一时刻,中国开始变得封闭,这可能是因为它对外部世界没有需求,除了长颈鹿这样的奇珍动物。因为中国是一个有丰富农业资源的大国。我很肯定中国掌握环非洲航行的技术,但是他们没有理由这么做,他们在国内已经可以获得想要的一切。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法国,法国有非常长的大西洋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成为一个强大的海洋探索者,因为它有非常富饶的农田。反而是那些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小国,比如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更有向外扩张的野心。

在9·11之后重提十字军东征,是最糟糕的言论
界面文化:书中所描写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启了第一波全球化的高潮,而如今,尤其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我们似乎可以感到反全球化的运动在席卷北美和欧洲,你怎么看全球化的未来?
罗杰·克劳利:我们正生活在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时刻,全球化正在从一个正面的词汇变成一个负面的词汇。但我认为对于全球化的未来无需疑虑。全球的经济联系已经如此紧密,强筑贸易壁垒的难度将会非常大。虽然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各自的利益,并且手段很可能是敌对的,但我仍然看不出,反全球化的防火墙何以可能。况且,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实,它涉及到每一个人。可能正因为此,它才会非常令人不安。欧洲正在为移民问题苦恼,不仅是欧洲内部的移民——脱欧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大批波兰移民的涌入,而且还有欧洲以外的移民,来自中东的难民,以及由于气候变化离开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移民。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设置移民壁垒的尝试,但是将会非常艰难,因为这与二战以来英国长期持守的自由民主传统相悖。
界面文化:你曾经在一篇文章中提到,由于欧洲难民危机,地中海可能再次成为欧洲历史转折的中心。你觉得难民危机是历史上长期宗教战争的负面遗产吗?
罗杰·克劳利:我并不这么认为。难民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叙利亚,导致他们背井离乡的,其实是中东的内部战争,虽然英美的干预也起到了非常糟糕的作用。ISIS也在将难民赶入欧洲,你也可以说普京在将难民赶入欧洲,很多人都坚信普京轰炸叙利亚是为了威胁欧洲的稳定。但无论如何,我不认为目前的中东问题和难民危机是宗教战争的延续。中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必争之地,一直都处于动荡之中,现在只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循环。殖民力量、一战以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瓦解,在中东创造出许多不同的国家、教派、部族,加剧了这种动荡,就好像苏联解体之后,巴尔干半岛上几个国家之间的争端瞬间爆发为仇恨和战争。
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的重要原则,但前提是,中国历史是相对连贯的。而对于我们而言,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似乎很难,我们只能从近期的历史中反思学习。比如欧盟就是我们从一战的历史中吸取的教训,一战之后我们惩罚了德国,于是导致了另一场世界大战,于是在二战后我们知道了不能再次惩罚战败国,欧盟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下诞生的。
对于从十字军东征中学习处理当今中东问题的经验教训这种想法,我抱有很高的警惕。小布什在911后重提十字军东征,我认为这是最糟糕的说法,瞬间带回了那些令人不安的历史记忆。十字军东征的时代人们的想法和今天人们的想法已有天壤之别,我非常喜欢L. P. 哈特利的一句话,“过去是另一个国度,在那里人们的行事方式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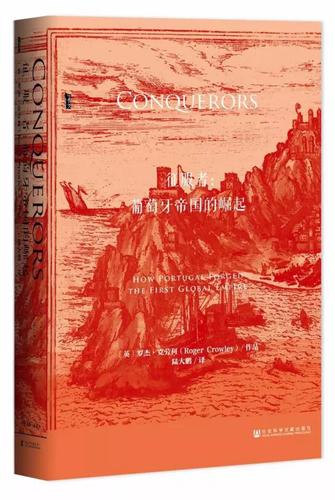
罗杰·克劳利 著 陆大鹏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1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