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的『思想界』我们关注刚刚逝世的社会学巨擘齐格蒙特·鲍曼和处于弹劾危机中的韩国总统朴槿惠。
鲍曼的一生是过去一个世纪的缩影。少年时代受尽贫困和反犹主义的滋扰,在颠沛流离中度过;青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曾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上过战场,立国军功;后来又因犹太身份被迫离开军队,进入学院,仍然信仰社会主义,却与党的路线渐行渐远;中年再次背井离乡,世界形势的急转直下也是他从建构转向批判,《现代性与大屠杀》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晚年的鲍曼笔耕不辍,不断回应着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的新问题,在“流动现代性”的框架下对微观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而朴槿惠的失败似乎预示着统治韩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朴正熙模式”的最终崩解。这位在父亲的政治遗产庇护下当选的女总统,最终却和这一政治遗产一同走向腐朽和衰败。朴正熙时代奠定的实用主义执政路线,以及政商勾结的运作模式,在助力经济腾飞的同时,垄断了加剧了社会分化,阻断了上升阶梯,造成了严重的腐败和制度上的顽疾,而这一切恶果都在朴槿惠的任期内以一种“父债子偿”的方式爆发出来。对于韩国而言,朴槿惠的失败,既是对既有社会秩序的挑战,也是寻求新的发展方向的机遇。
从大屠杀、新穷人到数位时代:纪念社会学家鲍曼
英国当地时间1月9日,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其位于英国利兹的家中去世,享年91岁。

《探索与争鸣》杂志在纪念鲍曼的文章中回顾了他的一生。鲍曼1925年11月19日出生在波兰西部一个贫苦的犹太家庭,二战期间举家从波兰流亡到苏联。1943年,18岁的鲍曼参加了苏联的波兰军队,还曾担任政治指导员,参加过科沃布热格和柏林的战斗。1945年战争结束,鲍曼被授予英勇十字勋章,荣升上校军衔,并获得了在华沙社会科学院学习社会学的机会。

1953年,鲍曼在波兰的反犹清洗中被军队解职。1954年至1968年,他一直在华沙大学哲学与社会科学系任教,最终还是因为反犹主义和“毒害青年罪”而被驱逐出波兰。短暂流亡以色列之后,鲍曼于1971年定居英国,一直在利兹大学任教,直到1990年退休。他终生没有加入英国国籍,去世之前还表示,“我是波兰人,我死的时候也是波兰人”。
鲍曼与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贝克(Ulrich Beck)并称为当代欧洲社会理论的“三驾马车”,他一生勤勉,笔耕不辍,先后出版过57本著作,发表了100余篇学术论文,涉及的主题相当广泛,包括大屠杀、现代性、全球化和消费社会等等。英国社会学会于2011年授予鲍曼终身成就奖,称其对现代性问题的阐释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社会学,赋予这一学科新的理论活力。鲍曼的新书《怀旧乌托邦》(Retrotopia)将于2017年1月27日正式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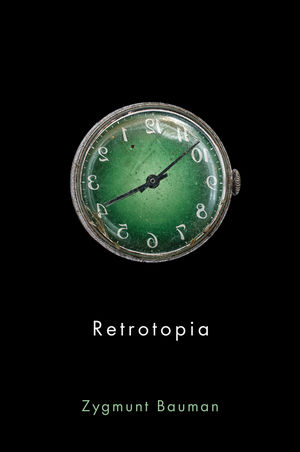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郭台辉在《鲍曼的思想肖像:在失去根基的现代社会,鲍曼提醒我们什么?》一文中梳理了鲍曼学术生涯的五个阶段:1.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波兰对苏东社会主义和英美资本主义的政治与社会问题进行社会学阐释,从葛兰西的思想中发展“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2.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前期,关注引起社会变革的主体力量,把知识分子置于决定性作用,试图重建东欧社会;3. 八十年代中后期到九十年代初,面对欧洲危机,转向对现代性的彻底批判;4. 九十年代初期到中后期,试图从后现代道德和政治来拯救现代社会;5. 九十年代末至今,全面转向流动的现代性,探讨个体生存的流动境况。
鲍曼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是从《现代性与大屠杀》开始的,这本书试图告诉读者几个反常识的道理:首先,相较于南京大屠杀这种反现代的残暴行为,德国纳粹的大屠杀恰恰是现代性的结果,正是因为现代官僚制和现代技术的合谋,大屠杀才可能如此大规模、高效率,完全丧失道德同情;其次,对于大屠杀的反思不仅要谴责加害方的残暴,受害者也要承担责任,如果受害者奋力反抗,那么加害的成本就会更高,甚至不可能,而受害者之所以合作,正是出于自我保全的理性选择;最后,基于以上两点,在道德被政治操纵,而现代个体依然唯理性主义是从,大屠杀的悲剧依旧可能重演。

齐格蒙特·鲍曼 著 杨渝东/史建华 译 彭刚 校
译林出版社 2011年1月
千禧年之后,鲍曼的关注点转向了大众面对的社会问题,他提出“流动的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概念,从不同侧面重写人类的生存境况。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浪潮下,一方面,资本和移民如潮水般涌入了劳动力紧缺、福利制度健全的西方国家,给西方既定的社会秩序和价值观念带来异质性的巨大冲击;另一方面,反全球化的浪潮也正在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它可以表现为非利益性的宗教纷争、种族冲突、文化矛盾,并最终导向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运动。鲍曼后期思想的价值就在于抓住了这些结构性问题给人们带来的流动性后果:所有人都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
文化研究学者刘昕亭则着重梳理了鲍曼晚期思想中重要的“新穷人”概念。在《工作、消费、新穷人》一书中,鲍曼定义的“新穷人”(the new poor)指的是“有缺陷的消费者”(the flawed consumer)。鲍曼提醒我们,“贫穷”不仅是物质匮乏和身体痛苦,它同时是一种心理折磨与社会压迫。消费社会里的穷人,必须生活在为富有的消费者们所设计的社会空间内,但是消费社会所倡导的生活模式,连同消费至死的不渝精神,对低收入群体来说,根本遥不可及。因此他们被排除在一切“正常的生活”之外,不能胜任挑选的社会职责,并因此承受着羞耻感和不合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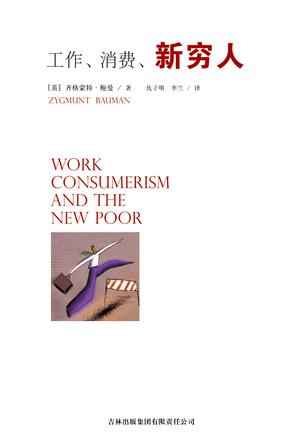
齐格蒙特·鲍曼 著 仇子明/李兰 译
吉林出版集团 2010年6月
鲍曼在书中指出,“依据特定的秩序和规范,每个社会用自己的形象建构穷人,给出存在穷人的不同解释,发现穷人新的用处,并采用不同的方式解决贫困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穷人从被隔离、被禁闭的对象一跃成为巨大的资源,他们被驱赶进劳动力市场,变成现代工人。资本主义的工作伦理一方面解决了工业生产所急需的劳动力供给问题,一方面将工作提升道德尊严的一部分,洗净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肮脏毛孔。
而如今时代不同了,在一个生产过剩、消费主导的社会,高扬的旗帜不再是“工作”,而是选择。有意义的生活,已不可能在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上实现,而只能在超级市场琳琅满目的商品中实现。劳动不再高尚,它只是提供更多消费机会的手段,而被排除在频繁购买活动中的穷人则彻底被社会抛弃。因此鲍曼指出,今天的穷人,比任何过往时代的穷人,都更为无望,他们第一次完全沦为一无所有、一无所用的废料。随着福利国家的倒戈,他们甚至无法把个人的苦难变成公共关怀的对象,反而被描绘为懒惰、有罪、不道德的群体,现代化风景上刺目的污点。
尽管中国还远远没有进入西方式的“消费社会”,但在北上广等超级大都市里,消费主义的旗帜早已猎猎飘扬。关于“月光族”、“新贫族”的讨论,已经将中国版的“新穷人”问题呼之欲出。中国的“新贫族”肇因不在收入而在消费,对于名牌、奢侈品的消费,将这些月薪不菲的新中产们拖入一种入不敷出、举债度日的窘境。在鲍德里亚之外,鲍曼打开了探讨这一现象的新路径,那就是这些疯狂地花着明天的钱的“新贫族”们,才是消费社会真正的合格居民,是消费社会培养的中流砥柱。换言之,消费社会的可怕之处,正在于它是一个大量生产穷人的社会,是一个将中等收入群体拖入泥沼,将其“下流化”的社会。
“端传媒”在纪念鲍曼的文章《从大屠杀到数位时代:为两个世纪把脉的思想者鲍曼》中指出,晚年的鲍曼比许多年轻思想家更关注数位时代(digital age)。2010年,鲍曼提出“流动的监控”(liquid surveillance)概念,他指出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panopticon)模式,在今天的社会中已经被弱化了,取而代之的全天候、线上线下的流动监控,这样的监控模式强调“自动运行”,算法被认为是中立的,具体的个体不再需要承担代码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的任何政治后果,这带来了权力与政治的分离。在政治仍然囿于传统的民族国家框架时,权力却随着资本和数位网络流动起来,传统政治对约束它无能为力。
朴槿惠丑闻:统治韩国半个世纪的“朴正熙模式”将最终崩解?
自去年10月曝出亲信崔顺实“干政门”丑闻以来,韩国总统朴槿惠的支持率跌至韩国建国六十年以来历任总统的最低,数百万民众上街抗议,要求她辞职,国会也启动了弹劾程序,并于今年1月在宪法法院举行了第二次庭审辩论。
上周,韩国延世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赵京兰接受了界面文化的专访,在专访中,她回溯了韩国建国以来历经的政治变革、市民运动与社会思潮,认为“崔顺实事件”预示着统治韩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朴正熙模式”的最终崩解。
赵京兰认为我们应该把“崔顺实事件”放在一个历史脉络中来审视。韩国第一次民主化运动是1960年的“4·19革命”,军事独裁者李承晚因此下台,随后,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于1961年发动“5·16军事政变”夺取政权,从此韩国进入了近20年的“维新时代”。朴正熙是一位颇具争议的总统,他实施了18年军事独裁,但在他的治下韩国实现了经济腾飞。韩国现在的经济和政治仍然在延续朴正熙模式,很多老一辈的韩国人怀念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增长,所以投票给朴槿惠。朴槿惠并没有超越她父亲的执政方式,只是拙劣地模仿和再现,这次“崔顺实事件”却将朴正熙模式彻底打破了,韩国亟待提出一个新的政治框架和经济模式。

朴正熙模式一方面体现在政府和企业的勾连,另一方面体现在企业和劳动者的关系上。在朴槿惠任期,韩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叫做“Hell Korea”,意思是今天的韩国如同地狱,“出身决定命运”的无力感弥漫在整个社会。而对朴槿惠政治能力和执政事迹的歌颂,其实也是出于一种误会,把她错认成了她的父亲,朴槿惠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对国家的未来也没有规划和想法,尤其是对2014年“岁月号”沉船事件的处理方式,令全体国民感到无比的愤怒和绝望。
赵京兰在采访中还回溯了韩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思潮。1945年光复后的三年美国军政时期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激烈对立的三年,反共运动如火如荼,这样的意识形态对立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在知识界中存在,表现为“人民民主”(People’s Democracy)和“民族解放”(National Liberation)之间的分歧。80年代的民主化运动之后,极端的反共主义者在知识界消失了,小团体文化兴起,日常的、小团体的市民运动越来越多,每个团体关注的议题不同,这些市民正是朴槿惠事件中“烛光示威”的主力军。
《上海书评》也于上周发表了《被朴正熙政权迫害的“反骨记者”最后为何“唱起赞歌”》一文,透过韩国著名的“反骨记者”赵甲济撰写的朴正熙传记,探讨了朴正熙执政十八年的功过是非及其对韩国政治经济的深远影响。
2017年正是朴槿惠的父亲朴正熙诞辰一百周年,这位执政十八年的铁腕总统,生前被一些知识分子嘲讽“支持率99%”,死后经过一些年的沉寂,近年来反而在民意调查中获得最高支持率,甩开第二位的金大中两倍多。这种“反转”,也体现在这本《朴正熙》传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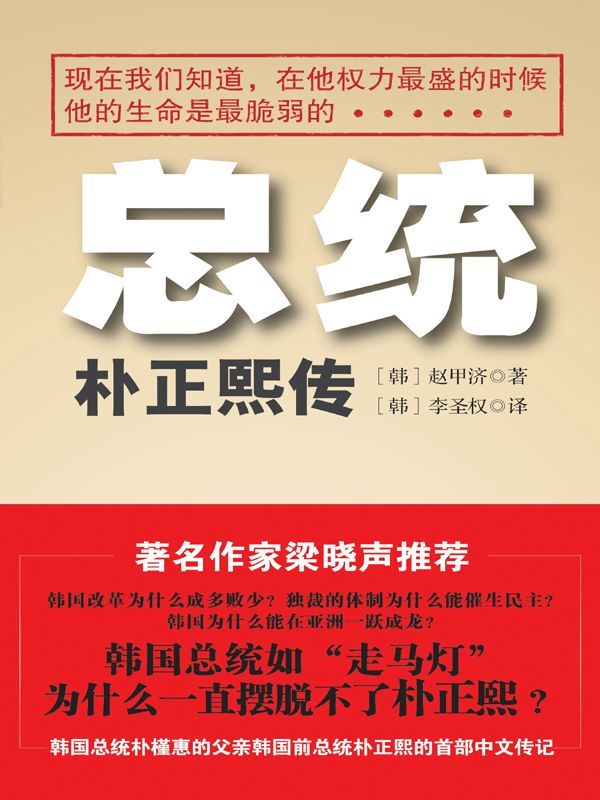
赵甲济 著 李圣权 译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年6月
在赵甲济看来,朴正熙的思想核心就是他实事求是的政治哲学,永远以国家利益为准则来分辨是非,这正是他选择以朴正熙来代表韩国实用主义、独立自主路线的原因所在。朴正熙的实用主义哲学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对待美日的态度。他在上台后便开始与日本谈判建立外交关系,解决历史赔偿与渔业纠纷问题,因为当时韩国急需重建经济的资金援助,除了日本,没有其他国家可以指望(美援的前提是韩日关系正常化),因此他不顾在野党、大学生和舆论的反对,甚至在首都发布戒严令镇压反对声浪,历史证明朴正熙的选择是正确的,六十年代成为了韩国经济振兴的起点。
同样,在朝鲜半岛统一问题上,朴正熙也不拘泥于意识形态,在他看来,“我们既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活的民族,也不是为模仿别国的民主主义而活的民族,比起那些什么主义、制度,实体更重要。”
这部传记在介绍他在经济、国防、外交等方面成果的同时,也没有回避他的一些劣行,例如他授意手下的中央情报部在西德绑架韩国学者、作家,到日本绑架金大中等等。1972年,朴正熙通过“维新宪法”推翻了自己通过军事政变建立的第三共和国,确立了无须大选永远掌权的第四共和国,一劳永逸的独裁梦也埋下了他被刺杀的种子。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