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4岁的玛乔丽·肖斯塔克(Marjorie Shostak)来到了非洲西南部的喀拉哈里沙漠,研究当地的昆族狩猎采集部落,一待就是两年。她并非人类学科班出身,本来也无意于田野调查,只是陪同新婚丈夫、哈佛大学理查德·李研究团队成员梅尔文·乔·康纳(Melvin Joel Konner)一同前往,但在她与昆族女性的接触中,却逐渐对她们的生活萌生了兴趣,而作为上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玛乔丽也很快意识到,以往对昆人的研究缺乏女性视角,于是她开始计划写一本关于昆族女性的书。
然而直到玛乔丽遇见妮萨(化名),她才正式找到了写作的方向。两人初遇时,玛乔丽是26岁的新婚妻子,浪漫的“六八一代”,而妮萨已经是50岁的中年妇女,结过五次婚,生过六个孩子(全部夭折),有过数不清的情人。玛乔丽对妮萨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她总来营地晃悠,要这要那,声音很大很尖,有点狂暴,老想引人注意,没个消停,还有点莫名其妙地卖弄风情”,玛乔丽想躲开她,又躲不掉,无奈之下干脆采访起她来,结果却意外发现,妮萨出口成章、经验丰富、逻辑清晰,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
回到美国后,玛乔丽将采访录音整理成书,并征得妮萨的同意,以她为书的主人公。从采访到成书,历经十几年,其间,玛乔丽从新婚妻子变成了母亲,从本科毕业生变成了大学讲师,她坦言,在写作的过程中,她也从妮萨的故事中汲取了很多精神力量。1981年,《妮萨:一名昆族女子的生活与心声》(以下简称《妮萨》)正式出版,一时好评如潮,此后也不断再版。
《妮萨》一书的意义不仅在于她真实地呈现了昆族女性的日常生活,是研究狩猎采集社会的宝贵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它颠覆了传统民族志强调客观抽离的写作规约,是对一种新的民族志叙事方式的积极探索。《妮萨》中一共有三重“叙事声音”:第一重是妮萨的声音,以第一人称讲述了妮萨充满坎坷却乐观坚韧的一生;第二重是人类学家的声音,综合对其他昆人的访谈,全面地介绍昆族部落的社会文化背景;第三重是玛乔丽自己的声音,包括作者本人的心境、感受,以及她与妮萨和其他昆人的交往。正是这三重声音的并置和转换,尤其是玛乔丽本人的在场,她的情感介入,造就了这一独特的文本,使之成为两位女性跨种族、跨地域、跨文化的一场对话。
1989年,在初识妮萨的20年后,玛乔丽重返非洲,彼时,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并刚刚被确诊为乳腺癌患者,而年届七旬的妮萨却精神矍铄、一如往昔。玛乔丽与妮萨及其族人一起生活了四个星期,临别前,她们还根据当地的信仰为她举行了治疗仪式。玛乔丽根据这次经历写作了《重访妮萨》,这一次,她放弃了多声部的叙事,只留下了她自己的声音,既有她作为一个人类学家的敏锐观察和深刻反思,也有她作为一名女性、一个母亲和一位绝症患者关于生命与爱、疾痛与死亡、女性身体与女性命运的体验与感悟。
1996年,年仅51岁的玛乔丽不幸离世,听到消息的妮萨叹息道,“伟大的神带走了我的女儿,弄瞎了我的眼睛。她就像我的眼睛,神带走她,我的眼睛也就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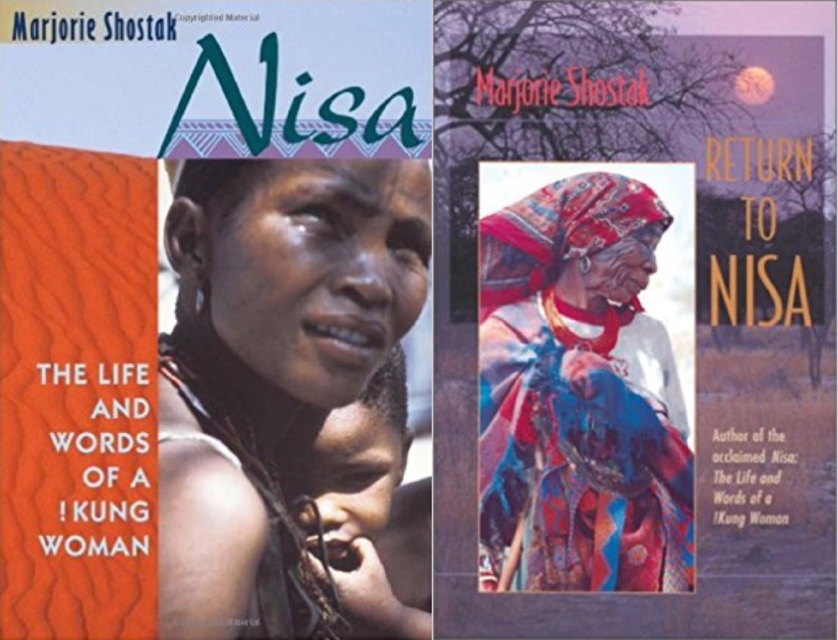
玛乔丽去世后,《妮萨》和《重访妮萨》两本书继续在学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妮萨和玛乔丽个人生活经历与所处社会文化背景的跨时空并置,不断带我们回到那个最根本也最难以回答的问题,作为一个女人,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究竟是什么,使我们超越所有的差异,拥有着共同的女性身份。在三八妇女节前夕,人大出版社和北师大文化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了“何为女性:跨文化的对话”主题沙龙,邀请《妮萨》的译者杨志,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丽,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黄盈盈,《中国哲学前沿》杂志编辑刘翔,中国艺术研究院副教授李修建以及北师大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沈湘平展开对谈。
“女性和自己身体的关系是紧密的、血性的”
“躺着又疼了,一阵又一阵的。然后我感觉到羊水破了,要生了,我心想:’哎哟,可能是娃要出来了。”这是《妮萨》开篇的第一句话,是昆族女子妮萨向作者玛乔丽回忆她生孩子时的场景。就是这第一句话,就把译者杨志难倒了:“不怕大家笑话,我第一句话就译错了,‘我感觉到羊水破了’,这句不是我翻译出来的,是我老婆翻译的,英文说‘I felt something wet’,但作为一个男性,我从来没想到过‘something wet’指的是羊水。”
在杨志看来,翻译《妮萨》给他最大的感触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自然而然的男人的世界”,即便他很想站在女性的视角去理解她们,但是做起来真的很不容易,很多时候并不是故意的,而是无意中就忽略了女性的感受。而当他翻译这样一本作者是女性,主人公也是女性的民族志作品的时候,这种隔膜就暴露出来,他的女性朋友就曾批评他的翻译过于男性化,尤其是妮萨口述的部分,“完全不像是一个女人说的话”。对他而言,翻译这本书,就是作为一个男性去学习女性世界的过程。
而身为女性,《中国哲学前沿》杂志的编辑刘翔对书中描写的很多妮萨最私密的身体经验都感同身受,尤其是怀孕和分娩。昆族的孕妇必须独自到野外去生产,不能有人陪同,分娩时要坐着,不能动也不许哭,否则就会被视为懦弱,遭到族人鄙夷,丈夫抛弃。生育对于昆族女性的风险和难度,远非一般的现代女性所能想象。然而,临盆前女性内心的忧虑和恐惧却是共通的。妮萨在书中回忆说,“孩子还在你肚里时,你会想得很多,心想:‘生娃那天,我会足够勇敢吗?我会害怕吗?我能活下来吗?生的那天,我能忍得了吗?’”刘翔在阅读这段话时,在旁边批了一句“一模一样”。“我生我女儿之前的那几个星期,每天盘旋在我脑海里的是一模一样的问题。”

在刘翔看来,《妮萨》不仅是一部关于妮萨的个人史,也是一部关于女性的身体史。从她小时候嗜吃如命、童年的性游戏,到青春期的试婚、初潮、几次分娩,再到她的衰老。在阅读中,刘翔屡屡讶异于妮萨的直白和坦然,她和她的身体之间是没有隔膜的,她可以直接叫出她身体任何一个器官的名字,可以直接面对她身体的痛苦和愉悦,直接地去承受性、生育和疾病施加于她身体的每一种感受,妮萨的经历让她感到,女性终其一生都在跟自己的身体密切地打交道,这种密切的程度可能远远高于男性。
正是这种共同的身体经验,使女性成为女性,也使每个女性个体可以跨年龄、跨种族、跨阶级地对她的性别身份产生认同,并和其他女性同胞形成联合。刘翔在现场分享了她自己关于生育的私体验:“我生孩子之前非常焦虑,就动用一个女博士所能想到的自我安慰的方式,用知识武装自己,给自己做心理建设,但是没太大作用,直到有一天,我到楼下的小公园散步,看到特别多推着孩子的妈妈,各种年龄层,各种相貌体型,各种受教育程度,那个瞬间我忽然释然了,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类存在,我和世界上所有的女性,甚至古往今来所有的女性,我们都是一样的。”
因此刘翔认为,当我们谈论女性主义的时候,需要首先承认性别的生物基础。“我们的文明已经发展到上天入地无所不能,在手机上按几个键,全世界都涌向你,全世界都听命于你,全世界都来为你服务,但是生育,仍然是一个非常野蛮、非常粗糙、非常血腥的事情。所以不管人类的科技发展到何种程度,女性仍然跟自己的身体有非常紧密的、微妙的、血性的关系,我们是更紧密地束缚于或者说困囿于自己的身体的。我当然举双手赞成波伏娃提出的那个著名的论断,’没有人天生是女人’。因为女性的身份和社会角色都是被建构、规训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女人的确天生是女人,这个以子宫为中心的身体机制,是不可抹杀的。”

“女权主义的目标不是把男人踩在脚下”
作为一个女性,是本质先于存在,还是存在先于本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康丽显然更倾向于后者,“我对于自身女性身份的认知,全部来自于社会化的过程,从我的穿衣打扮到言谈举止,甚至每一个细微的眼神交流,都是社会对我的规训,即便随着我的知识积累,我已经开始对于这种主体性有了反思之后,这种规训的影响依然很难摆脱”。
在康丽看来,如果去追溯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历程就不难发现,女性的诉求是随着时代而不断变化的。从17世纪末开始到20世纪的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主要强调的是男女平权,女性也要上学,也要工作,并且要和男人同工同酬;而到了1960年代,第二波浪潮的时候,女性的诉求就发生了变化,她们要求的不仅是平权,而且是对于女性主体性的一种全新的认知。从这一角度看,“何为女性”的问题不仅关乎女性,也关乎男性,也是“何为男性”和“何为性别”的问题。
进一步说,父权制束缚的不单是女性,还有男性。如果我们希望从女性的角度去打破这种束缚,那么就不应该把议题局限在女性的困弱上,更不应该以性别斗争为目标,要把所有男人踩在脚下。康丽指出,我们应该有一种更激进的想法,那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这种选择与他的生理构造无关。“我们的社会现在只承认男女两种性别,但我知道,像东南亚的很多地方,是存在三种性别认同的,而北美、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有多达七种的性别认同方式。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性别认同,男生不会因为我是伪娘被人看不起,女生也不再会觉得我是个汉子,别人就用异样的眼光看你,那个时候我们才都获得了自由。”
沈湘平也指出,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过去处于边缘的文化,正在逐渐进入主流视野当中,关于男性、女性甚至是人本身的设定都在不断地受到挑战,需要不断地重新定义。因此在这样一个时代问何为女性,其实就是在问何为人。

“关注不同女性的生活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反观我们自身”
女性争取自由的第一步,就是让她们的声音更多地被听到。在康丽看来,作为一部女性主义民族志,《妮萨》的意义在于两点:“第一,它记录了女性的生活,正如波伏娃所说,女性一直以来处于“第二性”的地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们在历史文献中的集体缄默,而《妮萨》让我们听到了女性的声音;第二,它是从女性视角来看待女性的生活,尤其是在大部分民族志的作者都是男性的情况下,这样的作品显得更加难得。”
而在社会学家黄盈盈看来,这本书不仅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对话,还是两种文化之间的对话,它向我们展现了在不同的文化中作为一个女人分别意味着什么。“马林诺夫斯基(著名人类学家,田野调查的先驱)时代的田野调查,还是强调研究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介入,客观地描述他所看到的世界,还是有一种“我是主、你是次”的权力关系在里面。但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于这种民族志方法的反思越来越多,开始强调研究者和田野之间的互动,这本书就是玛乔丽和妮萨互动的结果。”
这种互动,一方面是两位女性的缘分和际遇:玛乔丽刚刚大学毕业,是一位26岁的新婚妻子,而妮萨已经50岁,结过五次婚,失去了六个孩子;另一方面,也是她们各自所属的社会文化的激烈碰撞,玛乔丽背后是社会剧烈变革的60年代美国,而妮萨背后是物质极度匮乏的狩猎采集社会。既有琐碎的日常生活和细腻的女性情谊,又有宏大叙事的历史脉络,二者叠加在一起,构成了这部实验性、复调式的民族志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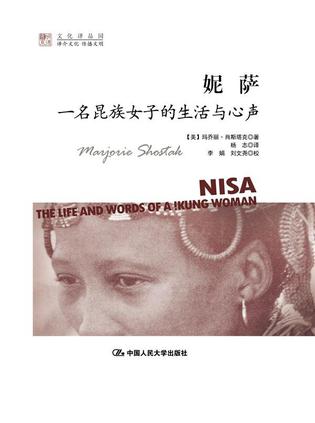
【美】玛乔丽·肖斯塔克 著 杨志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7月
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一个史前社会的女性是如何生活的?在黄盈盈看来,关注不同女性的生活经验,是为了更好地反观我们自身。“其他民族、其他文化对我们造成的冲击,带来的质疑,以及对我们文化中一些规制的挑战,正可以让我们反思,我们的文化中对女性,包括对性和女性身体的一些看法。了解在昆族文化中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中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这种反观性在《重访妮萨》更加突出,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作者本人的回忆录,一个罹患乳腺癌的女性,带着寻求身心治愈的期待重新进入田野,希望从妮萨那里获得帮助——包括巫医治疗——和生活下去的勇气。”
关于玛乔丽在书中对西方文明的反观和批判,也是人类学这一学科的思想潮流,但同时,李建修也指出,这也使得作者不可避免地为自己的笔调染上了浪漫主义的色彩,对于妮萨所在的原始部落,作者的描述带有明显的审美化倾向,这大概也是这本书美中不足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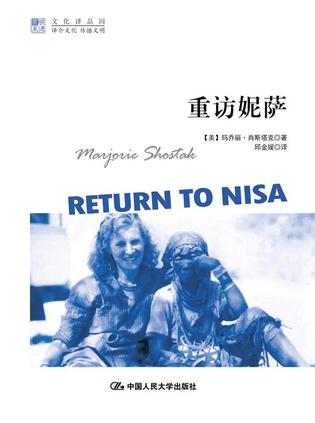
【美】玛乔丽·肖斯塔克 著 邱金媛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