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我批评”这个略显陌生、甚至因某种政治指涉而被污名化的词汇,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日常语境,甚至令人唯恐避之不及。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在传统文化和当代政治实践中,“自我批评”曾经占据过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我批评是儒家一整套修养工夫的基础。《论语》说“吾日三省吾身”,反躬自身不仅是塑造儒家理想人格的核心要求,也是由内而外辐射出一个理想世界的必要起点。
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一种与权力紧密结合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一种对个体实施管控、震慑和约束的有力手段,同时也是一种将个体高效地整合为集体的方式。通过要求个体对自身进行揭露、反省和批评,达到对个体的否定,也使个体获得了在集体中生存的前提。从这一意义上说,自我批评和自我否定恰恰是为了自我确认和自我保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批评和自我批评则是围绕反思、否定“文革”展开的,其目的是要回到或重建西方式的启蒙理想,而对这一启蒙理想本身,却是未经反思、全盘接纳的。
后两种形式的自我批评,正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近20年来思考研究的问题。在去年出版的《材料与注释》一书中,洪子诚谈到了1957年以来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的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道德问题;而在90年代初出版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他论述了80年代集中涌现的一批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中处理历史和个人问题的三种不同立场。
日前,洪子诚在中间美术馆发表了以“自我批评”为主题的演讲,从他对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出发,结合他个人的经验与感受,探讨了在错综复杂的历史遗产和现实境遇下,现当代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如何面对自己,诉说自己的问题。

将受难者英雄化,阻碍了我们思考历史责任
洪子诚认为,当今社会自我批评缺失,自我满足和自我隔离成为普遍趋势,这既是由当前纷繁的社会状况所造成的,同时也有着复杂的历史缘由。
在他看来,上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出现了一个针对刚刚结束的文革的反思潮流,它既针对历史的一些重要问题,同时也面对个人。总的来说,这一潮流是在新启蒙的框架下进行的,80年代是张扬主体性和人道主义的时代,因此涌现了许多叙述“文革”浩劫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这也可以算是80年代出现的一次自我批评的高潮。
我们该如何评价80年代这场反思运动呢?洪子诚认为其意义至今也不容低估,但站在今天的视角回过头去看,我们也必须承认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遗产一直延续至今。今天我们重提自我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偿还80年代反思运动所留下的历史债务。
在80年代末写作的《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一书中,洪子诚谈到了80年代反思运动中作家处理历史和个人问题的三个类型。占大多数的一类作品,是通过虚构一个英雄的形象,来回避自己的历史责任。这类作品在意识形态和艺术方式上,突出了文革的苦难和历史幸存者的形象,把历史悲剧化,淡化了喜剧和荒诞的成分。正如昆德拉、齐泽克等思想家指出的那样,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不存在真正的(包含了喜剧和荒诞元素的)古典悲剧了,对苦难的突出和强调成为了主流。反复出现的受难者/幸存者的形象,固然是一种历史事实,文革中许许多多知识分子都历经坎坷,一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提供这种历史见证的意义非常重大;但这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思想倾向和美感形象,受难者的形象也值得我们反省:赋予受难者以英雄形象和崇高感,阻碍了作者思考自己在历史中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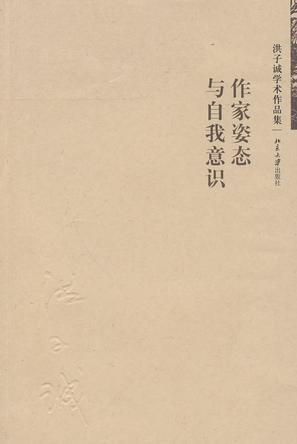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1月
令洪子诚意识到这种对历史受难者英雄化书写的问题所在的,是加缪的《鼠疫》。文革之后,文化封锁解除,外国文学陆续被译介到中国,存在主义作品在当时的青年中影响很大。洪子诚也读了不少存在主义小说,其中就包括加缪的加缪《局外人》和《鼠疫》。他认为《鼠疫》兼具现实性和寓言性,通过中世纪发生在北非的一场瘟疫,讨论了人们在面对灾难性的历史事件时应该怎样思考的问题。
洪子诚在《我的阅读史》一书中写道,《鼠疫》是一部用第三人称写的第一人称小说,它用编年史的叙事方法记载了从鼠疫开始到封城,到不断有人死去,再到最后战胜鼠疫,封锁解除的全过程,然而读到最后读者才发现,一直以第三人称讲述整个事件的人,就是故事的主人公——鼠疫中的一名医生。这位医生说过一句话,“要治疗一切能治疗的东西,同时等待得知(因为小说中一直强调”我不知道“,当事人对灾难发生的历史根源和演变的历史逻辑一无所知),或者观察”,令洪子诚印象深刻。
洪子诚立刻想到了伤痕文学,并自然地产生了对这种英雄化的苦难表述的不满,因为这种表述“阻碍了历史受难者对他们现实处境的清醒意识和更深层的追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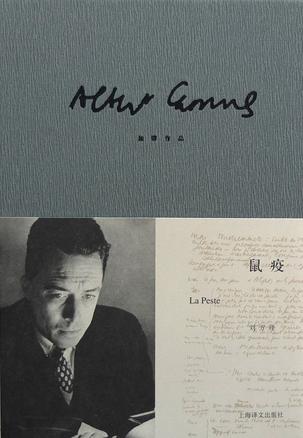
阿尔贝·加缪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3年8月
在真实的历史中,这些曾经的“文革”受难者在80年代之后获得了补偿,而这种补偿赋予了他们比50年代更高的地位和声誉。正如洪子诚的学生、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在一本书中所说的:“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受益者敢于明确承认,他们所获得的一切只是体制给他们的一种威慑性的补偿。”
从社会主义体制走出来的保加利亚批评家兹维坦·托多罗夫曾说过:“如果说,没有人愿意成为受害者,反之,却有许多人希望他以前曾是,以后不再是受害者。”他们渴望受害者的地位,是因为受过的苦难越大,得到补偿的权力也就越大。在洪子诚看来,这正是这一类反思文学和伤痕文学留给我们思考的问题。
善恶正误的二元划分将掩盖当代历史的复杂性
反思文学中还有相对占少数的一类作品,主题是经过历史的转折,主人公从英雄的幻觉里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过的是普通人的一生,杨绛的《干校六记》正是这类作品的代表。第三类反思文学则是通过严肃甚至近乎苛刻的自我反省和自责,试图重建“文革”中已经遗落的文人英雄的启蒙角色,比如巴金的《随想录》。
文学界对《随想录》褒贬不一。一些香港和国外学者认为巴金的《随想录》文学性不高,巴金先生对此做出过一个回应,他说《随想录》不是作为文学作品来写的,而是要为历史提供证言。汪曾祺先生和小说家张洁也认为,巴金对自己有着近乎残酷的自省,《随想录》是带着血痕写的。

作家出版社 2005年1月
在洪子诚看来,巴金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作家,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叙事和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可以总结为:全景式、三部曲式的结构方式,发自内心真情告白的叙事方式,小说的叙事者充分介入的干预态度,以及对世界善恶分明的道德态度。《随想录》也贯彻了这种艺术风格,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提醒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然而在巴金对于历史和自己的检视与反省中,也存在两个很大的问题。首先,巴金一直都是启蒙主义的信仰者,他对历史的反思基本上是在一个未经反思的启蒙主义框架下进行的,人道主义和人性是他评价历史最主要的尺度。其次,巴金过分关注道德层面,虽然道德是有力的武器,但道德的评价体系和以道德看待历史的方式有其局限和脆弱性。依据道德指标对历史事件做出二元划分,诸如善恶、正误、美丑、真伪、反叛与屈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当代历史的复杂性。
洪子诚指出,当代中国是泛政治化、泛道德化的社会,政治深入到普通人日常的言语和行动中,道德评价的标准也渗透到每个人的观念里,进一步说,所有的判断和评价都是在政治和道德的框架下进行的。然而,“一个标榜道德高尚的社会,也是主动宽恕和依赖臣民道德败坏的社会”。
在揭发被批判者的道德问题的过程中,批判者往往也采取了非常不道德的手段,在当代的历次批判运动中,批判者的道德并不比被批判者的道德高出许多,甚至很多时候还更加不堪。在洪子诚看来,这正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如果仅从道德层面去划分善恶、正误、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界限,并把这一界限看作是清晰绝对的话,就很容易掩盖了这一复杂的情况。
回溯自己在文革中批判和被批判的个人经验,洪子诚说:“在文革中,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界限并不像伤痕文学里所表现的那样清晰。”相反,荒诞的是,批评和自我批评逐渐演化成了一种没有实质内容的仪式。例如,文革期间北大中文系曾揪出了一个反动小集团,在中文系内部被反复批斗,罪行是恶毒攻击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但是恶毒攻击的内容却要保密,不能公开,因此批斗会好像一出荒诞剧,甚至比荒诞剧还要荒诞。正如昆德拉在谈论卡夫卡小说时所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为罪行寻找惩罚,卡夫卡的主人公则是为惩罚寻找罪行。”
在为惩罚寻找罪行的过程中,敌人和朋友、批判者和被批判者的角色不断颠倒错乱。洪子诚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一文中,详述了历次文艺批判运动中“颠倒错乱”的过程,这样做“并不是要把水搅浑,将历史视作一笔糊涂账,以为人和事没有正误、美丑、善恶之分,那被锁定在‘历史链条’上的‘零件’(历史参与者)的思想品格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而在于让我们能廓清当代政治生活中权力与道德关系的实质”。在两者无法分辨的时代,或者说,在道德评价成为政治斗争重要工具的时代,“道德唯有在权力的强制之中并且在实体化的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权力也是作为道德权威体系之一始能显现其本身的社会意义”。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年9月
洪子诚在演讲的最后指出,自我批评除了要“从自己说起”,还需要思考“说什么”和“怎么说”的问题。在后现代,在历史和现实种种问题错综复杂、带有极大含混性的社会环境里,在语言多元化的时代,如何面对自己和如何诉说自己,是非常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要知道,光靠真诚的态度是不够的,思想资源的问题更为重要,也就是我们反思自己,寻找自己情感、思想、行为中的裂缝的参照物和凭据是什么的问题。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