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敬明最初以敏感忧郁的文学少年形象出道,但如今,我们差不多要遗忘他的“作家”身份了。至而立之年,他是“闷声发大财”的文化商人与言行高调的电影导演,2013年还拿下过“中国梦践行者”的荣誉称号。《南方周末》略带揶揄地描述他跻身当红都会小说家的经历:“生长于西南小城,发达于超级大都会,作为中国最普通的‘民二代’,郭敬明把握了大时代中的小机遇……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小时代”。
不过,自抄袭风波始,郭敬明这十几年来从未摆脱过形象危机。不论小说的拜金言论、电影的华丽空洞或对少女少男的教主般的消费感召力,还是私人特质如身高、容貌,都能引来众人的嘲讽或不屑。
或许,我们可以借机将目光拉回到郭敬明的作品。尽管文化人对他往往不屑一顾,但郭氏小说的影响力却不可小觑。郭敬明仍以小说写作为业时,他最引以为傲的创作版图无疑是上海。而一度,他曾受人瞩目、也备受污名的身份是“小城青年”——人们津津乐道并反复指认这位“征服大上海”并试图为之代言的“凤凰男”虚荣拜金,本性难移,他书写上海的合法性亦因“外地人”的身份而一再遭受质疑。
上海书写一向强调作者身份的本土性,从小城青年蜕变成新上海人之后,郭敬明能算是新一代的上海文学代表作家吗?来自四川小城自贡、发达于国际都市上海的畅销小说家,又如何想象和书写上海?带着这些问题读郭敬明,便能发现他所引领的烜赫一时的文化现象背后,透露出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书写的大转变,这也与当今中国的大都会发展趋势息息相关。
郭敬明:新一代的上海文学代表作家?
2013 年时,北大教授张颐武曾在博客上将郭敬明列入上海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在张爱玲远去,程乃珊故去,而王安忆已越来越和上海年轻一代疏离而影响力淡化的时刻,郭敬明变成了上海想象的新的部分。”

此说法一出,当即遭到众人反对,网友纷纷以郭敬明是四川人而非上海人、其作品非纯文学等理由加以驳斥。《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近乎决绝地撇清郭敬明与上海的关系:“郭也许跟这个时代什么都有关系,就是跟上海想象没任何关系。”

有趣的是,我们早已频繁使用郭敬明的代表作“小时代”来命名当下所处的时代了,而近百万字的《小时代》恰恰是他“献给上海的金色赞美诗”。实际上,上海想象不可能总是诉诸老上海的风华灵韵——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和城市化改造令这种“上海性”难再追寻,城市旧日的生活肌理不断分崩离析,或物化为有待消费的怀旧商品,我们早已身处改头换面的“新上海”之中。郭敬明所捕捉的正是这样一种新的城市景观,他曾对记者说:“希望以后提起新上海,人们就会想到我的《小时代》”。不得不承认,《小时代》系列小说及电影有傲人的销量和票房,这无疑使它成为今天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上海故事之一。这些故事,有力地参与重构了新世纪新上海“美好图景”的想象——一个光鲜亮丽的国际化都市,一个跨国中产阶级仿佛从来如此生活的地方。而新上海的城市想象,恰恰是我们对当下中国大都市的普遍想象——目下影视剧里的北上广再现皆是如此。
作为新一代上海文学代表作家的郭敬明,便是在这个意义上成立的——他确信自己真正把握了这座城市的精华所在,这种把握与他是否来自何方并无关联,因为他对于上海之“精华”的领略只牢牢系于上海的当代都市景观之中。
从上海苦恋开始,学习成为“新上海人”
早在中学时代的散文之中,郭敬明已频繁倾诉自己对上海的苦涩迷恋:
我的根似乎是扎在上海的,就像人的迷走神经一样,一迷就那么远。这多少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要让不爱上海的人出生在上海?上帝一定搞错了……我的同学曾经在复旦大学里逛了整整一天,并且拿了很多照片给我看。我望着那些爬满青藤的老房子目光变得有点模糊,我想那才是我真正的家。
上海的历史感被转化为小城少年心中“奇幻之都”难以言明的灵韵,同样构成他未来想象的核心:“上海啊,上海。这两个字是多少人心里的梦,也是多少人心里的痛。它仿佛是一个庞大的终极梦幻,也同样是无边的灰烬旷野”。可以说,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符号,“上海”的意象自始即盘踞于他的书写版图,并几乎被视为中国所有城市的中心,其地位正如19世纪法国的巴黎——外省人的梦想、野心与未来都系于此。
郭敬明这样描写自己初抵上海、第一次“从人民广场地铁站钻出地面”时所见的世界:“庞大的。旋转的。光亮的。迷幻的。冷漠的。生硬的。时尚的。藐视一切的。上海”。接连抛掷的形容词与紧张短促的句点,定格了小城青年初到繁华冷漠的都会遭受的震惊与创伤。
致力渲染大都会的现代性震撼和视觉经验,这种都市书写并不罕见。上世纪 30 年代,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就是如此呈现上海的声光化电。吴老太爷从乡下乘轮船来到上海,怀中紧抱着《太上感应篇》坐进汽车,一路被南京路上光怪陆离的灯光和高耸的摩天大楼惊得全身发抖,昏死过去。
郭敬明书写上海的另一显著特征、也是他一以贯之的再现方式,则是如何辨识本地人与外省人的品味。散文《荒芜尽头与流金地域》里有这样一段微妙的心理描写:
你并不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地了解到罗森和好德之间的区别。在最初的照面里,他们都是二十四小时彻夜不休的夏天里嗖嗖地往外喷着冷气冬天里落地玻璃上结满厚厚雾气的超市。你不会了解到那些小资女青年在文章里,为什么对罗森推崇备至,而对好德不屑一顾。后来你才会慢慢地发现,罗森的饭团会好吃很多。推开门的时候扑面而来的是混合著台湾或者日本一样的气息,没办法用文字形容,却可以真实地涂抹在心里。
初抵上海的小说家觉察到小城青年和上海人(以“小资女青年”为代表)的微妙差别,在于能否从细微处分辨两家便利店的高下差别。实际上,郭敬明中学时代的文章便已深谙把玩文化资本的象征价值,比如散文小说《天亮说晚安》之中,听平克·弗洛伊德的文青便鄙视听迪克牛仔和臧天朔的文青。在那些吐露心声的早期作品之中,种种看似稀松平常的都市经验,都是作者学习融入都市的重要一课。这意味着一场身份的“改造”:自小城镇向大城市的流动要求年轻人告别乡土,习得全球城市的生活方式,成为一名合格的中产阶级“新上海人”。

小城少年的这样一种上海迷恋,要置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关系之中来理解。1990 年代以来的大都会发展趋势与竞逐之下,曼哈顿式的大都会成为我们想象城市的主流方式,北上广与那些我们戏称为“十八线小城市”的内地城镇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不过,郭敬明的此方梦土在某种意义上又非上海不可。不同于那些急于发展、力求模仿的后进者,上海曾深受上世纪西方殖民或半殖民历史及其现代性都会遗产的形塑,1990 年代以来的上海开发,将上世纪初“东方巴黎”的都会传说与当下“全球城市”的欲望意象无缝接合,使上海成为整个社会想象“中国大都会中产生活”的最佳空间。
从《长恨歌》到《小时代》:“顾里们”宣告“老克勒”的退场
王安忆的著名小说《长恨歌》里,有个反面角色叫长脚。外乡人长脚为了融入上海,如同十九世纪英国企图混入上流社会的穷小子扮作“假绅士”一般,为自己捏造了一个天方夜谭般的显赫身世。
香港中文大学的黄宗仪教授对这一段有个有趣的解读,说王安忆透过长脚一角暗讽“看似最全球化的人物往往是最乡巴佬的”,因为他们无知地混淆了“老上海不朽的都会传奇和当代大肆炒作的地球村景象”。故事结局中,这位野心勃勃的外省人为谋财而勒死了三小姐王琦瑶——后者某种意义上是王安忆认同的老上海日常生活的象征。
这么来看,长脚的破坏性隐喻几乎是明显的,外省人某种意义上代表了全球化、城市化的“代罪羔羊”——因此要讲一个真正的上海故事,就要辨别里面的“外省人”,然后加以排除。的确, 1990 年代以来那些不同程度上被经典化的上海书写之中,“上海性”往往定位于这座城市的“过去时”和“老后裔”:“只有张爱玲时代的老上海才是货真价实的,1949年后的上海则是那样的‘平庸’和充满了‘令人羞耻的拮据’,而现在的一切不过是赝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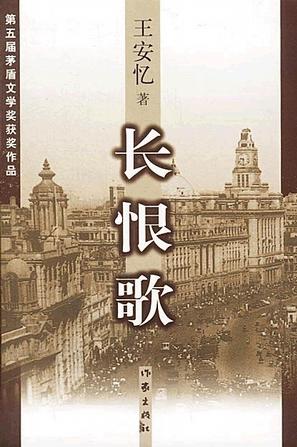
不过,郭敬明却要扭转 “新上海人”与“老上海后裔”的“新”、“老”之别。程乃珊在《上海探戈》中盛赞“老克勒们”的生活品味,相较“由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催谷的新生代上海人”能“掼几条上海马路”;但《小时代》中,作为都市新贵的“顾里们”则宣告“老克勒们”的退场,在新空间中登台的是作为全球城市新贵的新上海人。
在全球城市的发展趋势下,上海将自我改造为一所向全世界敞开的“大都会”,却又与此同时要求将自己收紧为一个排斥性的“本土”的概念——只不过,这种“本土”不再依托于上海方言、弄堂传统社区或是别的什么,而是郭敬明透过小说所重新定义、由都会新中产文化所主导的“上海性”。
女主角顾里成为坐拥象征资本、走在华丽度会生活最前沿的代表人物——这正是“新上海人”之中跨国精英的形象。《小时代》的上海只限于“上只角”的市中心(浦东陆家嘴的建筑群也只能作为窗口的风景存在),其它城区无不被鄙夷为“外地”与“乡下”。借顾里之口,郭敬明对那些与都会格调格格不入的外地人施展了俏皮而恶毒的讽刺。事实上,如何在上海百纳百川的公共空间(如人民广场)中辨识外地人的可笑样貌和举止,已成为《小时代》这套小说最津津乐道——也是最臭名昭著的内容之一了。比如,顾里调侃北京女人穿秋裤走进爱马仕店的样子,说是她“ 1998 年看完《午夜凶铃》之后看过的最恐怖的画面”。
郭敬明爱用“把品牌丢出来”的写法夸耀上海新贵的生活,盛大铺排 Prada 毛衣、Dior 礼服、Armani 沙发等奢侈的都市符号。这不是新鲜的写法,上世纪末自称“上海宝贝”的作家卫慧早也发扬光大了这种繁复的铺陈,她笔下的上海充满殖民情调,上海宝贝们流连酒吧和咖啡馆,与中国男人相恋的同时,又陷入与西方白人男性的情感纠葛。试图为 1990 年代末上海“新人类”代言的卫慧同样从南方小城来到上海,她因小说风靡全国而被媒体冠名“上海美女作家”。
不过,相较卫慧的上海书写,郭敬明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不再费力描摹那些符合西方想象的殖民化空间,即便是租界遗迹也被赋予了新的发展意涵,奢华繁荣的景象被寄寓于“最新”、“最高”、“最大”、“最快”的中国式都市想象。
重新定义“新上海人”的魔都
在今天,一个初抵魔都的外省人会如何书写上海?可能是排起长龙的网红奶茶店和点心铺,新天地石库门装饰的昂贵餐厅和酒吧,或者……这些在会玩的城里人看来可能也已经过时,因为新事物正不断涌现。
郭敬明几乎前所未有地将上海激进的城市建设和景观更迭,作为小说重要的兴奋点。这种发展的兴奋感令小说中的人物感同身受,城市建设播报与青春故事的讲述互为缠绕。上海的城建更新速度令我们的小说家最为激赏:
投资360亿打造的中国超级工程——虹桥交通枢纽工程,将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交通枢纽。三个天安门广场的面积里,集中着高速铁路、磁悬浮列车、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客运、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及民用航空。整个工程像是一个发光的巨大怪兽雄踞在上海的西部,在未来,人们将从它的体腔内部的各种肠道,迅速被运往上海的各个地方。
上海的一切景观都面向“未来”,又随时成为“历史”,因为它的发展潜力不可限量。黄平曾批判《小时代》呈现了“一个历史完全被架空、可以与纽约、伦敦、东京彼此置换的上海”。事实上,郭敬明正要如此改写上海再现的传统。在《小时代》中,上海非但与纽约、伦敦等老牌全球城市相较毫不逊色,甚至后来居上、更胜一筹。这种城市的礼赞,与上海90年代以来城市化、全球化发展规划中的理想上海形象可谓高度重合。如房伟所言,“《小时代》第一次完整地呈现了中国式繁华景观的想象。”

《小时代》中的上海城市空间,体现出永不止息的新奇华丽,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以及不可磨灭的阶级区隔。而《小时代》的故事,几乎宣判了“青春”一词在当代中国所内置的阶级属性:“长得好看又有钱的人才有青春”。于是,郭敬明对于上海神话不带批判色彩的残酷礼赞,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少男少女们的“悲伤”来源之所——因为他们必须以“征服”的姿态来处理自身与城市的关系。
《小时代》中的角色们有这样一个日常生活癖好,在高处俯瞰整座城市的繁荣地景——这正是19世纪巴黎外省人小说中常见的场景。在华丽的聚会、节日或是晚宴的尾声,年轻而耀眼的男女站在露台之上俯瞰城市灯火,宣告那些通过“个人奋斗”达到与之匹配的经济及象征资本的“外来者”,已成为这座都会当之无愧的新主人。然而,“小时代”的征服感却始终无可奈何地透露出一个“悲伤”的信息:这座耀眼的、物神一般的大都会实际上无法为任何人所征服。这是小说人物周崇光(某种意义上也是郭敬明的自我投射)那段著名的个人抒怀所表达的意象:面对大都市的“浩瀚宇宙”,个体存在将永远如同“渺小星辰”一般“微茫”。
可以说,凭藉《小时代》此一声名狼藉的上海小说,郭敬明不但完成了对于“当代上海”的再定义,甚至吊诡地改写了“当代中国”的时代基调。鲁迅笔下处于现代化悬而未决的关口、方生方死的“大时代”,由此转化为被明晰的大都会丛林规则所限定、以原子化个体之微茫感为填充物的“小时代”。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