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次对马东的访谈,许知远成为了大众公敌。在访谈中,许知远强烈的自我表达欲,对采访对象、对 90 后和这个时代的偏见遭到了广泛吐槽。接着,2016 年许知远访谈俞飞鸿的视频也被翻出来,在完整版的采访里,他一遍遍地变着法儿又略带骄傲地问俞飞鸿“有男朋友吗?”、“这样的男人你喜欢吗?”、“就没有想过要依靠男人吗?”、“真的没有想过吗?”这种居高临下审视和轻薄女性的姿态,更近一步引发了人们的怒火。
在这场围攻中,描绘许知远的种种犀利金句不断诞生,有网友觉得,许知远对女性的态度彰显出“曾经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终于变成了如今丑陋的老男人”——不真正关心社会,自恋,爱好批判别人,性别歧视……种种特征异常鲜明,一个守旧的“姿势分子”形象跃然纸上。不过,对许知远的个人攻击再犀利也不能解决社会问题,这场大众 vs 精英的战斗背后,还有更深远的现象值得探讨和批判。

大众v.s.精英:新媒体背景下的话语权争夺
近期的相关争论中,许知远被认为是一类守旧精英知识分子的代表——当然,也有人批驳他的文化和素质不够称为“知识分子”——但总体而言,至少他塑造和表现出了一种非常传统的中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
从身份上,许知远是地道的话语权所有者,他曾为多份知名杂志撰稿,更是自己担任几本出版物的主编、内容总监,也曾因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而风靡一时,在文坛叱咤多年,能够号称“公知”。在表达方式上,他的文字明显区别于大众写作,习惯于表达自己对社会的失望,但又提不出大众看来“建设性”的意见,只是有着车轱辘式反反复复的抒情和悲凉。这一切充分代表了大众心中当代社会中男性知识分子的某些典型特征:充满理想主义情怀但不接地气;不真正关心社会发展,而是在无止境居高临下的说教中充满着偏见和自恋。大众强烈抵制和反对的并不只是许知远,而是具象化的许知远背后站着的面目模糊但是特征明确的传统文人群体。
反感知识分子这一现象,建立在新时代媒体发展和话语权结构变幻的语境之上。

在旧式媒体发达的社会中,由于话语传播的权力结构,知识分子具有绝对的权威和话语力量——只有他们可以在公共视野中发言,用脱离大众的精英式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在技术推进,新媒体的发展,娱乐的大众化等种种条件催生下,大众话语权逐步崛起,传统精英自上而下的“话语统治地位”开始丧失。大众可以通过互联网带来的新浪潮掌握某些知识优势,例如“浅薄”的90后可能比许知远更懂动漫。于是,草根大众从以往被教育和被审视的被动角色中解放出来,自由表达对文化名流的不满。
在这样的情况下,目前已经开始慢慢形成的多重价值观社会对旧观念的抵制变得顺理成章,一些压抑已久的社会观念冲突爆发出来,显现出大众 vs 知识精英的态势。种种冲突当中,有两个明显的“痛点”恰好就是许知远这两次“走红”的原因——“娱乐化”问题和对女性的态度问题。
社会的娱乐化是知识精英和大众的显著冲突之一。通过大众娱乐在欢快的心情下接受知识,已经成为了互联网新一代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为什么不少网友认可《奇葩说》的原因——类似的大众文化产品由于传播范围广,影响力大,尽管对某些话题的展现虽不深入,也比较偏娱乐化,但能够在社会中引发讨论和思考。
与此同时,不少知识分子早就开始批判和反思这种社会娱乐化常态。最著名的是利维斯派和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的指责:“装腔作势的空谈”缺乏道德严肃性和审美价值,造就“欺骗性的意识形态”,使人们满足于虚假的意识,沉溺于无思想的享乐……
这个议题本来值得反思与讨论,但比起大众娱乐亲切和蔼的传播方式,一些发自知识分子的批判显得尖刻又高傲,没有现实意义和具体举措,只是动辄高呼情怀,用喋喋不休的说教让大众心怀不满。“庸众”,这是一个在知识分子语言体系当中高频出现的词。许知远曾多次表达对大众浅薄的不满,在文章《庸众的胜利》中,他写道:“是公众的无知、浅薄造就了韩寒成为意见领袖……他们需要的只是情绪宣泄出口。” 2015 年 5 月,《南方人物周刊》把青年领袖奖颁给许知远和演员佟大为,宋佳,歌手钟立风等人……许知远上台发言称:“看到大家对娱乐、对明星那种发自内心的追求,对世界完全没有个体精神和审美,沉迷在肤浅的大众狂欢里。”当然,许知远的姿态不是独特的,只是当代精英的一个缩影——就算自己未必视自己为知识分子,他们也往往粗暴地把大众归类为无脑盲从的傻子:冯小刚批评中国有太多垃圾电影票房高的原因是有太多“垃圾观众”;而罗振宇的《罗辑思维》有一期名为《庸众的迫害》,批判无知的庸众的种种愚蠢行为是在伤害社会精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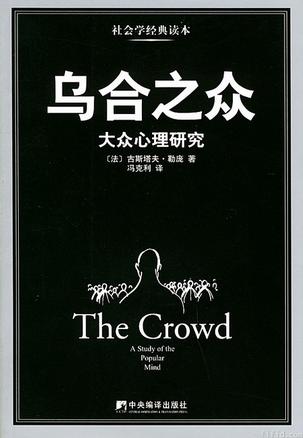
而在对妇女态度的问题上,一些知识分子也似乎和大众完全脱节。力挺俞飞鸿的网友们多少受到了当代中国女权发展的影响。独生子女浪潮,经济发展,文化开放……新环境下生长起来的一代有条件也有能力反叛压制女性的传统思想,号召社会用更多角度和更合理的方式去对待女性,而不只是单一地把女人视作审美的客体。但一向处于权势上层的一些男性知识分子,似乎不能接受女性的崛起,他们还希望停留在过去时代审美女人,掌控女人,保护女人,拥有女人的主导性地位,“文艺圈直男癌现象”频频发生,不胜枚举。许知远曾经写过:“在上个世纪的后半叶……生硬的女权主义者拼命挤压着女人身上芬芳的汁液,把她们变得勇敢却干燥起来,她们错误的男性化行为与倾向理解成坚强”;周国平也曾在微博发表言论称:“男人有一千个野心,自以为负有高于自然的许多复杂使命。女人只有一个野心,骨子里总把爱和生儿育女视为人生最重大的事情。一个女人,只要她遵循自己的天性,那么不论她在痴情地恋爱、在愉快地操持家务、在全神贯注地哺育婴儿,都无往而不美。”;韩寒则在采访中说希望女友和太太“和平共处”。此类言论要么充满了浪漫化但毫无掩饰的性别区分思想,要么直接表达了对妻妾成群的婚姻关系的期待,完全和社会大众期待的社会发展趋势背道而驰。
种种由于地位不同产生的矛盾,结合各色“知识分子”的负面新闻——民众想到大学老师就想到了烧钱课题和掺水论文;想到经济学家就想到了利益集团和无耻鼓噪;想到电影导演就想到了潜规则和炒作烂片;想到作家编剧诗人等就想到粗制滥造故弄玄虚……人们把无数压迫已久的社会问题和情绪顺着许知远“处处是槽点”的访谈发泄出来,喷薄的网络语言成了大众对抗精英的新子弹。
公共讨论的消解,与文化消费的崛起
在抵制和批评许知远的过程中,看似通过新媒体赋予的话语权,大众完成了一次新话语和旧话语的交锋,展现了一场草根对上层,年轻一代对年老一代发起的成功“抗争”。不过值得警惕的是,但这种抗争几乎完全是被建构在文化工业和消费产业的框架内,各色热点容易被轻易地建构和消解,最终流为狂欢式的发泄,而不是真正有建设性的社会讨论。
随着新闻和评论发酵,讨论逐渐简化为窥私和文化偶像之间的站队。眼下最火热的的讨论点,只是对许知远个人“解释权”的争夺,站在不同立场的“挺许派”和“倒许派”刀剑相向,把许知远个人变成窥探和分析的对象,从《为什么许知远是最令人无比尴尬的公知》,到《珍惜许知远,哪怕不喜欢他》、《许知远这个人》、《13个许知远冷知识,我们就是他公司里虚张声势的90后》,再到《调戏俞飞鸿初夜,满嘴“性、情爱、潜规则”,许知远这代中国老男人有多丑陋?》,舆论场对许知远个人分析的无孔不入,已经到了信息过载的地步。而那些更具有启发性的议题,例如以《奇葩说》为代表的娱乐节目如何对抗传统知识传播,是否能够达到普及知识的目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存在怎样的问题等等,都消失在无穷无尽的个人攻击或者吹捧里。这场本能够演变为“当代知识分子和公众媒体应该如何作为”的议题探索,变成一场唾沫横飞、八卦四生的娱乐盛宴——奇观化、情绪化的信息在媒体操作下压缩了深度讨论的空间,更为讽刺的是,许多知识人士也和他们眼中的“庸众”一样投身其中。
就算稍微涉及到大众和知识分子的思维鸿沟以及话语冲突,相关讨论也往往粗暴地呈现为非黑即白地为偶像站队的形式:是挺马东还是许知远?是挺俞飞鸿还是许知远?只要是站在大众立场反抗知识分子“旧观念”“旧统治”的文章和评论,几乎都会在批判许知远的同时赞美马东或者俞飞鸿,但事实上他俩无论社会地位还是从事的职业上,谁也不比许知远离大众更近。马东既是典型的文化商人,同时也是知识分子。他最为大众所熟知的作品《奇葩说》正是靠贩卖观点和知识展演为主题,包装文化偶像,通过造星运动来获得利益。但是在批判许知远的文章中,马东往往被描绘成大众的代言人和打破知识壁垒的先驱者。而和俞飞鸿相关的评价更为离奇。群众一边批判许知远采访俞飞鸿时频繁用“你真的很美”打断她的思想表述,只用外貌来审视她,一边却反复强调她的美貌和气质,类似“奔50的俞飞鸿反而在岁月的历练中越发迷人”,“俞飞鸿不愧是女神,又美姿态又好看”的评论屡见不鲜,和每一个女性息息相关的女权话题变成了崇拜俞飞鸿,支持“女神权”的呐喊。

由于从新媒体和大众媒体中获得了与传统权威对抗的话语权力量,人们很容易陷入对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无批判性的崇拜。许知远的话题看似是中年人与年轻人的代沟,以及“知识分子”与“庸众”的区隔,仿佛战胜了许知远就胜利完成了大众对权威的战斗。但《十三邀》和《奇葩说》其实本质上并无区别,它们虽然包装风格和探讨形式不同,但都是互联网大众文化节目产业链的一部分,并且都有明确的观众服务意识,在呈现方式上选择谈浅不谈深,用情绪和冲突而非理论说服观众。在《十三邀》里,许知远与其说是一个采访者,不如说是一个表达者,节目组也无意压制他的表达欲,反而更加凸显“偏见”这个话题点,甚至故意剪辑进去一些看似“谈崩了”的尴尬瞬间,以两种不同立场之人的表达与碰撞作为节目的核心内容,塑造冲突,吸引观众。镜头感极强,懂得驾驭剪辑和音频节奏的许知远,并非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相反,他很擅长包装和贩售自己对大时代的焦虑和愤怒,并准确地戳到了社会的痛点。
在《花样姐姐》、《中国有嘻哈》、《极限挑战》等等真人秀节目中,我们已经习惯了各种娱乐明星之间的“互怼”。温吞的迎合与其乐融融的氛围不再吸引观众了,交锋和矛盾才是最大看点。只要一发生冲突,收视率就马上飙升的现象,早已早成就业界心照不宣的绝密法宝——有冲突要拍,没有冲突制造冲突也要拍。巨大的流量与话题度已经让“怼”成为各色娱乐节目的主要气质,伴随着一篇又一篇话语夸张、立场偏颇的公关稿。
不过,文化名流像偶像明星一样参加“互怼”,还并不是常见的现象,“知识分子”式的出言不逊能够博得大众的目光,正如每次冯小刚在新片宣传期都要来一段“炮轰大众”,并且百发百中。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许知远背后的团队才选择了用出言不逊作为节目卖点,事后的传播效果证明这个方案行之有效。《十三邀》取得了如娱乐真人秀般的效果,许知远和嘉宾都从中获益,取得了爆炸级的曝光量,甚至超越了 pg one 和 Gai 互怼的关注度。
由此看来,在营销套路遍地皆是,文化消费无所不在的现状中,“打败许知远=大众打败精英”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无穷无尽的缠斗也不过是继续为文化工业添砖加瓦,让腾讯,节目组和相关人士在曝光度下涨粉赚钱而已。大众能否超越这一体系进行更深刻的讨论,真正创造价值观更多元、探讨更公开、话语更平权的世界,也许才是接下来值得关注的话题。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