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部通篇用油画拍摄的电影,
《至爱梵高 · 星空之谜》在朋友圈刷屏了。


无数文艺青年趋之若鹜,
顶礼膜拜心中的艺术偶像。
一个生前只卖出一幅作品,
靠弟弟供养的社会“loser”,
最终亲手了结自己短暂的生命。

他绝想不到在164年后今天,
他会成为全世界的超级“IP”,
这个人便是文森特·梵高。

这位穷困潦倒一生的艺术大师可能也想不到,
21世纪的今天无数人会以他为“生”,
博物馆、纪念品、复制油画……
而另一方面,
世人可能并不知道,
在荷兰梵高博物馆旁的纪念品店里售出的仿制油画,
大部分都来自中国深圳的一个偏远小乡村:大芬村。
【一】

大芬村本只是个穷困的客家小村落,
占地0.4平方公里,
原住村民300余人。
上世纪80年代村民仍靠种田为生。
但因杂草从生、污水遍地,
这里被俗称为“大粪村”。

但在1989年,
“大粪村”的命运被从此改写。
一个名叫黄江的香港画商因房租高涨,
带着20多位画师从黄贝岭移师大芬村,
从复制和出口西方的知名油画起步,
而就是这次偶然的机会,
使得大芬村成为了“中国油画第一村”。

大芬村距离深圳布吉镇只有三公里,
被两条交叉的主干道裹夹,
周围挤满了商铺、餐馆和旅舍。
马路边的建筑上挂着张巨幅海报:
“世界油画,中国大芬”。
而村口的巨型画板上则写着“大芬油画村”,
一座手执画笔的雕塑会让你误以为到了798。

村子里除了三条短街,
便是横纵分列的小巷,
到处都是绘画工作室和画廊。
沿着狭窄的街巷溜达,
不到2小时就能逛完整个村子。
很难想象,
在中国的这个偏远村庄。
会展现出另一种腔调的西方艺术。



而就是这样一个地方,
画出了全世界将近60%的油画。
每年生产和销售的油画达100多万张,
年出口创汇3000多万元。
大芬村用了20年的时间,
终于不再是那个贫瘠穷困的“大粪村”了。
【二】

一个小学文凭的农民,
半天时间可以画出一幅世界名画。
你可能会难以置信,
但这却是大芬村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

黄江最初收了几十个学生,
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
没有任何绘画基础,
艺术对他们来说很遥远,还有些神秘。
他从调色、用笔开始教,之后是临摹,
培训一到两个月就开始上手画了。
这些学生熟练以后,
有的叫上家人和老乡来一起学画,
有的后来还收了徒弟,继续传播。
到现在可能有六到七代画工,
形成了一个有几十万人的油画工业。

一幅名画通常几人分工完成,
每个人都只专职画其中一部分。
比如最受欢迎的《梵高自画像》,
由五人完成,眼睛由一人承包。
这种流水线模式使工人画得很熟练,
而一幅《梵高自画像》在职业画家手中,
至少要一天多的时间完成,
但在大芬村的画工手里,
一天可以画出十几幅。
而这样一幅“行画”,
售价通常只有几十块。

这里约有万名画工,
夜以继日地赶制着世界名画,
销往全国各地,全球各地,
而他们画的最多的就是梵高。

你可能也很难相信,
在阿姆斯特丹博物馆的广场中,
摆放在玻璃橱窗内的《向日葵》仿作,
同样出自这个偏僻村庄的画工之手。
【三】

在大芬的油画生产者们,
按照绘画水品的高低被分为:
画工、画师和画家,
这三类人呈金字塔形分布。
画家卖原创产品,
画工制作山寨名画。
无疑画工处于产业链的最底端。

他们被画廊雇佣或接受画商订单作画,
靠的是“走量”,
收购价常被压得很低。
经过层层倒手和漫长的运输后,
画作最终出现在国内各地和海外画廊中。

大芬村和众多艺术区一样,
艺术与财富的光环,
引得大江南北的谋生人群慕名而来。
为了艺术,也为了生存。

英国画家大卫在咖啡厅表演,
他在大芬村已经呆了近十年。

诗诗之前从事销售行业,
突然有一天她觉得,
自己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生活了,
便在大芬租了一个墙面,
一边画画一边卖服饰。

画家陈鸣婵正在自己的画室里作画,
她在四十岁实现了财务自由后才开始学画画,
不需要将画画当作生计,
她更愿意画自己喜欢的风格。

50岁的李红民从1991年开始,
就来到大芬村附近做画工,
见证了大芬油画村的完整发展历程。

来自梅州的朱新明是墙壁“画工”,
1996年,21岁的他跟着叔叔学画画。
每月靠卖订单画,收入低则七八千,多则两万多。
有时候他画不过来,就会找同行帮忙。

在这些“画家”中,
有的画了一辈子的梵高,
有的开始追求原创之路,
有的功成名就,也有的穷困潦倒;
有的深深地扎根于此,
有的则在一两年后随风飘散,漂泊天涯。
但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画,不断地画。
他们笔下,不仅是色彩和颜料,
更浓缩了时代发展的印记。
【四】

无可否认的是,
大芬村里仍生活着大量最底层的画工,
他们曾经是画厂里没日没夜干活的工蚁,
用一幅幅复制油画换取微薄的薪水。

但随着大芬村行业的聚集和饱和,
随着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
画厂模式在大芬村注逐渐被淘汰,
流水线模式在带来高速和低价的同时,
也让大芬村一度被贴上了“山寨”、“低廉”的标签。

为了留住和扶持原创画家,
大芬村“软硬兼施”:
为画家、画工兴建公共租赁住房;
建成全国首个美术产业园区配套美术馆,
携手中国美协每年举办油画展,
定期组织原创画家外出采风,
……
这个曾经的高仿村正在拼命改变,
而底层画工们的命运,
也将被时代的巨手频频改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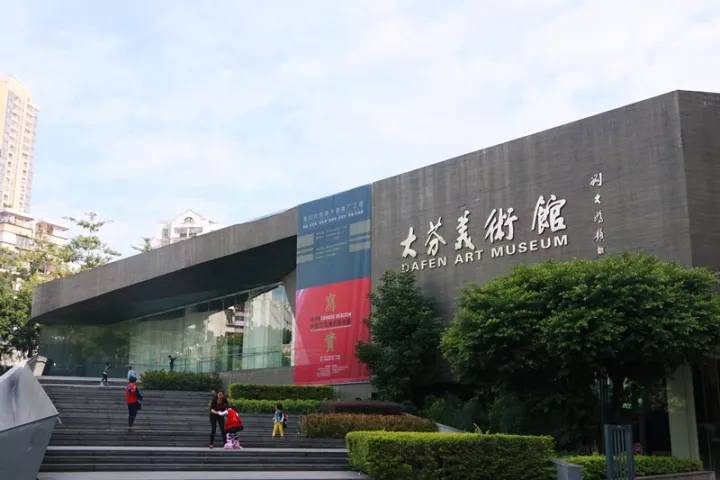
在大芬村,“艺术”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作为生存工具的“艺术”,
是日夜重复的笔触和相似的构图;
另一种则是作为爱好和追求的“艺术”,
奢侈而脆弱,需要艰难供养才不至于失去。

在狭窄的巷道中,
在弥漫颜料气味的画室里,
即便是色彩艳丽的油画,
也填充不了贫瘠的生活。

▲图:@春月
于是“中国梵高”们在眼前的画布上,
又添上了一笔。
每一笔,都离艺术更近,
却又很远。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