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对读者而言,读书是一件个人甚至私密的事,但无论是写作还是出版,要面对的不是单个的读者,而是某个读者群体(读者层),可见其重要性。然而书之社会存在的三要素——作者、出版者、读者中,处于出版过程或文学过程末端的读者在很长时间里并没有进入文学研究者的视野。
日本学者前田爱在著作《从音读到默读》中写道:“在现代,一般都认为小说是一个人默读的,他人不参与其间,但偶尔会遇见年迈老人用一种奇怪的抑扬顿挫音读报纸的情景,不禁让人料想这种默读的读书习惯普遍化为时尚浅,不过才两代、三代吧。试从日记、回忆录之类资料中探求一下明治时代的读者状态,就会惊讶于那时人们还依恋着音读的享受方式,其根深蒂固超乎我们的想像。”以这种从音读到默读的角度观察读者十分有趣,这既是一位读者从孩童到成人的阅读方式的转变,也是人类读书形态史的一个缩影。
读书——人类所独具的文明行为,也具有历史性,而“从音读到默读”是读者形态的最大变化,不但汉字文化圈,整个世界的读书史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从音读到默读》
最近,筑摩书房出齐了《前田爱著作集》,六卷,开本比大三十二还大些,每卷五百页上下,书脊厚厚的,装帧淡雅,摆在书架上煞是好看,诱人取下来一读为快。于是,从中读到《从音读到默读》一文,副题是《近代读者的形成》。
此文最初发表于一九六二年六月号《国语与国文学》杂志,一九七三年与其他论文合编为《近代读者的形成》,由有精堂刊行。二十多年过去,新闻学教授山本武利为《前田爱著作集 第二卷近代读者的形成》作解说,断言这部论著仍旧是最高水平的:“读者研究从来都不过是文学研究的副产品,以读者研究本身为目的的著书在日本还不曾有过。《近代读者的形成》,如题目所示,是日本第一本揭出读者研究旗号的著作。岂但是第一本书,而且时至今日,犹未被后来的研究者超越。”

日本的文学研究者意识到读者问题,举为研究领域之一,肇始于一九五〇年代后半。按照前田爱的看法,外山滋比古一九六一年发表的《修辞余像》应算是正规读者论的嚆矢。外山滋比古是英国文学教授,另著有《近代读者论》(三条书房一九六九年刊),在该书后记他述及当时读者研究状况:“文学上的读者论方法或读者的研究,在我国几乎是无所关心,在海外也不过才对其苗头略为注意,虽然还处于这种阶段,但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变化正日趋要求确立读者论方法。”以往的文学研究,对于出版问题、活字问题、读者问题是极其冷淡的,然而,要把握文学的社会基础,非研究读者不可。以读者研究为媒介,才能把微观的文学与宏观的社会置于同一次元来论证。尤其探究近代文学的形成时,更必须重视这些文学的外部“制度”。前田爱就是在研究近世后期通俗文学(所谓戏作)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触及读者和出版的问题,从萨特的《何谓文学》、里斯曼(Riesman,David)的《孤独的群众》、艾斯卡尔比(Escarpit,Robert)的《文学社会学》等论著得到启示,借助于利维斯(Leavis)等人的方法论,营构了他的第一篇纯粹的读者论《从音读到默读》。
以此文为先导,进而又撰写一系列论文,试图从三个位相——作者的读者意识、出版机构的构造、读者的享受相,立体地突现读者层的实态。前田爱的读者论内涵媒体论、传播论、文化身体论等,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探究实在的读者层和读者意识,另一方面在“文”的表现中捕捉那个时代的“社会”。他广征博采,从当时的作品、日记、回忆、书信、自传及报纸杂志等大量资料中索隐钩沈,力图再现近代文学读者的生态与风貌。有人说日本学者搞研究常常抓小题目,重视实证,含含糊糊地尽可能不下论断(如《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武安隆、熊达云著,六兴出版一九八九年刊),这种现象可能是出自日本人的性格,而前田爱正是凭不厌其烦的实证作业名噪一时,使日本的文学研究进一步从思想性裁断和观念论美学脱出,他的读者论也得以保持其价值,不因时势推移而湮没。


《从音读到默读》是前田爱读者研究的代表作。他说:“在现代,一般都认为小说是一个人默读的,他人不参与其间,但偶尔会遇见年迈老人用一种奇怪的抑扬顿挫音读报纸的情景,不禁让人料想这种默读的读书习惯普遍化为时尚浅,不过才两代、三代吧。试从日记、回忆录之类资料中探求一下明治时代的读者状态,就会惊讶于那时人们还依恋着音读的享受方式,其根深蒂固超乎我们的想像。”这让人蓦地想起鲁迅的三味书屋——
先生在书房里“大声道:‘读书!’于是大家放开喉咙读一阵书,真是人声鼎沸。有念‘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的,有念‘笑人齿缺曰狗窦大开’的,有念‘上九潜龙勿用’的,有念‘厥土下上上错厥贡苞茅橘柚’的……。先生自己也念书。后来,我们的声音便低下去,静下去了,只有他还大声朗读着:‘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
读书——人类所独具的文明行为,也具有历史性,而“从音读到默读”是读者形态的最大变化,不但汉字文化圈,整个世界的读书史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与前田爱发表《从音读到默读》同年,加拿大社会学家麦克卢汉(Mcluhan,Herbert Marshall)出版《谷登堡的银河系——活字人的形成》,也说到“古代和中世的阅读全是以音读进行的,伴随印刷文化,眼睛加快了速度,声音被迫沉默了”。英雄所见略同,是因为他们都受惠于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的著作,不过,二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对象各走一路,前田爱寻究的是明治初期新的文学读者的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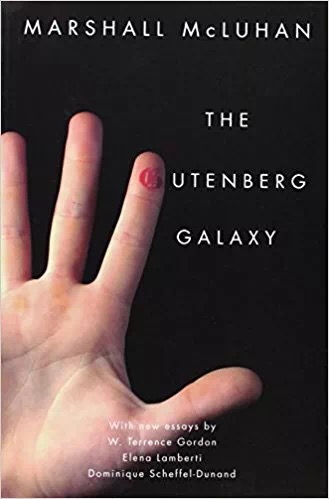
里斯曼曾试图从与清教主义的关联上探讨默读习惯的成因,说过:“其实,甚至在谷登堡出现以后,到现代的读者方式普遍化仍花费了漫长时间。书籍即便是独自读,也出声地朗读;自己随便按发音拼写文字(直到约翰逊博士的辞书统一了正字法)也显示了这一点。把印刷的行倾斜,头像梭子似地迅速转动,默默地、不显山露水地、私下地阅读,学习这种读法的——这的确像他们——是清教徒。这种时代较晚才开始的印刷的书籍像外向之门一样打开了内向之门,把人从他人存在的喧骚引向孤独。”
公元三五四至四三〇年在世的奥古斯蒂努斯(Aurelius Augustinus,即奥古斯丁)的著作《自白》(现通译《忏悔录》)中有这样的描写:“他读书时,眼睛在纸面上驱驰,心里捉摸着意思,但不出声,舌头也不动。”可见那时已经发生了默读现象,但一般习惯是读出声来,默读要令人少见多怪的。有欧洲学者主张,默读首先兴起于古代后期的基督教界,七世纪至十一世纪在不列颠岛的,随后在大陆的修道院抄写室传开,十三世纪波及大学和经院学者们,一个半世纪以后在世俗的贵族阶级中间普及。实际上,直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最普通的民众仍离不开音读。
音读是书面文字从口头语言发展而来的原始现象。声音转换为文字,但习惯于听说的人们还需要读出声,把文字再变回声音,借助耳听来理解意思。尤其是书面未显示说话时的间歇,更障碍理解,使读难以无声化。罗马时代的文书字面是连成一气的,在英吉利、爱兰尔,八世纪出现单词断开书写的文献,默读普遍化才具备了前提条件。句逗原本是基于发声,而非句法。句逗成为一种技术,乃至即学问,使“读书人”乐得借以垄断知识,恐怕是口头语言与书面文字愈来愈脱节的结果。即使在读书方式已彻底演化为默读的今天,音读的残迹也随处可见,人们不是常常说文章“顺不顺口”么,据说作家们一时把握不住写得如何,也要“读读看”。孩子刚刚捧起书本时,一定要放开调门儿朗读,这正是从音读向默读的过渡,是人类读书形态史的缩影。
前田爱把“音读”分为两类,一类是“朗读”,作为传达手段或理解的补助手段,再一类是“朗诵”,是为体会文章的韵律而朗朗诵读。这里的“朗读”,主要指的是民众的阅读行为。明治初年“朗读”还普遍存在,如《山川均自传》所记:“每晚,父亲读得津津有味,母亲做着针线,姐姐织着东西,全家人一起听。”一人读众人听的读书方式乃基于民众的读写能力低下,并且与日本“家”的生活样式(缺少私生活天地)有关。当时的通俗小说等文学样式具有民众文娱的特性,正是与这种共同享受的形态相适应。那时小说还不是个人鉴赏之物,而是家族共有的教养食粮和娱乐对象,其读者层大大超出识字者的限界。在某种意义上,说书也可算是一种变相的读书(听书),是共同读书在市民阶层的社会化,商品化。
家庭共同读小说的享受形态,令人联想到五、六十年代全家人收听一台收音机消遣的情景,而现在晚饭后聚集一室收看一台电视是普遍现象。但小说的享受形态由共同向个人嬗变要缓慢得多,二者曾长期共存。小说逐渐封闭于一个人阅读的世界,除了它本身的演进与影响,也意味着家庭合作性与亲密感的式微。

“朗诵”是明治时代念汉籍的青年(所谓书生)们的特征,在学校、宿舍、政治结社等精神共同体内创造叙事诗般的享受场,大概是一种“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在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氛围。与之相应,文学样式是汉诗文、政治小说等。显然,这样的读书不同于隐遁的、孤独的读书,在酒馆、沙龙等集团性场所的朗诵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与纽带。日本近代化之初,汉诗文曾起过巨大作用,可以说默读的确立也伴随着对汉诗文的疏离。汉诗文铿锵上口,韵文不消说,甚至散文也本来是为诵读而写的。南宋杨与立幽居诗“柴门阒寂少人过,尽日观书口自哦”之句,活脱脱一幅“音读图”,中国读书人就这么自我陶醉了千百年,直至三味书屋的老塾师。日本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始实施新教育,但由于父兄之间尊重汉学之风犹盛,子弟放学之后往往还要在家庭或私塾学习汉籍。前田爱说,诵读汉籍这一学习课程,是通过反复放声念语言的音响与韵律,将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精神语言——汉语的形式刻印在幼小的心灵上。虽然不理解意思,文章的音响与韵律却几乎能从生理上领会。这种诵读训练出来的青年们,具备大致等质的文章感觉和思考形式,就可能超越出生地、出身阶层的差异,沟通同属于精英者流的连带感情。而且,以对于汉语的音响与韵律的感受能力为前提,朗诵汉诗文的行为也具有增强这种连带感情的作用,恰如使用方言能强化生活在同一地域社会的人们的亲近感。
日本有一种文娱形式,叫“诗吟”,是朗诵汉诗文的遗风。“诗吟”常与“剑舞”相配,并伴以筝、十七弦、尺八等,听来颇令人发思古之幽情。英语学教授渡部升一曾说到:“有人以为中国人不像音读那样读汉诗很有点怪,但其实古时候的诗的朗咏法在中国早已经失传。王维的《辋川集》中有‘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这‘长啸’的意思一定是朗咏。在美国的大学,我曾与一位台湾来的老文学家同宿,请他演示一下长啸是什么样,可他答道:‘如今全都失传了,没人知道,也没法知道。’于是我写了一首李白的诗,用日本式的诗吟朗诵给他听。那一定是稀奇古怪的情景,在美国的大学宿舍里日本人给中国的中国文学教授吟唱李白的诗。既然长啸的传统在发源地中国已断绝,我们就只好把诗吟作为现存的长啸法了。”(《古语俗解》文艺春秋一九八三年刊)这里“长啸”是否“一定是朗咏”且不说,而关于音读诗文的方法,念过私塾的老人们大概还会依稀记得吧。
“在日本,活字以前的木版时代相当长,并不是从口承时代一下子就进入活字时代的。木版印刷虽然是印刷物,却大量残留着口承传统,印刷的语言能还原为肉声,实际是被出声地读。”(前田爱《近代文学与活字世界》)活版印刷术以前的木版整版印刷年代大体相当于音读时期,活版印刷与木版印刷交替的明治初年,印刷的文字还不能作为独立媒体充分发挥其机能,而兼带复制或再现口头传播之手段的作用。就是说,活字既作为个人的传播样式起作用,又常作为以家庭共同体、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等集团为单位的传播样式起作用。

随着活字印刷术的发达,“一篇文章忽地化作数万印刷物”(近代文学家坪内逍遥语),一个读者可以得到更多的书,一种书可以拥有更多的读者,“自个儿读自个儿的”,读书完全变成个人行为,读者对出版物的接触形态由音读彻底转变为内向的默读,近代读者因之形成。电影有观众,广播有听众,就抽象的概念来说,读者与观众、听众是一样的,但不缀以众字,好像也透露着读这种行为的孤独性。读书形态的转变,一方面影响到作者的文章感觉及作品构成,另一方面也促使读者的欣赏方式(享受相)由吟味抑扬顿挫的形式美移向形象的把握。就艺术表现的手法和特色来说,基于话本的古典小说宜“(音)听”不宜“(默)读”。骈四俪六的鉴赏角度在音读,“锦心绣口”,难怪默读的读者们往往要觉得言之无物了。汉字既有象形,也有摹声,所谓“义存乎声”,过去时代的人们读得“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想来也半是沉醉在汉字的音响所塑造的意象与境界里。尤其是那些拟声拟态辞语,对眼的愉悦确实远不如耳。明治时代老派读者对言文一致体抱有反感,理由之一是“韵律欠如”,音读不成了,“欲读嗟如钳在口”(苏轼《石鼓歌》),对此,言文一致运动倡导者山田美妙(一八六九——一九一〇)敦促读者们改变鉴赏方式,因为言文一致体小说不着想于音调,是需要用“通常谈话态”阅读的。
默读使读者与书籍建立了更自由、更亲密、完全内在的关系,可以不为书籍构成的复杂性或论述与注解、引文与诠释、正文与索引等关涉所拂乱,读得更快。而今情报化时代,出版物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图书的传达条件和接受条件进一步改观,默读更发展到“速读”阶段。
外山滋比古曾评介《近代读者的形成》,称道“从音读来探索近代读者的形成是前田爱的独创”,该书足以和英国利维斯等人的读者研究、美国的畅销书研究比肩。读书是孤独的,但无论文学还是出版,所面对的并不是个人的读者,而是读者层(群)。英国的读者层(Reading Public)研究起步于一九三〇年代,首先有文学史家克鲁斯认为读者的存在以某些形式反映在作家活动及文学作品中。不过,一旦着手对读者层的变迁进行实证性研究,立刻就撞上史料不足这堵壁垒;克鲁斯的研究以状况证据方面的史料为中心,尤重视读者接触印刷物的场。一九三二年,利维斯出版《小说与读者层》,以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理论性研究,几乎提起了所有读者层研究的问题原型。她从小说与读者层的关系着眼,论断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众读者的出现使小说即文学内容的质量降低。
一九五〇年以后,贝内特以读者层为基轴,实证地砌造出版史;韦布完全抛开历来的文学史角度,从传播史切入,尤为关注读写能力问题。瓦特关于十八世纪读者层成长与小说出现之关系的研究,在读者层是规定文学活动和内容的独立变数这一点上,与利维斯共识。阿尔蒂克把读者层视为整个社会背景的产物,从历史学家的视角把握读书在十九世纪社会的位置,即“大众读者层的社会史”。读者层的历史所蕴含的问题极其复杂,超乎技术性水平,在当权者眼里,读者问题不仅是文学的,而且是政治的;一九六一年威廉斯从理论上考察了这个课题。进入一九六〇年代,有关读写能力(Literacy)的研究成为主题目。读写能力是人成为读者的基本条件,是读者层形成的必要因素,与出版物的刊行数量等同样,是读者层推定、出版研究的重要线索。人的认识、思考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往往取决于读写能力,所以这方面的史料收集与研究,对读者与政治、社会之关系的分析是一个促进。克雷希的《读写能力与社会秩序》(一九八〇年)就是以教会法廷的宣誓证言书签名为基本资料,查考了都铎、斯图瓦特王朝时代英国的读与写。一九八二年,百科全书研究家丹顿发表《书的历史是什么》一文,试图打破欧洲、美国传统的出版史、印刷史、文艺社会学等框界,总结一九六〇年代以来有关“书”的各方面研究。他认为,这一研究领域发展显著,但综观全景,由于是从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思想史等各种“学”涉入,又任其自然成长,繁茂得好似热带雨林,令行旅(新的研究者)难以穿越。
一九六〇年代后半,读者研究在美国、德国也兴起,如美国批评家菲什通过具体作品分析读者对作品的反应过程,一反以往关于意味是作者创造的,或者先于读的行为而埋入作品当中的之类见解,认为经由一个个读者的读的行为中的“解释战略”才产生作品的意味。德国批评家扬斯用《挑衅的文学史》重新构筑以读者为轴的文学史,而伊萨的《行为的读书》从作品与读者的相互作用对读书行为做现象学分析,其重要观点是文学作品只有靠读者的参与才能填埋“空地”与“空白”。
前田爱(一九三二——一九八七)发表《从音读到默读》时年三十一,那时节接受美学全然不似今天这般发达,此论可谓“前无古人”,在日本的文学史研究和传播史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不过,他后来并没有就这一主题更深入下去,而是连连向别的主题挑战,致力于近、现代文学的记号论解读,以《都市空间中的文学》(一九八二年出版,获艺术选奖文部大臣赏、日本地名研究所国土研究赏)名世。“历史地考察读者层,这一作业所花费的时间与劳力数倍于固有的文学研究——作家论和作品论”,或许正因为如此,有关“从音读到默读”的研究似乎也“后无来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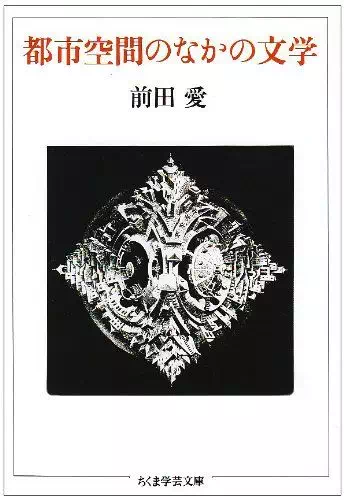
如果说近代读者研究的障碍在资料难觅,那么,相对而言,考察分析现代读者就容易多了,虽然显得少了点理论味儿。与文学史或文学理论领域的读者论、读者研究比较起来,出版读者论似乎偏重于现代。在现代寻找读者,不外乎两种方法,最正统的是向读者征询意见,再就是深入观察周围的少数读者,借以推测整个读者层的构造与状态。由前田爱、山田宗睦、尾崎秀树三位“教养主义隆盛时期成长的杂学派活字人”鼎谈而成的《现代读者考》(日本出版学校出版部一九八二年刊),就属于后一种读者分析方法的出色实践。据他们所考:“与其他时代相比,现代读者的状态最流动。乍一看混沌不清,其实是多样化、流动性的原故,因而也难以掌握”。年轻人生活在动用视觉、听觉、嗅觉等五感或六感的立体的感觉世界里,对于他们来说,以活字为中心的传播不过是极其狭隘的表现形式。新一代知识人读者不再是以往活字文化的教养主义式类型了。
书的社会存在取决于三种人的相互关系,即作者、出版者、读者,历来的视点似乎也循此顺序,把处于出版过程或文学过程末端的读者等而次之,只当作被动的存在。事实上,若无视读者(出版的消费者,文学的接受者),无论出版还是文学就必将不可收拾。当年筑摩书房之所以破了产,原因恐怕也在于倚仗是教养主义出版的老字号,不回应读者层的意识与变迁。对于有良知的出版,读者毕竟是爱护的,载舟覆舟,筑摩书房正是在读书界的支持下,一九九〇年终于复兴,这套《前田爱著作集》的出版也可以作为一个纪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