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统合的故事听起来常常像个枯燥的童话。曾受战争困扰的德国与法国早已开始寻求经济上的合作机制,以避免在未来发生冲突。两国在1950年代开始有了煤炭与钢铁的交换,这一经济交易渐渐地发展为贸易协定、边界开放与欧洲统一货币。这个故事里并没有多少人类能动性,有的只是一群官僚在会议桌前商谈地区经济发展与关税政策,他们深信,只要能为新的泛-欧洲认同构建出一套与之相匹配的经济与政治环境,那么社会现实便自然会朝这个方向演进。这群“戴高乐一代”的高级祭司不仅想建立一个能够自上而下发号施令的欧洲统合体系,并对那些基于反殖民原则重思边界的年轻一代政治积极分子抱持高度怀疑。欧盟达成了某种实用性的妥协:它在捍卫福利国家的同时反对社会主义,它在令欧洲大陆更加一体化的同时又试图拒斥来自诸多非欧洲国家的全盘性(full-on)全球化的冲击。
但眼下我们念念不忘的泛-欧洲文化并未在布鲁塞尔的会议室里取得什么进展,它是与欧洲诸国政府时常发生摩擦的一系列文化运动的产物。如理查德·伊文·乔布斯(Richard Ivan Jobs)在其新作《背包大使》(Backpack Ambassadors)里所表明的那样,共享的欧盟价值观高度依赖于搭便车、音乐节以及四处游荡的“68一代”青年积极分子。乔布斯对二战之后不久兴起的无计划旅行对集体性欧洲文化的塑造过程进行了考察,尤其关注环欧徒步旅行是如何成为西方中产阶级青年人的“成人仪式”。这一丰富的口述史当中所谈到的大部分旅行,均为无目的的长途跋涉,青年以此寻求人生体验,而战后欧洲人口流动性的增加也建立起了一种新的归属感,人们逐渐开始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比自己的出生国更大的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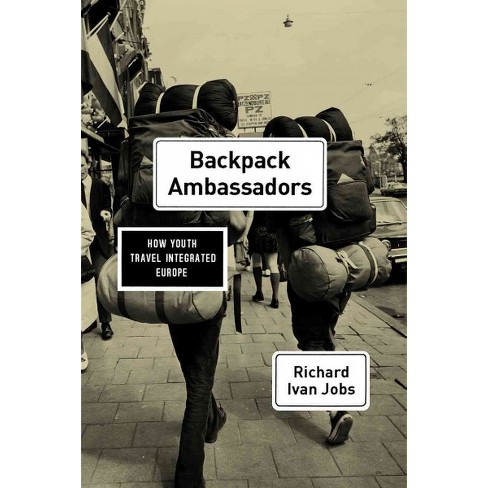
在此书开头,乔布斯以青年旅舍为例,考察了民族主义与旅游业的复杂关联。青旅最早兴起于20世纪早期的德国,后来迅速国际化,直到纳粹上台才告一段落(纳粹也鼓励青年人去参加登山俱乐部、野营和童子军,但这些项目都深受希特勒青年团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之影响)。二战结束后,青年旅社得以复兴,并带有明确的世界主义愿景,希望能够超越此前曾屡屡造成动荡的国界区隔、团结欧洲青年。一般来说,青年人会选择在夏天出行,前往青年劳动营做志愿者,接着会在青年旅舍或以沙发客的方式居住,以重建被战争破坏掉的团结纽带。这些劳动营的工作量不小并且基础设施很差,但参与者倒是很享受这种与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人同舟共济的体验(除开某些敌对倾向明显的国家),以此来反击其父辈一代的条件反射式的民族主义倾向。
不过,这些项目在冷战开始后很快就变得政治化。1951年的洛雷利节(Loreley Festival)在西德的莱茵河畔举办,一群青年人在一座原先由第三帝国兴建的露天圆形剧场内齐聚一堂,开展各种音乐活动,气氛欢乐而融洽。另一个成功的青年节日于1952年在东柏林举办。战后不久,徐徐升起的“铁幕”两侧都试图吸引东西两方的青年,但社会主义欧洲在流动性上的不足很快就令青年人的独立旅行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纯粹的西欧现象。
青年人横跨欧洲大陆的旅行开始吸引到公众关注,始于“泥土天使”(mud angels)的事迹,这些青年在1966年的佛罗伦萨特大洪水中抢救了许多无价的艺术珍宝。这些具有多国背景的志愿者比意大利政府的行动速度要更加快捷,他们乘坐火车涌入城市,迅即组织起人力,从受到泥水侵袭的博物馆里将画作与雕像运到了安全地带。颇有些讽刺的是,公众对这群拯救了国家遗产的青年人的赞赏来得有些不合时宜。那时公众——尤其是在较为保守的南欧地区——正愈发对披着长发的独立旅行者感到担忧,视这种临时起意的旅行为一种危险的到访形式。
事实上,意大利的国际旅行者数目是最少的,它与其它一些南欧国家类似,家庭纽带较强且可支配收入相对不高。先前,背包客在人们眼里本质上是一群从“现实世界”中撤出来喘口气的中产青年。这一点多年以来都是不争的事实:在战时成为英国特工之前,帕特里克·李·费尔默(Patrick Leigh Fermor)曾于1930年代周游欧洲,乔治·奥威尔亦曾于两次大战期间前往巴黎体验过一番底层生活,算是一场小有名气的“个人秀”。不过,受披头士和嬉皮士反叛情结影响的新一代旅行者更加公开地与社会相决裂,并告诉路上遇见的人们说自己绝无任何回归想法。

从1960年代开始,无计划无目标的环游欧洲之旅成为一种彰显中产阶级身份的固定仪式,它确证了某个人的经济地位,但同时又对其父母所坚持的资产阶级仪轨提出挑战。虽然欧洲人——尤其是那些来自更为富裕的多语种国家的人,如荷兰、瑞典与德国——相当喜爱背包旅行,但其环游欧洲的路径却大多是由美国人或澳大利亚人为他们规划的。某种意义上讲,局外人反而更有可能首先认可并接受这种同质化的青年文化:旅游在欧洲是富有创意的且与过去的国家间过节无甚关联。津津有味地享受夏季背包徒步旅行的,正是那些富裕的美国人。如同乔布斯所发现的:
“尽管美国学生相当习惯于中产的舒适居家环境,但他们仍然二话不说地接受了逼仄的居住条件、登山时复杂多变的环境、热啤酒以及不熟悉的食物。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漫长旅途中所需付出的必要代价。”
然而,这种不拘小节的自由在本地人眼里通常是不受欢迎的。许多国家设置了最低货币要求(亦即要求入境者必须兑换一定数额的本国货币——译注),在其它一些地方,反应要来得更具敌意,当地人企图强行剃掉嬉皮士背包客们那不无冒犯意味的长发,1968年在贝尔格莱德就发生了这种事情。
尽管背包客乍看之下像是身无分文的游荡者,但他们可是带着实打实的德国马克和美元前往希腊这类遥远去处的,这一点对那些胆子大到敢去东欧的背包客尤其重要,那些地方的居民极其需要外汇来协助其缓和经济上的短缺。部分城市甚至走得更远,专门把自己包装成了背包客文化的胜地。1966年,左翼无政府主义运动(Provo movement)开始在阿姆斯特丹迅猛发展起来,各种占领活动层出不穷,吸引了大量青年。但荷兰却并不打算驱散大量涌入的移民,其旅游业更是抓住机会大做文章,推出了“邂逅无政府主义运动”(Meet the Provos!)四日游套餐,路线与一般的度假旅程类似,但加上了与运动成员在艾瑟尔湖(IJseelmeer)泛舟的活动。当阿姆斯特丹被睡在广场的嬉皮士“攻破”的时候,这个国家并没阻止寻求冒险的青年人露宿街头,反倒允许他们去冯德公园(Vondelpark)落脚并为其筑起了大面积的背包客营地。

1968年,这一新兴的宽容政策遇上了真正的挑战,青年政治积极分子们纷纷想要在第一时间前往巴黎瞻仰一番。许多人受到了粗暴对待,尤其是丹尼尔·孔-邦迪(Daniel Cohn-Bendit,德国政治家,目前在欧洲议会任职,曾是“68风暴”当中的风云人物——译注),乔布斯详细叙述了他的经历:各国政治领导人担心青年的反叛会产生不良影响,孔-邦迪屡遭各国拘留和驱逐出境。不过,大部分旅行者并没有鼓动群众运动的想法,只想当个观察者而已——在巴黎,他们看到了1789年大革命精神的重生,在布拉格,青年人群起而反对审查和苏联的高压手段(后来因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中断)。在苏联入侵之前,《纽约时报》曾不无兴奋地评论称:“如果你还没满30岁,那布拉格就是你今年夏天的去处了。”
乔布斯的书以一场戏剧性的、略显忙乱的火车之旅为线索而渐次展开,尽管中途多有停靠,但却从未迷失方向,它展示出背包客的反文化如何促进了泛-欧洲认同的形成以及如何无可逆转地改变了全球旅游业的格局。富有的北欧人前往物价低廉的南欧旅行所造就的流动状态,目前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早在1970年代,背包客就曾乘坐过跨国巴士前往喀布尔,并在伊斯坦布尔、马拉喀什和加德满都等地建起了背包客专属区域。事实上,随着欧洲统合计划的成功以及南北欧经济差距的缓和,地中海旅游对想要追求极简生活的人而言就没什么吸引力了。此外,随着欧洲文化越来越同质化,许多青年为了体会一番异国风情,也开始倾向于前往泰国、南美和印度等地。
乔布斯不无谨慎地表明,背包客只是战后发生巨变的流动性的一种表现而已。富裕国家的青年人跑到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去探险,而这些国家的移民则顺着相反的方向前往德国、英国与北欧谋生,有时则会定居在那里。这一趋势很快超越了地区性运动的限制,彻底地全球化了。不过,背包客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了自己作为访问者——而非接待者——所享有的各种特权,仍然是不甚明确的。乔布斯发现,旅游愈发地热门起来,成为彰显文化地位的活动以及发达国家各阶级都享有的权益:“在战后的西欧……大众休闲与个人流动性被誉为促进民主化的力量,它为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赋权,刺激经济发展,鼓励国家间的交流……休闲性的流动从渴望变成了预期。不过,随着旅游变得更加普及化,也有观点怀疑旅客出行时是否还能一如既往地保有探索未知、体验新处所的冲动,怀疑旅游是否沦为了某种例行公事的、与买车和上大学无甚区别的中产阶级成人仪式。”
尽管背包客相当赞成欧盟的边界开放政策,但这不等于对欧盟本身的赞美。乔布斯对此有精当的分析:
“透过往来频繁的旅行及人际互动,这些旅欧背包客主动地推进了欧洲诸国边界的自愿性民主化,尽管其路径也并未与欧洲联邦计划(federalist European project)合流。”
不过,在增强欧洲性(Europeanness)的过程中,许多心系泛-欧洲文化的人——包括背包客在内——却动摇了令他们得以享有开放边界的一系列制度与政治的机制。许多享受跨欧洲大陆背包旅行的、借助伊拉斯谟奖学金出国读书的、在超市里购买免关税外国产品的人仍然投票支持了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Five Star Movement)、英国的独立党(UKIP)或丹麦人民党(Danish People's Party)——而这些都是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新兴政党。
关于欧洲不可逾越的高墙及边界的文化记忆正在消退。马其诺防线已经开放了60多年、柏林墙在大约30年前也在一片欢欣鼓舞中被击碎和铲平了。如今,在诸如布达佩斯的凯莱蒂火车站(Keleti Station)这样的欧洲大陆中转站,时常会有一群仔细研读欧洲铁路全图的青年背包客,叙利亚和阿富汗的难民也这样做,但他们的目的则是找到一个重新开始新生活的去处。尽管欧洲人视旅行为理所当然,且受惠于欧盟法律的优点及其含金量颇高的护照,得以在世界各地自由往来,但欧洲大陆的外部边界却正在固化,进而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一群人通过冒险找乐子、背包里各种物资一应俱全,另一群人则在恐惧中流亡、背包里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洛杉矶书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