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并不能坦然面对死亡。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听到的话总是:你要遮掩自己的悲伤,要向前看。虽然教堂、墓园这样制度化的公共空间给我们的悲伤提供了一个出口,能够短暂地发泄自己的情绪。但在转身离开的时候,我们的生活还是得回到正轨,一如往常。美国人和死亡的关系用科恩兄弟1998年的《谋杀绿脚趾》的最后一幕就可大致概括:两个老友精简了悼词,匆匆了事便去打保龄球了。今天,我们站在一个青黄不接的节点,对待死亡的传统方式已经瓦解,新的一套惯例还未建立起来。
大卫·查尔斯·斯隆(David Charles Sloane)的新书《墓地已死?》(Is the Cemetery Dead?)审视了我们不断进化更迭的哀悼形式,特别是我们与墓地的关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斯隆总会“把尸体摆到人们面前”。这次,他把焦点放在了死亡之上。在我们的文化中,对这个话题的关注度远远不够,而且许多人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眼不见心不烦。斯隆以追忆亡妻开篇,引入了全书内容。从他痛苦的挣扎,到学会接受现实,到选择“安息之地”(这个词本身就掩饰了我们对这种地方本身功能的抗拒和不安),斯隆列出了一长串致敬名单,从墓地管理者到教堂司事,足以看出这一系列工程内容丰富而复杂。另外,有了在父亲看管的墓园内的成长经历相辅,他对死亡的研究更添了许多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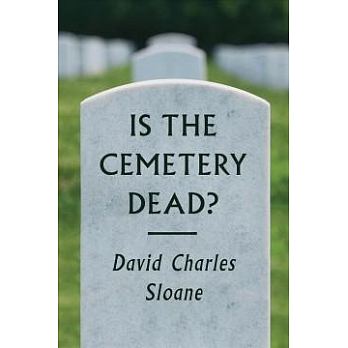
斯隆在书中写到,一直以来,墓地在美国、加拿大人眼里都是公共空间的代表。在十八世纪和更早的时候,死者都被直接埋葬在教堂周围的墓地里。这些密密匝匝的坟墓毫无美观可言,有时候尸体甚至被堆叠在一起。纽约的三一教堂历经岁月捶打,屹立不倒,坐落在摩天大楼的包围之中,虽然也有一些古老墓地像它一样持久至今,但更多坟墓早已物是人非。似乎所谓“永恒”的承诺比我们想象中有弹性得多,而那些有色人种的尸体尤为如此:非裔美国人和原住民的尸体遭受了各式各样的蹂躏、搬移和破坏。在类似曼哈顿、旧金山这样很吃香的城区,市里的墓园里是没有他们一席之地的。
19世纪初,美国人开始重新思考逝者的埋葬方式。人们借由“改革”墓地的契机,建立了美国第一批总体规划空间,从合理化、网格化措施(有时候还把现存的街道网络放到缩略模型里)到英国景观园艺启发下的“田园空间”。这些墓园分布在城市边缘(此后就被归入城市范围内了),它们有公园般的休闲娱乐空间,用一种理想的方式,将逐渐远离树木和绿荫的城市居民带回自然的怀抱。
城市不断扩张,公共空间却依旧匮乏,类似波士顿郊外的奥本山墓园和纽约布鲁克林的绿荫(Green-Wood)墓园这样的地方就发挥了不小的社会作用。它们打一开始,就几乎是按照景点来设计的,墓园里处处都是蜿蜒曲径、山丘池塘。城郊的这些墓园变成了大家眼中的宠儿,登上了周末度假、漫步的情人和游客的必去清单。在十九世纪中期,每一年,有轨电车都要将约摸五十万参观者送往绿荫墓园,在美国,它成了继尼亚加拉大瀑布之外第二受欢迎的旅游景点。然而,这些游客常常会因为在墓地内抽烟、野餐、和爱人勾勾搭搭或者践踏花草而破坏了墓园的规则。参观者在这种用来反思和追忆的场合,做出了不守规矩的行为,未免令人讨厌,美国媒体也展开了激烈讨论,从而挖掘出新需求,推动建立新的对公众开放的公园。在纽约,中央公园和展望公园在几年后相继建成开放。
生活富裕的都市人竟然喜欢在故去的挚爱坟前野餐,这听起来可能很荒谬,但在维多利亚时代,死亡其实是生活的一部分。十九世纪30年代,美国城市的婴儿死亡率接近50%,许多家庭都会在客厅显眼的位置摆上几个“玻璃柜”,剪下夭折孩子的一撮头发,锁进柜子里。同时,人们还会带着新结成的姻亲,来到自家墓园,和“其他”亲戚见一面。小山丘爬满青苔,哥特式的铃木上雕刻着天使的模样,这些宏伟的郊区墓园风格令人感伤,也塑造了我们今天对墓地的印象——令人毛骨悚然(《史酷比》里的坟墓就是一个例子)。然而,到了今天,大多数人被埋进了另一种墓园,被人们称作“纪念公墓”。

到二十世纪早期,几乎所有墓地都成了公墓,在一大片草地上,一个个坟墓被集中在在最小面积的土地上,竖起纪念碑。最早在城市公园、墓地中出现的草坪或是未经修剪的草皮,很快就扩散到那些没什么人烟的庭院里,成为郊区的标志。公墓里那些坟墓规规整整,横平竖直地排列着,营造了一种干净齐整的视觉空间(同样也让割草机能畅通无阻)。这些纪念公墓出现的时机恰好——医学的发展延长了人们的寿命,儿童死亡率也大幅下降,看护病人或垂死老人的工作被转移到单独隔离出来的专业疗养机构,死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戏份变得越来越少。然而,即便斯隆在叙述中一直保持温和,他还是严厉批评纪念公墓是人们在那些“因文化元素被建构和约束的空间”里“努力追求一致”的缩影,这种趋势主导了整个二十世纪上半叶。战后高速公路网疯狂延伸,不断扩张的郊区也挑战了郊区墓地存在的合理性。一些老旧的墓园卡在日趋衰落的近郊,位置尴尬,另一方面,人们住得也越来越分散了。

墓园是一种故乡的“根”的象征,但这种根的意识变得越来越陌生:人们在好几个城市之间辗转,家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要选定一个死后委身之地越来越难。很多人都逐渐认清了现实,于是选择将尸体火化,并且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处理骨灰——虽然这往往意味着像以前一样把骨灰埋在传统坟墓中。如今,美国很大一部分(48%)死者死后都接受了火化,比土葬的比例(46%)还要高,在未来几年里,这个数字预计还会有显著增长。20年前,当《谋杀绿脚趾》里沃尔特将多尼的骨灰洒进太平洋的一幕上映时,火化依然是一种另类行为——虽然1960年代天主教已经解除了对火化尸体的禁令,纳粹在种族屠杀中也焚烧过尸体。在那以后,火化逐渐成为一种常态,也给墓地带来了麻烦。
现代的环保运动指责公墓是对资源的大量浪费。墓地占用了大量肥沃草坪,标准的葬礼过程也带来了一定污染。殡葬行业每年要消耗超过302万升防腐液体(其中含有大量甲醛);制作棺材则要耗费超过3000万板英尺的硬木,为此要砍掉近10万棵成年树木。现代墓地有钢筋混凝土材质的墓坑,一个个筒仓大小的桶装着满满的除草剂,还有耗水巨大的喷灌系统。用斯隆的话说,它们已经变成了一种“复杂的工业景观”。墓地的拜访者少了,维护墓地的成本却成倍增长,不论是金钱还是环境意义上,代价都不断提高。真是讽刺啊,美国这些中产阶级即使在死后也还在破坏环境。
面对这种“美国人的死亡方式”,一些抗议者掀起了一波新的倡议,反对个性化的殡葬活动,连墓地也一并抵制了。其中有一些倡议是植根于激进环保主义土壤中的,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发源于英国的的“自然埋葬”运动。“自然埋葬”运动最初受到原住民仪式和管家工作的启发,延伸了“自然出生”运动和临终关怀的概念,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们对待摇篮到坟墓的态度。在这些墓园里,花在葬礼上的钱可以用来保护森林;尸体被简简单单用裹尸布抱起来,或者放在质朴的木棺里;简单的本地石碑也代替了华丽雕饰的石碑。这一策略对岌岌可危的林地效果最为显著,因为在那里,正是墓园的存在,才保住了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
斯隆在书中写到,疾病和其他的传统健康杀手已经几乎被人类解决了,但谋杀、自尽、性暴力、车祸和其他带来创伤的死亡方式,每年依旧会夺取近20万人的生命,他们中许多人还很年轻。惊人的是,(在美国)每天平均有7个人被枪支夺取性命,类似这样意外结束生命的年轻人之死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需要一种特别的纪念方式。在一些饱受枪支暴力侵扰的低收入居民聚居区,墙壁上到处都是“R.I.P.”。
二十世纪中叶,路边开始出现十字架,在一些车祸多发地段,十字架甚至多得“像是一座小型坟墓”,造成了安全隐患。直到工程师担心这些小型纪念墓碑会扰乱交通,带来安全问题,他们设法建立起新的洲际公路系统,这些十字架才逐渐被遗忘。后来,在一些洲际公路的十字路口,人们会摆放着一些白色自行车,这些“幽灵自行车”是用来纪念被撞死的自行车手的。通常,它们是由那些和死者关系不那么亲密的人放置的,与其说它们的作用是纪念,倒不如说是为了提醒注意。墓地不可能囊括形形色色的公众哀悼活动,当今,恐怖主义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暴力时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甚于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在公众场合,随时都可能看到悼念活动。
正如斯隆所说,今天的墓园也不好过。绿荫这样的郊区墓园能够保持发展势头,也许是因为它声名大噪,它的地理位置也不容忽视(不管怎样,它都是属于纽约的地产),但其他许多墓园难以平衡盈亏。许多墓地正在想方设法转型成有意义的历史遗址、绿地空间或者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对周围的居民和死者家属也不能失掉尊重。绝大多数墓园都选择明哲保身,谨慎行事,但有一个例外——洛杉矶的好莱坞永恒公墓在1990年代晚期整修一新,而今的业务包括举办喜剧之夜、在改造过的共济会小屋里开办摇滚演唱会,还有举办露天电影放映活动。许多墓园现在也承接火葬业务,有些墓园会让自己的环境“重新变得像野外”,以适应自然埋葬的需求。这些变化让人不禁好奇,墓园会不会转了一圈回到原点,变成奥姆斯特德设计的公园的样子,而这些公园最初的灵感来源,正是墓地。

而今,社会上又涌现了一些新的殡葬方式,简直是古怪的科技乌托邦。一些公司提供服务,能将骨灰压缩到钻石里,让死者的家人把他们挚爱的骨灰作为吊坠或是戒指“穿戴”在身上(一个人身上的碳元素就能制造好几颗钻石)。与此同时,目前火化尸体的主流做法对环境会有什么影响,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最近一项联合国调查发现,火化尸体的牙齿时会释放出汞,如果这些有毒物质不能被很好控制,很可能会成为“大气污染的相对重要来源”。因此,火化过程优化了过滤设备,一些墓园也放弃了火葬,转而采用更环保的方式进行葬礼。火葬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也大得惊人,有人提议说,火化的余热可以用来给地区供热,不过人们对这种热源的不安还是挥之不去。还有些人提出了“生物殡葬”——又称作“水葬”——用强碱和高压让人的血肉剥离,只剩骨头和一种“可以直接倒入下水道的”无菌液体,死者的骨头还能归还给亲属。超过10个州都将这个方式纳入法律允许范围内,但一些宗教和其他保守主义的声音也源源不绝,抗议“把祖母冲进下水道”这件可怕的事情。
还有一些新的构想,用“设计思维”创造性地重新描绘了死亡。设计师李琳佳(Jae Rhim Lee)和迈克·马(Mike Ma)通过一段点击量超高的TED演讲,介绍了他们的“无限量寿衣”。这件衣服介乎日本的忍者服和伍迪·艾伦执导的《性爱宝典》里的精子衣之间,由蘑菇的孢子缝制成,能够祛除尸体的毒性,从而“减少下葬后对环境的影响”。卡特里娜·斯佩德(Katrina Spade)也提出了“重组计划”,设计出一个别致玻璃结构组成的网络,从尸体的表层深入到核心部分,让它成为“营养丰富的堆肥”。这些新方法既是艺术,也是一种商业——李琳佳和迈克的蘑菇寿衣已经投入市场,价格1500美元,毫无疑问,它们的吸引力之一,就在于能够激起社会的争论。这些项目也让人们看到了死亡、哀悼和最重要的——尘归尘,土归土——三者之间的一种新的关系。
但斯隆并非只是在这个行业的专业边缘浅尝辄止,而是一遍遍和传统墓地的负责人打交道。他没有给读者讲述过多稀奇古怪的来世故事,没有过多文学描述,也没有对墓地里未经许可的文化庆典活动作过多记录,而是给我们呈上了死亡护理行业的一份冷静的报告。他的文字很有价值,因为在墓地里试点进行的空间规划,在我们生者的世界里也总是能得到呼应。通过墓地的建筑和景观,我们能一窥人类与大自然不断变化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的的亲朋挚爱总会一个接一个离开我们,而我们这些还活在世上的人,有义务选择一种合适的方式,给他们尊重,让他们安息。
本文作者Sam Holleran是一名作家、跨学科画家、艺术家。他对图形文化、城市化和建筑的研究收录在著作《异见、印刷和公共图书》(Dissent,Print,Public Books)、《艾弗里评论》(The Avery Review)中。
(翻译:马昕)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洛杉矶书评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