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不仅参与了历史,也创造了历史。谈到法西斯主义复苏时,她的语气就好像自己在独裁时代生活过一样。1939年,纳粹吞并捷克斯洛伐克,还是小孩的奥尔布赖特和家人一起逃离了家乡。经过10天的躲藏,她的父母离开布拉格前往英国,并在诺丁山门(Notting Hill Gate)“高级起来之前”找到了落脚地——位于波特贝罗路(Portobello road)的一处公寓。奥尔布赖特对伦敦最早的记忆是感到迷惑。“我什么都不清楚,我父母是典型的欧洲大陆人,我那时候也还没有弟弟妹妹。我很孤独。”当希特勒开始发动闪电战,“每天晚上我们都住在地窖里,大家都在那里睡觉。”
后来,她也曾经回过诺丁山的旧居。“我按了门铃,现在仍有人住在那栋公寓里。公寓比我记忆中小了很多。我愚蠢地问他们地窖是否还存在。他们回答:‘地窖当然还在。’他们带我下去,我看到那幅绿色的画还在,我一直记得那幅绿色的画。”
尽管她从小就是天主教徒,但几十年,她才发现父母是犹太人出身,她的许多亲人在大屠杀中丧生,包括三位祖父母。
奥尔布赖特一家从伦敦中心的诺丁山搬到泰晤士河畔沃尔顿镇(Walton-on-Thames),与“其他几位捷克人一起合租”。这里也会有炸弹落下,不过她仍然喜欢这部分童年的“每一分钟”。“我去上学,我们在防空洞里唱儿歌《十个绿瓶子》(A Hundred Green Bottles Hanging on the Wall)。”当时并没有那么可怕,因为“我的父母能让不正常变得正常”。
她成为了一名“电影明星”。红十字想要拍一部关于难民儿童的电影。“我就是那个难民儿童,他们送了我一只粉色的兔子作为报酬。”
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战时的英国是“非常好客的”。“英国人会说:‘你们的国家被独裁者占领,我们对此感到抱歉。欢迎你们来到英国。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们?你们什么时候回家?’”

奥尔布赖特的父亲约瑟夫‧考贝尔(Josef Korbel)是一位外交官,当时为捷克流亡政府工作。她回忆道,父亲那时候拒绝去避难所躲避炸弹,因为他要为BBC写完一则广播。希特勒失败后,考贝尔带着家人回到家乡,寄希望于捷克斯洛伐克能够重建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但没过多久,1948年,由苏联支持的政变者在这里建立了共产主义卫星政权,考贝尔带着一家人再次离开,这一次他们在美国寻求到了政治庇护,并定居科罗拉多州。马德琳·奥尔布赖特被同学们称为“马迪”,这时她11岁。美国人欢迎移民时会说:“你们的国家被糟糕的政权占领,我们对此感到抱歉。欢迎你们来到美国。我们能做什么来帮助你们?你们什么时候能正式成为美国公民?”她停顿了一下,然后说:“那时的美国是不一样的。”
奥尔布赖特作为担任记者和外交政策学者的经历,让她对政治产生了兴趣。1978年,吉米·卡特在任总统,奥尔布赖特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员。后来,奥尔布赖特担任了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1997年,比尔·克林顿指派她为国务卿,根据美国宪法,这是非美国出生的公民能够担任的最高政府职务。她是美国外交部第一位女性领导人。

图片来源:The Life Picture Collection/Getty Images
在担任美国外交官的四十年间,她的生活和观念再一次被暴政的概念所改变。她曾与朝鲜前最高领导人金正日见面,并在自己的新书中回忆道,他是一个诚恳、彬彬有礼的人,“他父亲的诞辰是朝鲜的纪念日,而他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塞尔维亚斯前总统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并不符合法西斯恶魔的刻板印象”,他喜欢“假装无辜”,即使他的部队试图对科索沃进行伦理大清洗。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非常有魅力”,当他排挤走“一群疲劳的精英主义老男人后”,最开始似乎打算遵守对国家的承诺。当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刚开始在土耳其掌权时,给人民带来了新鲜的改变,因为人们以前总被“住在大豪宅或者军队出身的”人统治。“这些领导人一开始确实会同情工人阶级,直到他们体会到权力的滋味。每个人都一样。”
奥尔布赖特新书中有一章关于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她评价普京“非常冷漠,就像是两栖动物”,但他也非常有能力,黑暗的能力。“他很聪明,打得一手好牌。他开始把中欧、东欧与西欧逐渐分裂,大目标是把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分裂开来。”
之后她才开始接受,西方并没能准确理解俄国在冷战中收到的屈辱,也没意识到俄国已经准备让一位民族主义伟人带领国家变得更强大。她回忆一位俄国人的抱怨:“我们曾经是超级大国,而现在只是有导弹的孟加拉国罢了。”她告诉我,“普京自认为就是那个伟人,那个救世主。”
我问她,与独裁者的直接接触是否让她能够总结出这些人的共同点。她笑着说:“我的答案可能会让你觉得意外。我和他们见面的时候,他们和平常都不太一样。”她讲了匈牙利总理——一位非自由民主制支持者——维克多·欧尔班(Viktor Orbán)的例子。“他是人人都喜欢的异见者。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出资供他去牛津念书。他创立了匈牙利青民盟(Fidesz)。当他年岁渐长,青民盟的年龄限制也逐渐放宽。”她用标志性的尖细声音回答。欧尔班·维克多在政府中的变化也让她感到震惊。“我没想到,我觉得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就是奥尔布赖特新书《法西斯主义:警告》(Fascism: A Warning)的主题。这本书呼唤我们注意全球集权主义的复苏,也惋惜自由国际主义政治的衰退。奥尔布赖特的父亲曾著书讨论暴政的危险,并指出美国人已经习惯了自由。“他们非常非常自由。”他写道,以至于美国人把民主视为一种理所应当之物。奥尔布赖特的这本新书也是对父亲的致敬。她引用作家、化学家普里莫·莱维的名言:“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法西斯主义”,并通过对独裁统治者的观察、过往独裁者的历史和这些人造成的恐惧来支持她的观点。这些独裁统治者包括贝尼托·墨索里尼、阿道夫·希特勒等,他们都给世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串名单的最后,还有唐纳德·特朗普。
她同意,我们不该随意称某人为法西斯主义者,以免这个强大的词语失去了它本身的力量。“我不是说特朗普是个法西斯主义者。”她说。不过,当她把特朗普和历史上其他法西斯主义者放在同一本书中相提并论,并以此来警醒大家小心法西斯复苏时,她确实认为特朗普是一位法西斯主义者。
在书中,她频繁地提示读者把现任总统和过去的独裁者联系起来。她提醒我们,特朗普时代发明的“抽干沼泽”(drain the swamp)这个短语,来源于墨索里尼时期的意大利短语drenare la palude。她引用希特勒谈论自己成功秘诀时的原话:“我来告诉你们,是什么让我站到了今天这个位置。我们的政治问题看上去很复杂,德国人已经无能为力……我把它们简化成最简单的术语。大众意识到了这一点,并遵守我的命令。”听上去熟悉吗?

图片来源:Chien-Min Chung/AFP/Getty Images
我向她提出建议,指出她的新书并没有给“法西斯主义”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是很难定义的,”她回答我,“首先,我认为法西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体系。”
正是特朗普的执政方法让他能够和1930年代的独裁者联系起来。法西斯主义者通常是政治舞台的大师,他们让“人民”反对“敌人”,靠此为生,煽动人们的情绪。法西斯主义者告诉支持者,复杂的问题通常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他们认为自己是国家的救世主,并把自己和国家合为一体。他们想要颠覆、败坏和淘汰自由组织机构。奥尔布赖特提醒我们,他们通常会通过选票来获取权力,然后从内部侵蚀民主的根基。她喜欢墨索里尼“一根一根拔鸡毛”的说法,因为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及时意识到自由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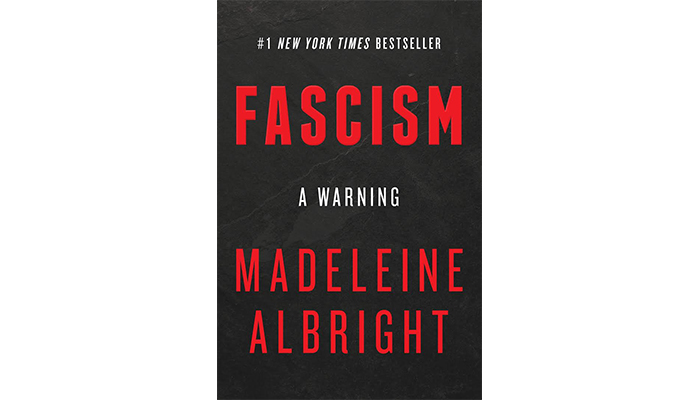
(翻译:李思璟)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