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托尼·朱特于2010年去世。这几年,他的书在国内陆续有译介和出版。《战后欧洲史》《责任的重负》《未竟的往昔》《沉疴遍地》《事实改变之后》……中文读者也逐渐了解了这位当代重要历史学家和思想家的思想全貌。
在托尼·朱特生命的最后两年,他饱受肌肉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亦称渐冻人症)困扰,《记忆小屋》是他患病之后口述的回忆录,也是朱特唯一一部谈论自己的作品。在一个个无法动弹的寂静黑夜里,朱特在脑海中一遍遍搜寻、整理过往的记忆,以此构建了自己的“记忆小屋”。他有时候关注小事,描写祖母的犹太料理、伦敦的绿线巴士、瑞士的小火车;有时候放眼大千,论及西欧战后一代闹剧式的革命、时代的思想禁锢,以及自己对于政治的观察和参与。这些文字在动人和锐利、私人性与公共性、具体发生的历史和身处其中的具体感受之间穿梭,追索的即是一个历史学家的人生历程,也是20世纪的复杂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而今在全球风生水起的反对性骚扰的运动和呼声,在托尼·朱特的时代,同样颇具影响力。上世纪90年代,作为一个从大西洋彼岸登陆美国的知识分子,托尼·朱特对于美国大学防范性骚扰的规范怀有微妙而复杂的抗拒心理,《女孩,女孩,女孩》这篇文章,回忆了他本人的成长背景,也谈起了他在当时在具体规范底下是如何做出选择和行动的。在而今,反性骚扰运动波及全球很多领域的情况下,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沉默,朱特的陈述,或许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展现知识分子对于所谓“政治正确”的个人态度。
女孩,女孩,女孩
文 | 托尼·朱特
1992年,我在纽约大学历史系当系主任——是系中唯一一个60岁以下的单身男性。“锦上添花”的是:大学性骚扰举报中心的地址和电话就赫然印在我办公室门外的公告板上。历史学是一个女学生越来越多的专业,系学生会时刻准备打击任何带有性别歧视——或其他更恶劣的——意味的言行。肢体接触即构成恶意企图,关上办公室的门就足以定罪了。

我上任后不久,一个二年级研究生来找我。她曾是芭蕾舞者,因对东欧历史有兴趣,别人鼓励她来我这儿。我那学期没有课,本可以让她改日再来。然而我没有,相反,我将她请进了办公室。我们关起门来讨论了一番匈牙利经济改革,然后我建议她进行自主研究——由我做导师,翌日晚间起在附近的餐馆进行。几节课后,我突然强打勇气,请她去看了《奥里安娜》(Oleanna)的首演,一部戴维·马密特(David Mamet)创作的讲大学性骚扰事件的无聊话剧。
怎样解释这种自我毁灭的行为呢?我脑内的宇宙究竟是有多梦幻才会以为唯独自己能安然度过那艰难克己的一小时——而两性规范交往的警钟却不会为我敲响?我对福柯的了解不输他人,也熟悉费尔斯通、米利特、布朗米勒、法鲁迪之辈。假使我说这女孩的双眼令人难以抗拒而我的意图又⋯⋯还不明朗,显然对我没有任何好处。那我有什么借口可说?拜托,先生,我可是经历过60年代的人。
60年代早期的青春期男性过着一种出奇封闭的生活。我们仍然秉承着父母的伦理观。由于都没车,加上家都小,没有私人空间,虽有避孕药,但除非愿意面对一脸反感的药店店员,否则无法买到:种种因素使然,那个年代的男女约会十分艰辛。于是大家都有充分理由认为,那时的孩子,无论男女,都纯洁、都百事不懂。我认识的男生大部分在男校上课,与女性罕有接触。我和一个朋友曾将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花在斯特里汉姆的勒卡诺舞厅,上周六早上的舞蹈课;然而到了当年的联谊会,从高登芬赖特梅尔学校来的女生照样笑话我们。我们于是终止了学跳舞的尝试。
即便你有对象约会,那感觉也像是在追求自己的奶奶。那个年代,女孩约会个个穿得俨然马奇诺防线:钩扣、束带、束腰、尼龙袜、提臀裤、吊袜带、衬裙外加胸衣。前辈们安慰我,说这些只是性感的小障碍,很容易绕开。然而我却产生了恐惧。而且,根据当时的电影、文学作品来看,产生恐惧的可不止我一个。过去的我们,都活在切瑟尔海滩上。
接下来,我们却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置身于“性革命”之中了。不过几个月,整整一代的女性就脱下穿了一个世纪的内衣,纷纷换上了超短裙和丝袜(或只是超短裙而没有丝袜)。我认识的 1952年后出生的男性中,别说见了,连听过上文列出的女式内衣的人都少之又少。法国流行乐手安托万在歌中乐观地唱着到“不二价”大卖场(相当于法国的凯马特)买避孕药的事。而在剑桥大学的我,则冷静而老练地替一个朋友为他的女友安排了一次堕胎手术。每个人都在“玩火”。
或者说,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在“玩火”。我那一代人相当重视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差别——我在加州认识的一个人,就用整整一篇博士论文探讨了“理论与实践中的理论与实践”。性爱方面,我们的言行是相互矛盾的。理论上标榜自己勇于革新,现实中却是一群循规蹈矩的人:少年时期度过的50年代对我们的影响,要比青春期的60年代更深。我们中许多人很早就成了家——且大多娶了各自交往的第一个正式女友。许多人的婚姻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为他人行为自由的权利而战斗,自己反而没大张旗鼓地干过什么。
我的前辈们成长在一个逼仄的,有如《幸运的吉姆》和《愤怒的回顾》中所写的世界里。他们对规则既敬且畏,也许会勾引小职员或女学生,但仍本能地受到纪律的束缚,不敢将自己的幻想活成现实。相比之下,我们这一代的情况则是幻想、现实不分彼此。60年代的唯我主义——“做爱,不作战”“走自己的路”“做自己就好”——一举冲破了所有的禁忌。但它同时也模糊了伦理标准,因为没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了。
1981年,我刚到牛津时,曾请一个学生和她的男友吃饭。我太太和我当时住在乡下的一个小村子里,那对年轻情侣抵达时,天降大雪。于是两人只得在我家过夜。我没做多想,就领他们去了有张双人床的小客房,随后便道了晚安。过了很久我才突然想到,尚不知他俩是否同床睡。几天后,当我小心翼翼地重提此事时,年轻姑娘拍着我的肩膀说:“别担心,托尼,我们理解你这种60年代的作风!”
我的后人们从老规矩里解放出来,又给自己戴上了新枷锁。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人严格抵制任何带有骚扰意味的言行,甚至不惜抹杀友谊的可能性和暧昧的乐趣。他们像10年前的人一样,虽然出于不同原因,却也严防死守到了不自然的地步。这不禁令我沮丧。清教徒禁人我之欲尚有自己的理论可依;如今这些人畏首畏尾却没有什么好理由。
虽然如此,当代社会对性关系的紧张情绪,偶尔也能给生活带来一些笑料。我在纽约大学人文学院任院长时,一个颇有前途的年轻教授被他系里的研究生指控对其有不正当接近。原来,他跟踪人家进了储藏间,并向她表白了。我去核实时,年轻教授承认了一切,并求我切勿告诉他太太。我的心情很矛盾:教授当然做了蠢事,但他一没有实施恐吓,二没有用成绩利诱。不管怎么说,他最后还是得到了严厉的警告。实际上,他的事业也等于是毁了——系里后来不再留任他,因为再也没有女生愿意上他的课。而他的“受害者”则接受了常规心理辅导。
几年后,有人请我去校律师办公室。问我是否愿意作为被告方证人出庭,因为那同一个女生又把纽约大学给告了。注意,律师提醒我:这个“女生”实际上是“男生”,这回起诉是因为学校没能认真对待“她”作为一个变性人的需求。官司要打,但我们也不能显得麻木不仁。
于是,我来到曼哈顿最高法院,向忍俊不禁的、由管道工和主妇组成的陪审团解释了大学性骚扰的复杂情况。学生方的律师向我大力施压:“是否有人已经告知您我方当事人选择改变性别的事,因而影响了您的理性判断?”“我认为不会,”我回答说,“我一直视她为女性,这不正是她所希望的吗?”大学最后打赢了官司。
还有一次,一学生指控我因其未提供性利益而“区别对待”她。系里的调解专员——一个讲道理且素有不肯因循守旧之名的女士——居间调查时发现,学生实际上是因为我没有请她参加我的研讨会而不满:她认为参加进来的女性必定都得到(并付出)了优惠待遇。我解释说,请她们来是因为她们更聪明。女生震惊了:原来除了性以外,被区别对待还有其他原因。她怎么也没想到,我不过是个精英主义者罢了。
有一个现象很能说明问题。与欧洲学生探讨带有露骨性描写的文学作品时——比如米兰·昆德拉的作品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们向来很放松。相反,美国年轻人——无论男女,平时个个直截了当,这时候却纷纷陷入紧张的沉默中:因为害怕逾越界限,他们不太愿意参与这样的讨论。然而,“性”——抑或文艺些的提法,“性别”——却是他们解释现实世界成年人行为时,首先想到的因素。
然而,正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对待性时,也把60年代的态度太当真了。对待性(或性别)时,过分关注或彻底无视,都是扭曲的。而只有把政治当娱乐、把政治当作自我的外在投射的人,才会想到要拿性别(或“种族”,或“民族”,或“我”)而不是社会地位或收入区间来区分人类。
凭什么所有的事都得跟“我”扯上关系?我的关注点对作为整体的大众来说,有什么要紧的?我个人的需求就能代表大众的需求吗?“个人的就是政治的”,说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如果所有的事都是“政治的”,那便没有什么事是政治的。我突然想到了格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在牛津大学讲当代文学的一堂课。有人问她:“那么女性问题呢?”斯泰因的回答应该被张贴在从波士顿到伯克利的每一处大学公告栏里:“不是每件事情,都能涉及所有问题。”
我们青春期随便喊出的一番口号,竟成了此后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但至少60年代时,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管嘴上怎么说,性⋯⋯就只是性。当然,对此后果我们还是难辞其咎的。是我们——左派、知识分子、教师——将政治放手给了一群对掌握实际权力比探讨权力的隐喻内涵更有兴趣的人。而政治正确性、性别政治以及对情绪伤害过分小心翼翼的做法(仿佛不受冒犯是一种权利):这就是我们从中得到的一切。
我为什么不能把办公室的门关起来?为什么不能请学生去看话剧?倘若我“悬崖勒马”,不就成了彻头彻尾的集体主义的“自我阉割”——未被谴责先觉有罪——给别人做了懦弱胆怯的先例?正是如此,而且正因为此,我看不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过错。当然,若不是我在牛津剑桥年间树立起的精英做派的自以为是,恐怕也不会有如此行动的勇气——虽然我一贯承认,知识分子的孤高和一个人的时代优越感之结合,的确很容易让这个人产生自己坚不可摧的幻觉。
事实上,正是这种自认无往不利的态度 ——一旦失之极端——引发了比尔·克林顿自毁前途的越轨,也导致托尼 ·布莱尔以为,参战正确性和战争必要性仅凭他一家之言即可决定。然而请注意,纵使再如何不知收敛地招惹是非、炫耀姿态,克林顿和布莱尔——以及布什、戈尔、布朗和许许多多我的同代人——还都继续与各自的第一任正式女友保持着婚姻关系。这方面我自认不如——我于 1977年、1986年两度离婚。然而,60年代那种激进态度和保守家庭观并存的现象,依然以其他的方式困住了我。那么,我是怎样在苟且地约会了那位有着明亮双眼的芭蕾舞者后,又逃脱了性骚扰警察的制裁的呢?
读者们:我与她结婚了。
(本文选自《记忆小屋》第三部分,由出版社授权发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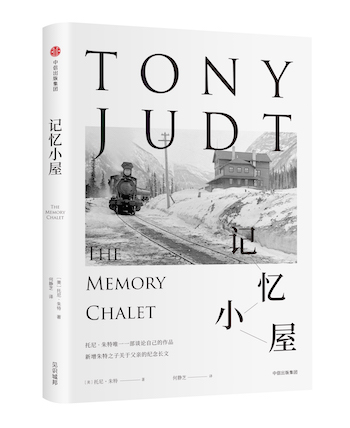
[美] 托尼·朱特 著 何静芝 译
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7月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