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马丽,系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加尔文大学亨利政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中国大迁徙:当代中国的移民、城市主义和异化》(The Chinese Exodus: Migration, Urbanism and Alien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最近新闻中频繁出现的、对城市犯罪案件涉事者曾是农村“留守儿童”身份的讨论,以及苏州等一些学校用隔离网和分班来区分外来移民子女与本地户口学区孩子的做法,再次引起人们对自1980年代出现的城乡移民潮这一“世纪撕裂”的回顾。
对于这场中国社会最大的转型和变革,马克思有一句话可以很好地概括,“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 曾经,提供人们身份和社会关系的地缘和业缘、单位制在二三十年前都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处于一种流动的状态,却并没有提供给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归宿。
当第一代打工者在80年代初进入城市时,他们从事的一般是郊区种菜、卖菜、保姆等工作。当时各个行业还形成了一些口碑较好的“品牌”,如山东的卖菜小贩、安徽的保姆、四川的厨子等。在1983年前,因为粮票还存在,这些打工者都只是带上口粮短期进城,这些工作也都是可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在他们的记忆中,被称为“盲流”和躲藏的经历还很深刻。城市是不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的本分是要继续在社会主义农村做建设。连他们自己,在被管制、被遣回的时候,也心存愧疚,仿佛背离了国家对自己的身份安排。在城市管理者看来,“盲流”的确给整齐划一的城市单位体制生活带来了不确定因素,更强化了他们对其“非法性”的认识。这些城市的外来人也因此永远不能够期望城市提供给他们任何的归属感。
我曾与一位资深NGO人士马姐访问北京刘娘府附近的民工聚集区,她自己属于很早的一批移民,1981年就从安徽进京做保姆,后来在外地民工聚集区创办了一个打工妹之家,开展一些妇女和儿童的社区活动,让原本封闭在家中带孩子的妈妈们有个去处。马姐说,她从1982年到北京之后,搬了一百多次家。我记得和她一起站在社区的一堆拆迁瓦砾面前时,她曾无奈地感叹说,“这里曾经生活过这么多人,但多少年之后,哎,谁会记得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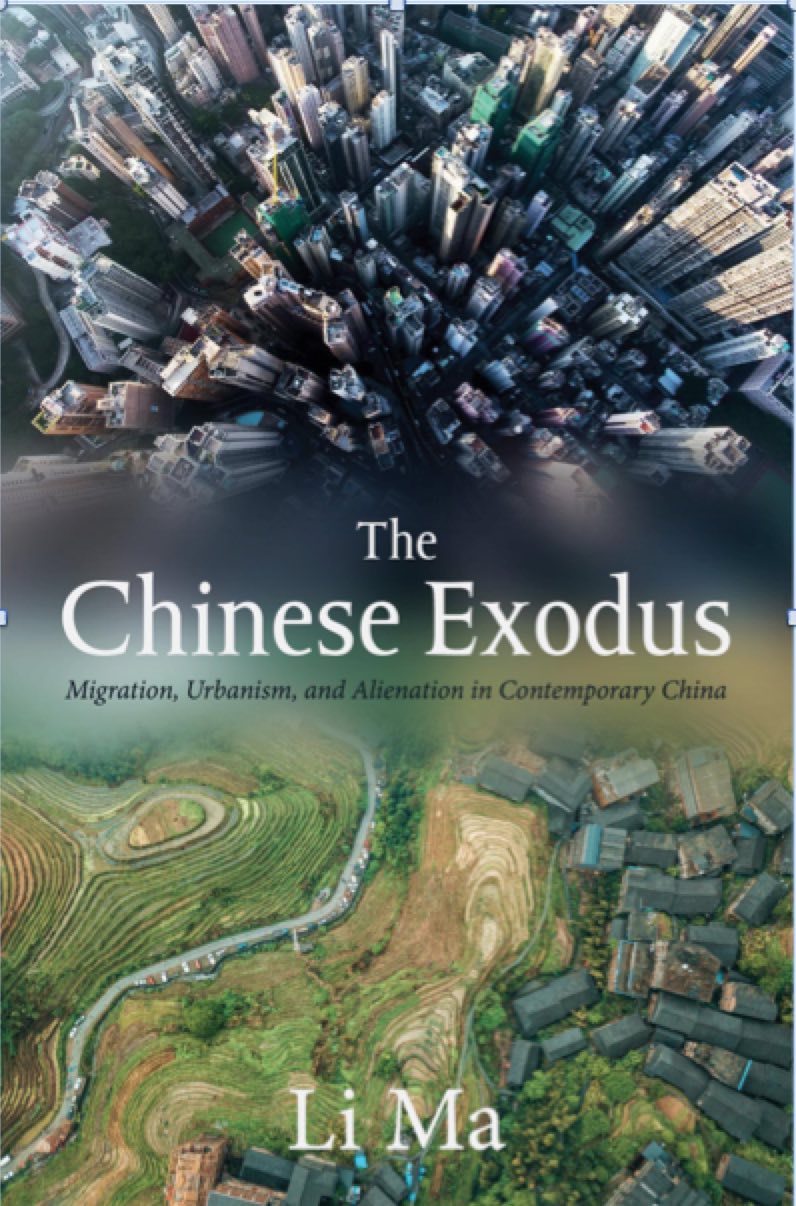
如果说对异族因陌生而产生的歧视是人性的一部分,那么歧视一旦被制度化,就会成为更加顽固的社会疾病。而社会的溃败,往往是从语言的败坏开始的。例如“盲流”一词,它是一个集体名词,将具体的人之人性消解,两个词分开来描述这些人的“非理性”、“非法性”和“流动性”、“不可控制性”。城市管理者甚至会把“盲流”与“流氓”两个词并提,给这些人建构起一种道德污名。这个词在城市人的心中根深蒂固,甚至到2009年时,一些街道管理者仍使用“盲流”一词来指代进城务工者。

在1984年农村公社解体后的十年,乡镇企业成了一个新的增长和就业模式,进城务工也被政策允许,只是仍需要自带口粮。待乡镇企业这一尝试彻底失败,自90年代中期,大城市的基础建设(建筑工地)成了大量农村打工者洒下血汗的地方。他们的脊梁扛起了公路大厦。 在同一时期,城市身份开始被商品化,甚至出现了户口买卖的黑市场,给少数人开了一条“跳农门”的通道。但是在臭名昭著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之前,农村移民仍是城市管理制度下不被欢迎的人群。只有在孙志刚事件之后,对农村移民的同情心才占了社会风气的主导。
自2000年初,随着私营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打工者进入到城市中的“非正式经济”中,成为城市多个产业的临时工和合同工,不再只是集中在建筑业和郊区农业。连支撑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制造业也依靠大量的农村移民作为主要劳动力。尽管与城市居民“同工不同酬”(城市居民是享有三险四金的正式工),这段时期进城闯荡的大多数,仍是第一代青壮年打工者,他们对于自己可以在城市落脚,已经很满足了。
到了2018年的今天,出现在城市经济的历史舞台上的大部分农村移民,都已经是第二代打工者。年龄上可能是90后甚至00后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同质的群体:都有“留守儿童”的成长经历,学历不高,没有专业技术。这些特征都是三十年来制度性歧视所结的果子。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比父辈出来打工时的学历更低、年龄更小。
日本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是这一群体的肖像。在与祖父母或亲戚“留守”农村十几年后,他们从初中、高中或技校毕业,兴冲冲地奔向大城市深圳。很多年轻人的父母还留在城市打工。因为父母从来都在城市打工,时不时告诉他们城市里的繁华,带回一些新鲜商品,让他们觉得自己,人生的路就是长大了也出去打工。父母们以前不会告诉这些年轻人外乡人在城市里的艰辛,因为中国人离家都只会“报喜不报忧”,而且对孩子还能说什么苦呢。因此第二代打工者对城市的憧憬过高,幻灭也更深。
第二代打工者一般都没有农业劳作的经验,但不同地区收入水平的差距,让他们还是觉得如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钱好挣”。正是一种直观的贫富差距,吸引他们幻想着远方的机会。那些刚进城的、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们,身上总带着一种斗志和向往。殊不知,当他们刚下火车的时候,已经有一批对同一个大都市幻灭的打工者刚刚离开。那些先到达的,在反复经历长时间工厂劳作、雇主不公克扣、黑中介诈骗,甚至流落街头之后,品尝了外乡人的种种屈辱和绝望。教育水平不高的他们,连描述自己这种绝望的语言也很单调:“累怕了”、“没意思”、“不够睡”、“没梦想了”。在《三和》纪录片中,当摄影师追踪的几位打工者在长期焦虑、失业、睡大街后,最终决定离开深圳,辗转去其他地方谋生路,好像还想去寻找更好一些的打工目的地。
与此同时,总有源源不断的打工者刚刚到达深圳。那些面带惊喜、满腹壮志的,都又是刚刚下火车的。后到达的他们,也会渐渐发现自己也只不过是七百万移民打工者的一员。每个人都只是重复着同一个不能改变的、幻灭的现实。
与第一代打工者不同的是,他们将欲望投射在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上。他们熟悉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网络游戏。因为对于大多数留守儿童来说,这些新鲜商品早就成了父母回乡带来的城市精神的象征。如果说城市家庭中还有很大比例的父母会质疑电子游戏对孩子的认知(专注力)和精神状态有负面影响的话,大多数农村家庭对此类科技产品都是照单全收。因此,这些便宜的电子产品陪伴了他们孤僻的童年,有一种亲近感,也塑造了一种慵懒的精神状态。当留守儿童在城市和乡村、亲戚和父母、过去和未来之间,被抛来抛去的同时,这些电子游戏产品却忠实地相伴身边。等很多人成年后,加入进城打工者的队伍时, 网络游戏谈不上是一种寄托,而是一种不用思考、忘我的生存习惯。网游给他们赋予新的身份,他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实现真实生活中不可能达到的愿望,包括物质上的(好车、好房)和精神上的(爱情、尊贵、荣耀)。
从80年代到2000年代初,第一代从农活到建筑工地和工厂的打工者,大多数人的精神寄托是为家乡的亲人(特别是孩子)多攒钱。除了公用电话和后来的手机(非智能),他们没有接触过通讯产品。五六年之内,网络和黑网吧进入到农民工社区里,成了大多数民工子女的课后去处。又十年之后,人人用手机上网的时代,让这一幼时的激情可以随时随处延续。没有克制,没有警醒,因为都是新时代所赋予的娱乐。活着不娱乐,挣了钱不娱乐,还能做点什么呢?
一个叫东东的年轻人,宁愿在奶茶店打一天的工,挣个100块钱,然后到网吧玩两天,钱没了再出来找“日结”的工作。他们不考虑明天,不考虑结婚,没有养儿育女的愿望,也不觉得对父母有储蓄养老的责任。甚至几天不吃饭、不洗澡,都成了很无所谓的事。《三和》纪录片中提到的“三和大神”精神就是这样一种因贫困而近乎超脱现世的心态。真的只是因为贫困而超脱吗?纪录片导演在和这些农村进城年轻人熟悉之后,才挖出他们为什么宁愿找“日结”(做一天付一天的现钱)的工作也不为明天打算,背后有很多辛酸的原因,只有打工者自己才体会得到。
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密度和高流动性,让社会关系趋于瞬间即逝(也被社会学家齐美尔称为“匿名性”),降低了犯罪的社会监督成本。在一个缺乏有效监督和保护的劳动力市场上,从求职、雇主面试到开工、领工资,每一环节都布满了陷阱和欺骗。在这个谁也不知道谁底细的城市社会中,没有社会经验的年轻人对职业中介黑幕和黑心老板防不胜防。 他们不是因为“不上进”、“不努力”,才选择“日结”这样的就业方式,而是被城市经济的现实伤害得怕了。
大企业即便黑,就算新闻上曝光,过几年还是继续招工。到人才市场的打工者们,看到富士康的招工广告,都会摇摇头:“去过的,这个不好。”有一位打工者解释自己为什么不愿意进工厂:“一进去,身份证被抵押,万一碰到个黑老板,连跑都跑不出来。而且用机器容易出事。”他说做“日结”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至少保护自己的“自由”和身体安全。
尽管“日结”让每一天好像浑浑噩噩,但至少自己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工作,什么时候休息,什么时候玩网游。吃饭也有很多自由,不像在工厂里,有的黑老板只给菜汤,但自由的“日结”生活,就可以在市场周围选择自己喜欢的小吃。还有一些再也无法负担起自己生活的年轻人,最终选择以100-200元的价格出售了自己的身份证,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个隐喻,曾经,他们的身份就因为户口等等,不足以让他们享受到同处在一个城市中其他有这种社会身份的、同龄人的那些权利,最终将身份证卖掉,却无法让他们逃离那个无所不在的无形的身份、阶层之网,相反,却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用一位出卖了自己身份证的年轻人的话就是,“我们就再也不能够离开这里和这样的生活了。”
詹姆斯·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写道,当传统反抗形式(如公开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对从属阶层来说过于奢侈时,他们会频繁、持续不断地诉诸一些微妙的行动,如偷懒、开小差、装傻卖呆、怠工等形式。久而久之,一群人会心照不宣地同时使用这些消极方式来自我保护。
第二代打工者愿意在城市里流放自己,只要那是他们可以选择的自由。这种生活方式很像他们自幼在农村养成的习惯:没有大人约束、散漫、得过且过。他们的生命始终处在对金钱的渴望和对现实无能为力的不安中,他们游离在这个城市,就像他们曾经游离在农村一样。反正家的感觉,对他们来说,已经很遥远了,而饥饿、生计、经济上的绝望,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的恐惧正在一点点吞噬着对未来的希望。正如一个28岁的年轻小伙子对《三和》纪录片摄制组说的:“我们已经被这个社会抛在后面了。”
也许他们在年幼时曾因父母的离开,而心神不宁、撕裂般地痛苦过,但一旦那种亲情和亲密感的纽带被提前剪断了,与家人团聚的期待一次次落空了,接下来的一辈子,即便遭遇什么不幸,好像也不会太疼了。他们也不为未来焦虑,好像在这个到处充满陷阱的城市,活一天真的就是赚的。当他们向《三和》纪录片摄制组倾诉内心,说知道“自己已经废了”、“就是在耗青春”时,他们脸上仍会挤出那淳朴的微笑。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