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思想领袖”都要有一套标志性的绝学。弗朗西斯·福山的名字和命运则与“历史的终结?”这句标志性的政治流行语密不可分,自1990年代早期起,在历史显然拒绝终结的这些年头里,在斯坦福大学担任高级研究员的福山屡次三番地做出尝试,想要重现他最初的成功。他的新书《身份认同》(Identity)诉诸了“血气”(Thymos)这一概念,主张它是理解眼下这一令人不安的政治时刻的关键。
“血气”(如果古希腊人对这一核心关键词的确有着最好的理解,那它就无损于可信度和书的销量)一词出自柏拉图的《理想国》。苏格拉底曾提出,灵魂内在地划分为两个彼此竞逐的部分,即理性和欲望,而柏拉图则认为灵魂还有第三个部分。如果说理性与人性相对应,欲望与动物性相对应,那血气就处于这两者之间。大部分《理想国》的译本都认为柏拉图所用的这个词在意涵上与“激情”(passion)相近。从其写作目的出发,福山主张,它的意思应当是“价值判断的处所”,类似于某种永恒的地位调节器(status thermostat)。
福山相信,许多其它政治理论家严重忽视了“血气”这一概念,但它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古典经济学试图以个体最大化其财务上的自我利益之类的术语来解释世界,但行为主义名作《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却指出,我们的理性能力经常被各种更具直觉性的力量削弱。福山主张,这些力量里面最为强大的,就是追求被尊重的欲望。
或许有人会提出,这一特定的张力,不过是自《傲慢与偏见》以来19世纪小说的常见设定而已,福山则认为,那是因为我们已经渐渐地失去了对人类本性之愚蠢的洞察。1930年代以来,一般而论的、马克思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已经瓦解了为了身份政治的利益竞逐。比起对于财富或安全的欲望而言,我们究竟是谁以及我们所认同的文化或国族群体类别,潜在地看,乃是一股更为持久的心理力量。
“血气是灵魂中渴望承认或尊严的部分,”福山提出。当其处于平衡状态时——“平等的激情”(isothymia)——便会产生想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取得他人承认的需求。阿瑞莎·富兰克林(Aretha Franklin)如同战吼一般的“尊重”呼声,为女性主义、民权运动和同志解放所共享,堪称一曲平等激情的颂歌。不过,一旦这种激情失控,那就会成为“凌驾他人的激情”(megalothymia)——亦即想要他人承认自身优越性的需求。一个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个体或群体,对自由主义的简单平等和拉平力量是高度不满的;他们想要“冒巨大风险、参与史诗般的斗争、追求宏大场面,因为这一切都导向期望他人承认自身的优越性”。听起来很熟悉是不是?
福山所谓血气比我们熟悉的自我(ego)或身份认同能更好地解释形塑眼下政治局面的非理性力量,这一说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立,目前不甚清楚,但他认为血气是个激发性的因素,可以同时解释普京的无情权谋和反性骚扰运动如病毒一般爆发的盛怒。而特朗普上台和英国退欧则出自凌驾他人的激情,它们乃是对多元文化主义和国际合作中的平等激情的反动。

从一定意义上说,后面这些现象也为福山于1989年提出的那个富有先见的问题提供了一种回溯性的负面答案。其名作《历史的终结?》后来扩写为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且销量火爆,在许多人看来,它解释了自由主义何以能取得对其它极端意识形态的“胜利”。

弗朗西斯·福山 著 陈高华 译
理想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09
鉴于该书在柏林墙崩塌这一历史性时刻问世,福山对其论点的再三补充说明(“这句话结尾是问号!”;“这是抛砖引玉而已!”;“‘终结’是指‘目标’而非‘结局’”)遭到了无视。在余下的职业生涯里——前苏东国家中独裁者和民族主义的沉渣泛起,削弱了其理论说服力——他花了大把时间和精力来修正那个夸张的说法。从这个意义上讲,血气只不过是他一生修修补补的一个小插曲而已。
不久前,我与现年65岁的福山就其新近的分析有过一番电话交谈,当时他还在加州的家中。十来天之前,他还在解释伊拉克中层官员对民主的推动。我一开头就问他:对选民理性动机的过度估计,究竟是一个普遍的状况,还是我们时代特有的症状?
他承认这并非新现象,但表示最近十年来我们似乎捧上台了一批相当典型的飞扬跋扈之人。“你知道,退欧会让英国经济付出很大的代价,因此退欧之举是不理性的,”他说。“但后来事实却证明,许多投票支持脱欧的人不但对此毫不在意,而且宁可繁荣受损也在所不惜。问题出在文化上,他们似乎甘愿付出这样的代价来控制移民。归结起来看,许多精英的错误在于,他们自以为能让政治只受经济理性引导,将国家认同感与之割裂开来。”
但这些民粹主义运动不是也能被某种孤注一掷的理性(desperate rationality)解释吗?鉴于近十年来个体的经济处境并无多大变化,一旦颠覆一切也能说得通了,它或许就是最后一搏?
“全球化无疑让很多人掉队了。自动化程度越高,不平等就越加剧,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仔细考察一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退欧的投票模式的话,你会发现两件事里的支持者其实都不算上述各种力量影响下的最大输家。如果你再看一看过去十年来在国外出生的英国公民数量,就会发现它的增长是相当明显的。这种规模的社会变迁如果掀不起一丁点逆流,那我反倒会觉得奇怪了。”
他认为,追求政治正确或曰要求尊重一切类型的差异,既产生又掩盖了上述的潜在感受。说得宽泛一点,他是否相信,过于坚持要求承认差异,将会令我们忽视彼此之间的纽带?
“左右两派都有自己版本的身份政治。左派版本的历史要悠久一些, 不同的社会运动都在强调自己与主流文化的差异,要求在各方面得到尊重。右派对此的反应则来自于产生如下疑问的人群,“好吧,那我们怎么办?为什么我们就没资格得到特殊对待?”从政治上讲,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它弱化了公民身份感(sense of citizenship)。而如今,左右两边都滋生了激进倾向。“

福山表示,如果没有第45届美国总统选举这件事,他根本就不会写这本书。他坦承说,自己和其他人一样,此次都没能预测到这些不幸的事实,但即便如此,单就特朗普这个异常恶劣的例子而言,福山倒是在三十年前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一书里预见到了他将“放纵无度——或曰傲慢地展示”其凌驾他人的激情(该书后半部分谈论末人处境时,福山提到了当时还是地产商的特朗普,视之为优越感过强的典型人物——译注)。而我则认为,金融崩溃近十年来所积累的焦虑心态,再加上战争导致的大规模移民等等征兆,可以说又提前敲响警钟的性质。莫非从来没有伟大的先例可言?
“我认为经济崩溃会导致一种更加直截了当的左翼民粹主义,”他说。“这一大规模衰退的始作俑者是华尔街的盗贼统治(plutocrats),但你得到的却是茶党和右翼积极分子的兴起。这部分地可以用1930年代以来日益兴起的身份认同议题来加以解释:人们更倾向于关心微观的不平等而非宏大的阶级斗争了。”
在他看来,特朗普四面开花的非自由主义行径是短期现象还是新的现实?“他肯定不是短期现象,”福山说,“暂且不论他造成的各种破坏、种族主义和荒唐举动,最令人不安的事情还是他享有的支持度。看起来,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他的举措表示认可,另外还有10-15%的人会因为他的减税政策而捏着鼻子勉强忍受他。”
另一方面,民主党也因此而日益左倾化,这导致了一种中间派失势的局面。“特朗普为了激怒左派,几乎是出于直觉地炒作了一些种族话题,而左派在回应上也越来越激进。我觉得他发现了分裂民众的机会,试图瓦解民主党这个竞争对手的团结。”
在见证这些力量时,我认为——并且注意到——无论英国退欧的支持者如何诉诸所谓“闪电精神”(Blitz spirit,指临危不惧、当机立断的态度——译注)来支持那些根本不可能得到辩护的方案,迄今为止他们仍然奇迹般地受到约束。《历史的终结?》似乎传达出了一种胸有成竹的乐观态度;其论旨与马丁·路德·金坚信的“道德的苍穹是漫长的, 但它却终将落向正义”颇有相似之处。如今他是否还有信心坚持这一乐观态度?
“我不太清楚自己是否乐观,”他说。“从某些方面看,这股逆流来得晚了,这有些出乎我的意料。”
福山自己属于第三代美国移民。他的祖父为了逃避1905年的日俄战争而移民到了美国西海岸,并在那里开了一家小商店。他的父亲则是个基督教公理会的牧师,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他的母亲出生于京都,是京都大学经济学系创始人的女儿。我问他,幼时在餐桌上究竟谈到过哪些有关同化和身份认同的重大问题。他会认为自己是个日裔美国人吗?“我从来不用那种方式来思考自己,”他当即答道。为什么?“我在成长阶段基本没在日本人社群呆过。”
他甚至没学过说日语——看起来也没有这种需要。“我觉得美国确实是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人可以自由成长,没有谁会因为族群背景而给你设置障碍。”如今,他表示,自己最近正为斯坦福大学里某些校园团体希望他与“一些亚裔美国人群体”会面而感到烦恼。他觉得这完全不是他的为人处世之道。
他父母也是这样想的吗?“我父亲会说一点日语,但不太流利。他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就一直在洛杉矶的学校体系内长大。我的母亲在日本出生,战后来到美国。她说英语的时候会带点口音,父亲则没有口音。我还记得,母亲多次说过她觉得美国人有种族主义倾向,她曾经遇到过歧视云云。但我也记得父亲说,自己在一生当中从未因为日本背景而碰壁。我觉得归结起来看就是这样,‘如果你能说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那你就会被接纳。’我的母亲恰恰不会。如果你观察一下美国的亚裔美国人,就不难发现,无论以何种尺度来衡量,他们都表现得比白人要好。”
看到去年在夏洛茨维尔发生的那场不无3K党风格的游行之后,他会对这些一直以来深信不疑的东西作何感想?“美国国家认同得以建立在一定的公民身份理念之上,是由于斗争而来,以民权运动的胜利为标志,”他说。“但转眼间你就发现,人们对何谓美国人的理解纷纷染上了了族群色彩。这是很不好的现象。特朗普为这些人群提供了支持和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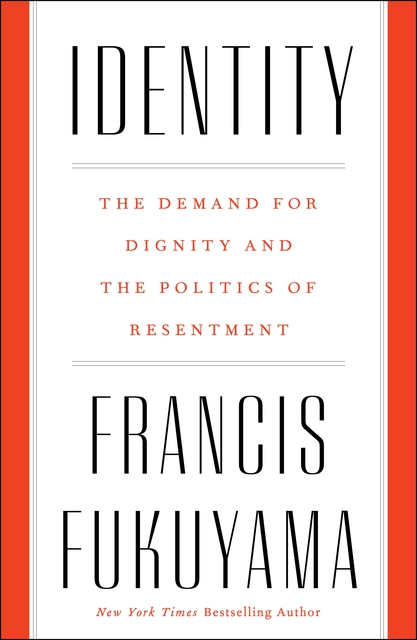
福山写书的目的,部分在于为这种高度分裂的政治局面开出解药。他强调,目前亟需一种能够与全体公民的关切展开对话的政治家,这样的政治家能有超越狭隘身份关切的全国视野,而非只顾自家利益。他会鼓励一些探索性的政策,譬如以国家服务(national service,一般指兵役,此处根据上下文看应为广义上的公益活动——译注)来使青年人认识到不同背景的人群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在目前英国和美国的政治气候下,他的构想真的能实现吗?
他承认说,“除非在自愿的基础上,否则不大可能。”“在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福山说,“曾经有过一项规划,青年人可以去市中心的公立学校参加一些志愿工作,或者从事其它类型的服务。我觉得范围还可以拓宽。但我觉得可能需要一场战争或重大外部事件,来激发这种参与服务的自愿性。”
福山认为,另一当务之急在于,政治家需要明白:互联网扮演了身份政治的加速器角色,社交网络允许个人只听取小群体的狭隘见解,而无需参与全国范围内或更加广泛的对话。“一般认为互联网有利于民主,因为它让人们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进而取得权力,”他说:“但我认为作为旧媒体象征的编辑、‘看门狗’和事实查验者仍是十分有用的——它们能降低虚假信息的传播速度,确保信息有起码的质量。这一切如今都是过去时了。你在网上看到的所有东西大体上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这类政策仍然阙如,他对未来的美国政治有何预期?他是否相信上述的过滤机制能驯服凌驾他人的激情?
“中期选举之后再来见分晓吧,”他半带笑意地说道。“在民主体制下,我们所拥有的制约权力的最大手段就是选举。如果共和党重夺两院控制权,那将被视为是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一种肯定,情况就很不妙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民主党赢下了众议院,那我们就能从其质询中得到潮水般的此类信息。这届政府在每个政策领域都是极具毁灭性的——无论是环境、健康还是住房——我认为他们需要对此有个解释。”
暂且不论各种相反的表象,他是否坚信自由民主仍有以柔克刚的能力——换言之,西方民主是否仍有可能被拉回平衡状态、设法保持中道?“这又回到了领导者的问题上,”他坚称。“如果缺乏能洞见这一鸿沟并设法跨越之的政治家,那么就很难回归正常。”
话虽如此,这位在现代政治生活中也许是最为知名的预言家仍表示,“要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实在很困难。”
(翻译:林达)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来源:卫报
原标题:Francis Fukuyama: ‘Trump instinctively picks racial themes to drive people on the left crazy’
最新更新时间:09/27 19:06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