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身名门,家族的影响催生他书写祖辈时代的文化轮廓;感知当下,香港的历史根基加深他与代际之间的对话。“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够理请当下和展望未来。”
本期《精神的壳》特别企划,网易蜗牛读书独家对话作家、青年学者葛亮。历史的厚重在他笔尖倾泻,历史人物归置家庭本位,从《北鸢》到《问米》,他在古典的“孤岛”写作,笔下尽是人间。

名门之后、名校副教授、最年轻的《亚洲周刊》小说奖得主……这些身份对于葛亮来说,都只是外界给的标签。从南京到香港,他在自己的作品里衔接家族的过去与当下的生活。从《北鸢》到《问米》,他在古典的“孤岛”写作,笔下尽是人间。
“家族的积淀,为我厘定了做人作文的尺度”

家族的名望是葛亮一直逃不开的话题,个人成就也常常被与之绑定,2009年的《朱雀》、2016年的《北鸢》,以及今年的《问米》,每本书的成功都让人不免好奇这位名门后生,生于70后却被称为“活在历史里的当代人”是如何以笔为眼,展现独特的历史侧写与文化审美。
韩少功曾言,葛亮的少年成熟令人惊叹,顺着文字的轨迹,不难窥见他的创作中充满着儿时耳濡目染的家教。葛亮自己则这样评价,“实际上每个人都有来自家族的滋养,这是我们生命中势必会面对的一件事情。”
对于他来说,家族的沉淀为自己的写作和人生都“厘定了一些很重要的尺度”,这些在他的写作中构成了某种重量,也在不断提示着他未来的写作重心。
在与父辈的交流中,葛亮被寄予的期许是他作为后辈,能对整个家族、对这个时代有一定的观察,“希望我作为一个当代人和那个时代中间有一种衔接和体认。”因此“切入历史”和“表达当下”,成为了葛亮的文学创作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母题。
家族的故事对葛亮的历史观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祖父葛康俞教授见背后,留下了一部艺术史遗作《据几曾看》,在家人与祖父生前好友的共同推动下,这本书得以正式出版。
深受这份时代温度的感触,葛亮决心以《北鸢》书写那个时代的文化轮廓。“其实这本书里写了很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人物的原型和我的家族也都相关。”
在这样的大历史作品中,葛亮倾向于把人物以家庭为本位,从家的角度去表述国,“因为家国概念一直都是我们历史表述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而我相信把历史人物从家的角度切入,实际上体现的是更有温度的人之常情。”也正是这样细腻的洞察,让葛亮的作品更能引发读者的共鸣。
读书造就多面历史观,写作沉淀内心力量

儿时的阅读经历深受父辈的影响,学俄语出身的父亲要求葛亮从小读旧俄的小说,提起帕斯捷尔纳克、法捷耶夫的作品,葛亮一连用了“篇幅巨大”“难以进入”这些词来形容,“小时候会有抗拒心理,但他们建筑了我对于文学格局最初的一种体认,使我受益匪浅。”
此外,少年葛亮的阅读清单里还有不少笔记体小说,不论是《世说新语》《阅微草堂笔记》,还是比较冷门的《耳新》, 都为葛亮建立起了中国文字审美的门槛。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学类型,在葛亮的文学创作中影响深远。
他为《北鸢》的民国时代背景特别打造了一种语言,既能承接古典文学的审美,又能够让当下的读者进入理解,“胡适先生也说过,笔记小说可补正史之不足,所以你在这样的事业中,再去把握对于历史现实的关照,就会从一个更有温度、抛弃成见的角度去看待历史。”
葛亮自己推崇的,还有沈从文、汪曾祺们的作品,“他们让我看到了中国文学的源流中,像醇酒一样越酿越陈的审美力量,它在平和中有暗潮。”
葛亮从中解读出一种对于历史民族文化的深层反思,以及我们在不同角度的视野里,可能获得的一种开放性结论。新作《问米》则是他对日本大师横沟正史的致敬,写悬疑却又不同于寻常小说的“步步为营,一以贯之”。
跳脱出《北鸢》《朱雀》“大风起于青萍之末”的历史观,他像横沟正史那样“将庸常的人生放在一种非常的境域之下”,期待能爆发出“非同寻常的人性张力”。“我希望能够让大家体会到在对我常态写作印象之外另一个维度和面向的我”。
如今葛亮身为浸会大学副教授,本职工作与香港的快捷生活节奏日常饱满,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文学创作,用葛亮的话说“是一种审美的整理和生活的梳理,实际上是内心的沉淀”。他通过这个过程让自己安静下来,并享受写作。
从2005年短篇小说《谜鸦》获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奖的首奖,到2010年成为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最年轻的获奖者,在这个年轻一代任何写作想法都值得尊重的时代,葛亮觉得这种文学奖项培育机制和对新人作家的挖掘培养非常完整。“一旦有一个年轻人对写作感兴趣,这种兴趣也许一时的,但是这些鼓励,使得他的文学创作生命力和延展性有了更多的空间。”
“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够厘清当下、展望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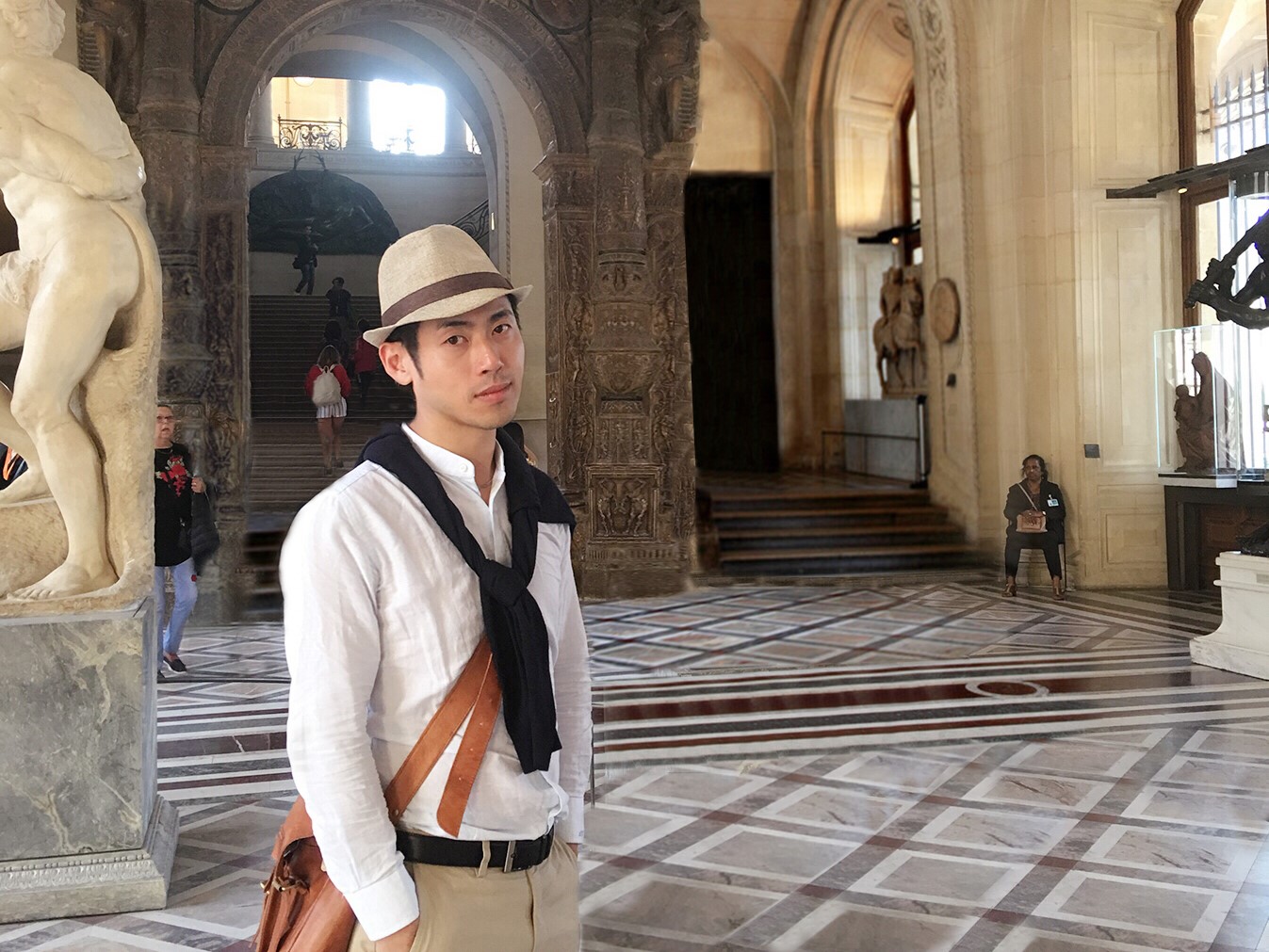
克罗齐曾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究竟如何看待当下,葛亮给出的答案是——一切有关于现代文明的呈现,都需要建基在对于传统的体认和反刍,乃至于一些相对来说比较深层次的体悟之上。
“两者的衔接,从无形之中构建了我写作的格局感和对深度和广度的把握。”敏感于现代文明的沈从文是葛亮推崇的作家,“我在小说中也非常重视这一点,现代文明必须要经过历史积淀的演绎和检验,才能恰如其分地展现内在的的生命力和延展性。”
历史的厚重在他笔尖倾泻,平和的、缓慢的,唤醒读者对过去积蓄已久的眷恋。
走过每一幢钟楼,眺望每一座码头,二十年过去,摩登都市香港已然成了葛亮的“第二故乡”。面临着传统建筑在这座城市的逐渐消亡,葛亮对市民们“一石激起千重浪”的心态深有感触。“前些年有一个概念叫哈布瓦赫的集体回忆。这些建筑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香港人在内心中间对自己城市来自于历史根基的一种重视跟强调。”
在与年轻一代的交流中,他也总是试图去寻找和厘清有关这座城市的历史因由。“长洲的太平清醮”“猴王诞”这些古老的节庆学生们都爱听。“加强代际之间的对话,其实也是共同建设一座城市完整的文化轮廓的一个必由之路。我们经常讲,你只有了解了自己的过去,才能够理清当下和展望未来。”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