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活跃在影视剧里的年轻人虽赚得不多,生活却光鲜亮丽。比如电视剧《欢乐颂》中,刚刚毕业的年轻女孩儿关雎尔和邱莹莹可以在上海徐家汇的高层小区里各自租住一个单间;再比如情景喜剧《爱情公寓》里,一群不到30岁的年轻人可以住在奢侈的套房公寓里。但事实上呢?现实中的青年人在出租房里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是不是有一扇能眺望陆家嘴夜景的落地窗?是不是从来不用和房东打交道,或为房租和搬家烦恼?
在当代中国,我们似乎极少读到写生活在出租房里的年轻人的文学作品。这种实际生活与文学描写之间的落差,就如同杨时旸在最近出版的小说《杨天乐买房记》中所写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经验缺少参照系,父辈的经验已经失效,“我们”也不知道未来如何——然而,少有作家愿意书写青年人在一线城市漂流的生活,“或许,相较于上一辈与历史、政治等宏大议题相缠绕的苦难而言,我们这一辈流于生活和生存层面的焦虑都显得不值一提……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杨天乐买房记》中,居无定所的困窘与焦虑四处弥漫。故事的主角杨天乐大学毕业,怀抱着留在一线城市奋斗的期望,在北京找到了一份专业相关的工作,也和爱人成家了,一切都像是渐渐步入正轨——除了他们在工作八年之后,仍然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在这些年里,他们眼睁睁看着小区房价从一万涨到了六万,也终于觉得人们将买房比喻“上车”是无比精妙的,因为房价就是高速行驶的列车,即便在狂奔的列车之后狼狈猛追,也只能看着车越走越远。

杨天乐的故事,大概也是无数正在大城市漂泊的年轻人的写照。为了更好地阐明“出租房里的年轻人”这个主题,我们还选取了另外几篇小说与之进行对比,或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回答跟租房相关的一些更具体的问题——出租房里的年轻人与房东的关系好吗?他们因搬家而苦恼吗?他们与同一屋檐下的合租者保持着怎样的关系?
厌恶房东,杀死房东,成为房东
没有“上车”、寄人篱下,不仅仅是出租房里的年轻人在哪儿睡觉、吃饭、看电视的问题,更关乎他们的私人生活和亲密关系。在《杨天乐买房记》里,因为没有自己的房子,年轻的爱人不敢生孩子——他们连一张自己的床都没有,只能睡在一张不知道被多少人睡过、渗透了不知多少人体液的床上;他们要小心在单人床上的动作和声响,最好不让住在隔壁的室友听到,然而床架的“吱呀”作响又不由得他们控制。这不禁令人想到英国作家戴维·洛奇在小说《好工作》里对伦敦房价飙升的吐槽,“现在,是房产支配性欲了。”

在文学作品中,性欲似乎只是房产支配的所有事项中的最微不足道的部分。而事实上,更重要的是,作为房产所有者的房东与房客之间的关系,并不如合同上所写的那么平等——房东定期的清洁检视、谆谆的教导以及突然造访,往往一再打断租户“安居乐业”生活的幻象。杨天乐自己也曾去宜家买花架、去姚家园买花草,试图为自己栖身的房子增加那么一点儿情趣,但房东只要想过来安放个柜子,他们就得让自己好不容易构建出来的“生活品位”让位。
租客觉得自己的尊严和情趣被房东的不懂规矩、不知界线破坏了,于是不止一次出现对房东的腹诽。我们可以在《杨天乐买房记》中看到,对于“好运气”买了房的房东,作为租房者的主人公心怀着一种几乎充满讽刺的羡慕之情。对于其中一位房东,他们想,“俩人都是七零后,赶上了好时候……不知道他们是先知先觉,还是运气好,如今也算身价不菲。自己现在一个月一万块钱的工资,无论如何也追不上了。”对于另一位职业是教师的房东,租户的评价几乎是完全彻底的讽刺,“对于规训他人有着近乎强迫症似的迷恋。或许在这个世界上,他能够规训的人并不多,只有自己的学生和房客。”此外,房东的审美品位、吝啬态度等等无不压迫着出租房里的年轻人,杨时旸在小说中讲到,有些北京房东把自己所有的破烂家具当古董般珍惜,不允许租客扔掉任何一件垃圾。
《杨天乐买房记》并不是唯一一部对房东持有“恶感”的小说。在以亚洲最大的经济适用住宅小区为题材的小说《日落天通苑》中,作者王云超也将外地人与北京人视为两个彼此对立的群体。他写道,北京人买了天通苑的房子,也不会过来住,只会“驱车”前来找中介索要银子;他将这个讨要租金的北京人形象写得有些过火,“他们昂起头颅,叉起腰肢,仿佛降临八大胡同的亲王,一面清点老鸨递来的分红,一面又不齿烟花柳巷的咸腥。”
以上对于房东的鄙视和敌意,在张敦的《杀死房东老太太》(后改名为《带我去戈壁》)里,演化成了更加激烈的愤怒,最终甚至激化为一场谋杀。这篇故事,据张敦在以前的采访中说,取材自他的真实经历。像上文提到的杨天乐一样,“我”本人也是大学毕业,从河北到北京做“北漂”,也选择在北京东四环到东五环之间租房,他和女友的房东是一位老太太,比杨天乐更糟糕的是,他们需要与老太太共用一个卫生间和厨房。“我”厌恶房东的理由与杨天乐基本相同——老太太霸道地占据了厨房的绝大部分空间,对于房间的使用法则有着绝对的权威——如果头发掉在了洗手池里,尿液滴到了马桶边沿,她就会前来敲“我”的房门劈头盖脸一顿训斥,“我”的表现唯唯诺诺,“简直不是个男人。”
与杨天乐对房东的抱怨与讽刺不同,《杀死房东老太太》的现实性显然沾染着疯狂幻想的色彩。“我”终于忍无可忍,联合女友把老太太杀死,并将她埋在了别人的坟里。更讽刺的是,当张敦写这个故事的时候,现实生活中的老太太就在隔壁房间,并不知道她的租客已经用纸和笔在文学世界里完成了一次对她的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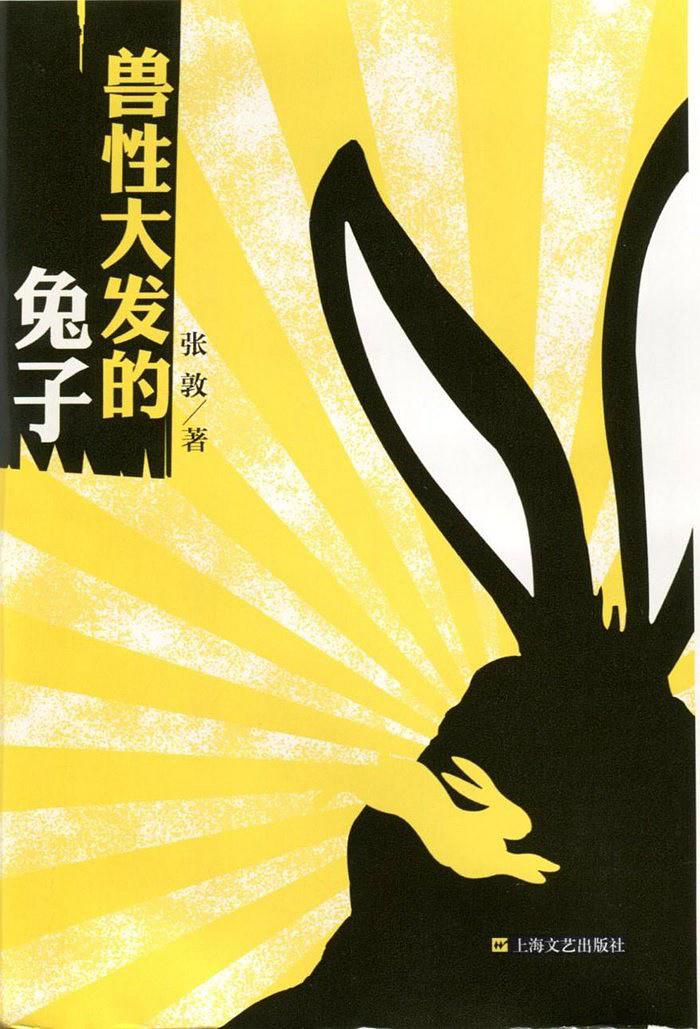
张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年
我们可以发现,为了弥补租房时受伤的尊严,房客们将房东作为心理层面的攻击对象,或者贬损房东,将他们形容为市侩的、自私的、没有边界感的,或者在想象中将房东“一劳永逸”地干掉,使他/她受到教训。而令这种房东-房客关系更加微妙的是,在《杨天乐买房记》里,当杨天乐夫妇决定买房、去探看别家的房子时,也成为了僭越别人居住空间的人,租户也需要由着他们仔细检阅私密的生活——家有几口人、有哪些生活习惯,尽收眼底。其中有一家看起来已经在尽力让自己的租房生活“中产化”,小两口养着狗,有一家宜家的木板桌子,桌子上还有两杯红酒。
“房子是租来的,一切就都是租来的。”当杨天乐检视别人的房子时,想到的并不是他们的生活还算体面,而是“这对小两口很快就顾不上喝红酒了,因为房子快要被卖了,他们马上就得搬家滚蛋”。从被别人撵滚蛋到期待别人滚蛋,杨天乐的这种转变恰恰体现出,房东遭到房客痛恨并不如这几篇小说所写——因他们刁钻刻薄、没有品位、贪婪不已或是自私自利——杨天乐也受过高等教育,还会去宜家购物装点居住空间,但与他自己的房东一样,他也在想象租客们滚蛋搬家的狼狈情景。所以,或许只能说,有了“房票”,一个人的信心和地位就都不同往日了,因此也就可以支配别人的性欲、指点别人的生活了。
搬家的烦恼:鸡零狗碎与阶级意识
房东指点与支配房客的最重要、最绝对的形式之一,就是告诉对方“你应该搬家了”。在一年间,杨天乐这对北漂夫妻“被迫”搬了四次家,情况各种各样,有时候是因为房东心血来潮要买房,有时又因房东婆媳夫妻突然反目。总之,房东一家的生活状况、亲属关系和经济状况出现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与打乱租客的全盘生活。相对于收拾东西和寻找新房,杨天乐觉得,更难以忍受的是一种被驱逐的屈辱、一种陷入鸡零狗碎的难堪,而当这种感觉直接撞上“在一线城市生根发芽”的宏伟愿望,前者可以轻松地将后者击溃。
《杨天乐买房记》中有一个场景是这样的:在一次搬家中,杨天乐夫妇一起提着编织袋走在天桥上,袋子因为质量差撕出一个口子,里面的锅碗瓢盆砸了一地,有一根筷子还砸到了过路汽车的车顶上,妻子蹲下拾捡筷子,突然哭了起来,丈夫上前安慰,妻子却哭得更厉害了。这只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城市生活片段,妻子情绪失控,丈夫安慰无效。然而,他们彼此都清楚,此时当众撕扯开来、落在地上、跌在车顶、让过路人避之不及的,并不仅仅是编织袋里的锅碗瓢盆,而是他们没有办法收拾得体的生活。

杨时旸 著
四川文艺出版社·新经典文化 2018-10
比起拾掇杂物和搬家迁徙,让租房的年轻人更加难以面对甚至难以启齿的,可能是再次入住陌生空间,无意间闯进别人生活时窥探到的不该窥探的局面。杨天乐为找房子,曾走进一间改造过的暗娼之家,“整个房顶就是一面镜子,地面被改造成了榻榻米,门口有一个摔坏了的小型粉色霓虹灯。”令他和在场的中介感到尴尬不安的是,他打开了衣柜抽屉,里面躺着两张光盘,光盘上有一个裸露的女人——这是一个富于寓意的时刻,他与这套房子的销魂过往直接照面,比想象自己正在睡的床沾染过多少人的气息,更加具有冲击力。美国学者马修·戴斯蒙德讲述穷人被驱逐的非虚构作品《扫地出门》里也有类似的场景,有一个工人专门负责清洁“驱逐”之后的房间,他对于其中一户“驱逐之家”印象尤其深刻:这一家的沙发包围着一个家庭舞台,舞台中间矗立着一根脱衣舞钢管,这显然是一个用于拍摄色情影片的秘密基地。
大城市漂泊者的搬家苦恼,并不是当下这个时代独有的。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作家萧乾因为自己养的猫跑到房东太太屋里拉屎而不得不搬家——房东太太对他怒吼道:要么扔猫,要么搬家。历史学者胡悦晗在《生活的逻辑》中讲述了民国知识人的不同搬家状况,并将搬家与文人所处的阶级挂钩。他写道,在上海,许多文人开始都是暂居一个地方,待安定下来,再找到合适的地方居住,但不同阶层的文人的搬家情况是不同的:有些文人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自然也改善了住房条件,比如林语堂从西式公寓搬到了江苏路的花园洋房;而长期处于社会中下层的青年知识人,只能在从一个破地方换到另一个破地方,比如作家唐弢几年之内换了四处房子,“迁出了没有扶梯的阁楼,搬进不见天日的灶披,在洋场上飘来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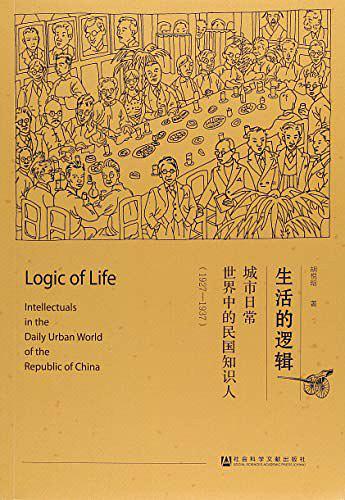
胡悦晗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对于六年内搬了三次家的钱歌川来说,搬家是一个阶级意识觉醒的时刻。他写道,搬家需要金钱,需要时间,还需要人手——这三者对于阔人来说是不缺的,但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恰好是最缺乏的。钱歌川不无讽刺地说,适合搬家的人偏偏不需要搬家,不适合搬家的人反倒要天天搬家。其实,钱歌川从日本留学归来,在中华书局担任编辑,经济条件并不算差。剧作家宋春舫也在《论语》里一篇名为《从“家”忽然想到搬家》的文章中,颇有阶级意识地将自己的状况与有钱人进行对比而写道,那些有钱的公子哥儿是不知道搬家是什么味道的,第一他们有产业,第二他们不会出现欠租的情况。这一点与视房东租户为对立阶层的杨天乐和“杀死房东”的“我”,颇有相似之处。
合租情谊:微弱的居住认同,新型的人际关系
《生活的逻辑》一书中写道,搬家意味着从熟悉到陌生的生活场景的变化,个体不得不随着空间场所的不断变化而被动适应,而这种变化“频繁地迁居消弭了居住者微弱的居住区认同感”。如钱歌川所说,“我们搬一次家,至少得两百块钱,而搬动了的东西,也得一两个月才能重上轨道,清理出个头绪来了。等到你住了相当的时候,周围的一切都熟习而习惯了,你颇能感着安居之乐,总之,你对于这个环境已经完全适合了,然而到了这时你又得预备搬家。”
在《杨天乐买房记》里,杨天乐夫妇也埋怨道,刚刚熟悉起这个地方,又不得不要离开了。这对夫妇在搬进新房子之后,会通过种种第一次的经验而积累起熟悉感和认同感来:“第一次在这里做饭、做爱、看电影、买一盆花、听到邻居吵架、听到楼下小公园的广场舞舞曲,逐渐地熟悉起来。”而令人无奈的是,“当一切都变得不能再熟悉时,就意味着要搬家了。”搬家次数多了,在逛街和旅行时他们已不愿再添置有趣的物件,因为这会造成搬家的负担。毕竟,“睡觉、做饭、洗澡、上网”才是房子的基本功能,相应地,“睡觉、做饭、洗澡、上网”之外的情感——比如熟悉和认同——都显得负累,因此需要果断地舍弃和利索地剥离。但是,人需要的住所远远不止是为了“睡觉、做饭、洗澡、上网”。由于欠缺居住的认同感,融入城市便也十分困难,在跟农民工交流时,杨天乐甚至会羡慕对方,因为对方根本没想过在城市扎根,因此也不会体会到“在而不属于”的侨居漂泊感。
与此同时,在城市中频繁地迁徙,也让租房的年轻人与以往不会接触的三教九流形成了新鲜的碰撞。在一些“北漂”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从城市合租房里生长出的新型人际关系。在王云超的《日落天通苑》中,“我”和十个人合住在天通苑一间九十平米的两居室里,这些人分别居住在隔断、次卧和主卧里,住户人群的分布非常复杂:既有视觉系的杀马特、KTV公主和她男友,也有房产销售员和他的男友,甚至还有一个男人的“小三”。比起《杨天乐买房记》里的整租与《杀死房东老太太》里和房东合住的方式,这一篇的租住生态最显恶劣。

王云超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年
在这群人中,“我”是唯一过着朝九晚五生活的人,相对于规矩的“我”,他们的生活显得混乱而充满“活力”——日夜不分,彻夜party。房间隔音很差,所以“我”的耳边几乎是一曲由喘息、呻吟和木床嘎吱声合成的奏鸣曲。就是在这样逼仄的生活情境中,“我”与这些在别处毫无交集的人群搭起了伙,除了一起聊家常,还出于共同利益一起抵制天通苑的黑中介——租户之一包工头甚至号召“我”把黑中介给砸了;这群租户需要在内部进行分工,有个女人说,“你们这些老爷们儿到时候冲到前面,护着咱们家女的。”
在这个战斗的时刻,偶然地被抛掷到同一屋檐下的、完全不相干的人们,竟然团结成了一家人。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建立于“同仇敌忾”关系之上的合租情谊,就在“我”与这群人交往加深的过程中,“我”的朋友劝“我”搬家,理由是,“我”这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怎么能和一群没有受过教育的“盲流”合租?而“我”的反应是,“受过高等教育怎么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就一定是好人?”

与那些一团模糊地展现青年精彩都市生活的电视剧——比如《欢乐颂》或者《爱情公寓》——相比,《日落天通苑》里的生活似乎是大城市生活的“暗面”了。然而这“暗面”并非对于“合租”或“群租”脏乱差印象甚至道德败坏的迎合,相反,小说不仅如实描述了租房比买房低一等、群租比合租更低、次卧低于主卧、隔断低于次卧、暗隔又低于明隔的生存状况,也充满想象力地展现了不同背景的人们搭伙吃饭、谈天说地的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景象。 受过高等教育的“我”,在漂泊无定的合租生活中,寻找了一丝亲切与认同。
更重要的是,这份亲切与认同与传统乡土社会的地缘或血缘异质,也与人们受教育背景、职业背景和社会地位无关,而只是来自同一屋檐下的朝夕相处。就像租房被认为是过渡的居住一样,合租的情谊也更像是一种处于过渡时期的感情,而谁又能否认这感情的真切呢?尽管明天去留无定,至少他们此时此刻互相取暖、彼此慰藉,给予他人脚下这座城市所给予不了的归属感——这一重飘渺的意义,已远远超越了三尺栖身之地“睡觉、做饭、洗澡、上网”的基本涵义。
……………………………………
欢迎你来微博找我们,请点这里。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