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在燃烧。沸水在翻腾。白宫里坐着一个格外残忍的人物,鼓舞着世界各地的反动势力。政治中间派里聪明的男男女女们手足无措。(既有规范被颠覆,礼节已是过去式,事实查验似乎未能发挥预期的效果)正当性的丧失搅乱了他们的方向感,也击碎了他们试图将业已破碎的政治重新粘结起来的美梦。起先他们还宁可不去反思为何自己的政治被搞得一团糟。
与此同时,工人阶级生活的漫长危机仍在继续。约有80%的美国人靠薪水过活。将近一半的人竟然承担不起区区400美元的开销。一边是数十年不见起色的薪酬,另一边则是美国住房、健保和教育成本的疯涨,这已经让有尊严的生活沦为了一种奢侈。然而这还不足以刻画危机的深重。问题不是要生活得如何体面,而是生活本身日益成为一件难事。英美两国的预期寿命均有所下滑。气候变化正在杀死加州和波多黎各的居民。紧缩(austerity)则让利物浦和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的民生难以为继。
如果这番话听起来很阴暗,那也理应如此。我们正朝一个崩坏的未来狂奔。不过那也并非不可避免——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设法降低它来临的可能性。在如今这一万马齐喑的时刻,这无疑是一缕亮光: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自1970年代后期以来左派尤其是社会主义业已式微的国家,左派尤其是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左派的战斗性和动员力正呈现出复兴趋势。
英美社会主义者不再是永远的输家了。有时他们甚至还能取胜。他们正在建立机构、竞选公职、组织工会、参与直接的行动和互助。他们一反右派的虚无主义和中间派的绥靖主义,向一个更宜人的未来迈进,一个工人阶级及其诸多变体——青年、移民和酷儿——能够安居乐业的未来。
科尔宾和桑德斯将一度边缘的理念推向了主流——他们也许很快就能取得将之付诸实践的权力。
英美的一系列运动不是同质化的。它们由多条各不相同的脉络构成,形塑它们的则是无尽的论辩。社会主义是个复杂且有内在张力的传统,这一点无论在1918年、1968年还是在2018年的今天都丝毫没有改变。当然,有两个人格外显眼:杰里米·科尔宾和伯尼·桑德斯。两人之间差异虽大,但都属于社会主义传统——科尔宾来自英国工党中偏左的本恩派(Bennite),桑德斯则从青年社会主义联盟(Young People's Socialist League)起家。依照彼得·弗雷瑟(Peter Frase)的说法,两人都是“幸存者”:他们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社会主义最后的一波高潮与当今之间建立起了鲜活的联系,在撒切尔主义、里根主义、布莱尔主义和克林顿主义当道的漫漫长夜里一直坚持社会主义信仰。此外两人也是各自国家里社会主义复兴的弄潮儿。虽然眼下的社会主义时刻肯定不局限于这两人——实际上还包括了不少对两人无感乃至于有敌意的元素——但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前景而言仍然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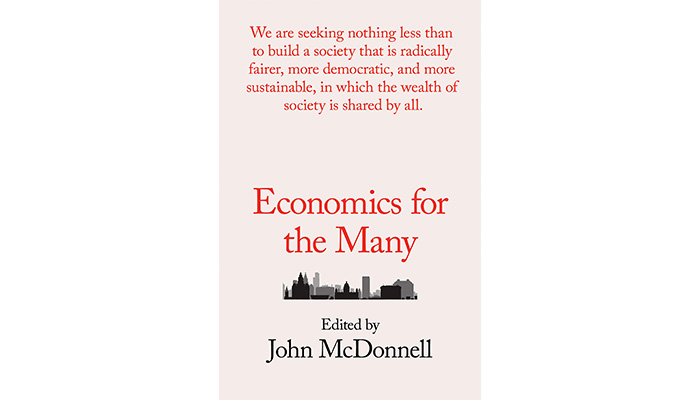
有两本新书分别就二人的谋划提出了各自的洞见。一本是Verso出版社的文集《为多数人说话的经济学》(Economics for the Many),由科尔宾的影子内阁大臣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all)主编,该书概述了围绕科尔宾主义展开的新经济思想,并简要阐发了未来工党政府将会推行的一系列政策。桑德斯的《我们自此出发:抗争的两年》(Where We Go from Here: Two Years inthe Resistance)由Biteback出版社负责发行,书中回忆了2016年以来的政治斗争,勾勒了一幅在特朗普治下推动进步事业的路线图。
不管你对科尔宾和桑德斯有何看法,他们所引导和激发的力量都正处于一个有趣的发展阶段:不同于最初的那波反叛,某些一度边缘化的理念已被他们成功带回到主流视野当中,但两人也尚未掌握足以将理念付诸实践的权力。这或许只是时间问题。
即便有转瞬即逝的风险,科尔宾主义也依旧是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当科尔宾于2015年成功夺得工党党魁之位时,主流的共识是他坚持不了多久。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托尼·布莱尔当时还警告称工党将“面临毁灭”。三年后,科尔宾仍然稳坐工党一把手,党的发展势头也相当良好。科尔宾复兴了工党,这离毁灭它差了十万八千里。党员数目剧增:新涌入的成员高达35万余人,令党的规模几乎翻了三倍。工党在2017年大选中的得票率创下了1945年以来的新高,对此,数十年来最激进的党纲功不可没。
科尔宾主义彰显了毫不含糊的左翼规划在政治上的可行性,它直接抨击了紧缩的逻辑以及金融资本的霸权。在笔者写作此文的时候,英国的二次退欧公投正好搁浅,特蕾莎·梅的领导地位面临挑战,尚不清楚近期会有何种发展。不过,假如工党能赢得下次大选,当权后的科尔宾又会怎样施展拳脚?
《为多数人说话的经济学》提供了一些可用于回答此问题的素材。书中的16篇论文涵盖了相当多元的主题,从贸易到税收再到科技。它们提出了多条思考经济问题的门径,并提出了一系列的重构方案。概言之,其中的共同线索是马丁·奥奈尔(Martin O’Neill)和乔伊·吉南(JoeGuinan)所称的工党的“制度性转向”:这一雄心比微调既有制度安排走得更远,试图构建一整套新制度。科尔宾主义希望能像当年的撒切尔主义一般,彻底改变英国的政治-经济结构。
这一转型将会有何等样貌?以《为多数人说话的经济学》来判断,其预期结果是一个高薪、高生产力的经济体,以生产性而非金融领域为导向。公共银行、公共投资和公共所有制将会与大规模的合作组织一道,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积极的产业政策将会透过“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来引领向后碳(post-carbon)社会的转型,同时扩大健保、母婴及教育开支,以维系一个强健的社会供给系统(system of social provision)。

这一安排仍然没有脱出资本主义的藩篱,但其基于一种新型社会民主解决方案的再平衡有助于英国社会朝向更为人道和平等主义的方向发展。资本也将会张牙舞爪地遏制这样的安排。即便科尔宾主义没有与资本主义决裂,但其议程已包含了对资本积累过程的实质性社会控制。如果以史为鉴,不难想见资本将会尝试或至少威胁要以毁掉整个经济体的方式来把这一议程扼杀于襁褓之中:不借贷、不投资或选择撤出这个国家。
麦克唐纳意识到了这一危险,这迫使他开始就各种可能的情况展开沙盘推演。书中的许多作者也同样有所意识:其中西蒙·芮恩-刘易斯(Simon Wren-Lewis)就解释了工党的“财政可信性规则”(fiscalcredibility rule),它透过承诺不超支来安抚金融市场。其它人提出的对策则主张:以小额资本来对抗大资本,以生产性资本来反制金融资本。
但这一切充其量不过是短期的战术性动作,仅能争得些许喘息空间,无法逆转深层次的发展进程。惟一能捍卫新社会民主方案的力量也就是捍卫最后一人的力量: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动员。战后的福利国家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千百万人民希望和要求改革。而关键在于,战后的长期经济扩张也意味着实现前述承诺所需的资金可以透过促进增长而非再分配来取得。
今天的经济增长率是相对低迷的。这无疑要求更大的动员力度。对此,当今的社会民主制只得对资本所拥有的那块蛋糕动刀,而非做大蛋糕本身。这就让阶级斗争的问题变得尤其重要——奇怪的是《为多数人说话的经济学》竟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本颇为有趣的书在观念上不乏闪光点,而这也证明了科尔宾主义在学识根底上的厚重。问题在于不能只靠观念,它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事。也许会有人怀疑:科尔宾主义的命运或将更多地取决于究竟有多少人愿意在其社群和工作场所中参与到破坏性的行动中来,以捍卫这一计划并自下而上地使其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赢得一场大选只是第一步。“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曾写道,“下一步如何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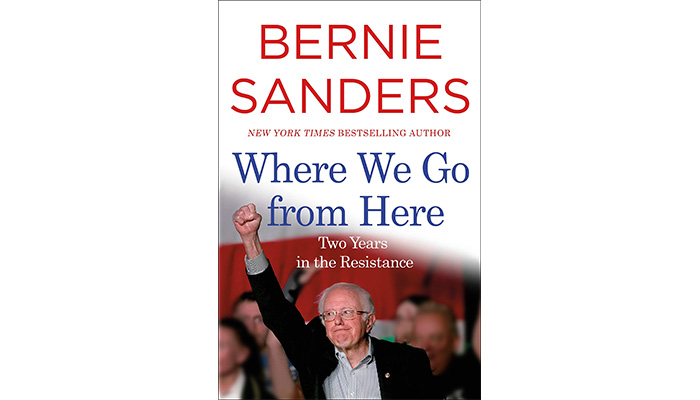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各种力量的均势看起来就不那么有利了。没有人对资本外逃做沙盘推演。美国左派比过去几十年来更具自信和战斗性,但其敌人也更强大了。在《我们自此出发》中,桑德斯描述了他在特朗普就职日所感受到的愤怒。他想要处理诸如健保、不平等和气候变迁等“不计其数的问题”。然而,在特朗普治下,他明白自己不得不采取另一种姿态:践行一种“防御性的模式,以避免坏状况滑向更坏的方向”。
在特朗普时代,左派必然处于守势。但要紧的是采取正确的守势。2016年大选以来,反特朗普主义涌现出两大支派。其中一派想要把钟摆拨正,以回归原状。它信任规范、两党合作和宪政主义。这是自由主义中间派和民主党领导层的立场。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民主党于新近的中期选举中重夺众议院后所发表的胜选演说中对此有详述,当时她立誓要重建“宪法对特朗普政府的制约与平衡”。
与几十年来的颓势相比,美国左派正变得更自信且更有战斗性,但其敌人也更为强大。
比较而言,另一派反特朗普主义者则推崇一种超越程序主义的政治。他们试图构建新的进步主义多数,既反对特朗普主义,又与民主党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亲商界(business-friendly)中间派划清界限。桑德斯是这一愿景的主要推手,《我们自此出发》一书即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不懈努力。透过一连串短小精悍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全国范围内四处奔波,于各地市政厅组织集会的历程。
民主党内有一批头面人物,他们似乎被目前的政治形势冲昏了头脑,产生了一种精神错乱。他们如共识动物一般渴望着妥协。他们需要相信持反特朗普立场的共和党人的存在,无视这种人根本就不存在的事实。在右派势力远超自身的情况下,他们还在设法寻求和维系中间立场。
桑德斯跟这群人道不同不相为谋。他的政治路线根植于对抗而非共识,这令他比起大部分民主党同仁而言更切合于当下的处境。事实上,对抗就是他这本书的主题——不是两党之间的对抗,而是不折不扣的阶级之间的对抗。《我们自此出发》一书充满了阶级斗争气息。在第一页上,桑德斯就将其目标指向“亿万富翁阶层及其豢养的政客们”,这是他反复强调的主题。但凡听过他演说的人都不会对此大惊小怪,但作为一名一流的美国政治家——这个国家里的当红人物之一——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还是略有些令人震撼的。这或许是他身上最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地方。他提醒我们说,要紧的不只是贫富差距:富人之富裕与穷人之贫穷之间有因果关系。富人压低了薪酬,抬高了健保成本,没完没了地打仗和杀戮,还对波多黎各进行剥削。
桑德斯表示,解决之道在于对他们发起一场“政治革命”。他的意思是说,要发动大量通常被排除在选举政治之外的人群——尤其是青年人、有色人种和工人阶级——并组织他们从事草根运动,要求打击盗贼统治(plutocracy),推动更广泛的民主。他的愿景是多数主义的。“如今美国人民得到的并不是他们想要的东西。”他写道,同时还提到了支持诸如全民健保(Medicare for All)等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广泛呼声。
根据桑德斯的回忆,当他在2016年初选中提出这些政策时,它们被打上了诸如“极端”和“不现实”之类的标签。现在它们都变成了主流,在胜选的民主党人当中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它们。他提到,自己在两年前曾提出过提高最低工资的立法案。当时只有五个人共同参与提案。当他在2017年4月再度尝试时,支持的参议员达到了22人,其中包括民主党领导层中的大多数。
显然,桑德斯赢得了一部分战斗。但还有许多仗要打。他在某些方面成功地令民主党左倾化了,且激励了诸如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特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这样的新一代挑战者。但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民主党仍然被中间派把持着,这群人享有结构性的优势,极难乃至于根本不可能撼动其统治地位。民主党极其善于对社会运动进行分化和瓦解,这成功地防止了一切试图将其重构为真正意义上的左派政党的努力。
另一道难关则是:共和党人。桑德斯正确地指出,特朗普的党不能反映大多数美国人的观点。事实上,共和党人自己似乎也明白这一点:他们的权力依赖于抬高投票门槛、有偏向的选区划分以及美国政治体制的极端反多数(anti-majoritarian)架构。但就算共和党只代表少数人,这一少数也没有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中期选举中投票给共和党的人大约有4700万,共和党选民也热爱特朗普——这一群体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大约在90%左右。即便进步派人士成功地拓宽了投票权的范围并且提高了代议机构的代表性,这群特朗普的支持者仍不会消亡,他们甚至可能会蜕化为一股更为凶险的势力。
要迎合知识分子的悲观情绪并不难,但更要紧的是发现希望之所在,并以此来为意志的乐观主义(optimism of the will)注入动力。而乐观主义的最佳基础说到底正是我们眼下处境的奇特性——它奇特到足以让两个老社会主义者在英国和美国政治中走上前台。历史中会有一些这样的契机,各种元素散落开来,又以全新且出人意料的形式重新组合在一起。事态发展就此变得不可预期。时间的流逝并非平滑,而是有跳跃和断裂的。另一个世界因而变得可能,即便没有担保可言。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