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时,有一小群医生相聚于西雅图的某间会议室,探讨如何更好地帮助人们求死。其中有一些医生工作在医学助死(medical aid-in-dying)的第一线——亦即为绝症病人提供某种结束自身生命的方式。他们之所以来参会,是因为助死运动(aid-in-dying movement)当时碰上了麻烦。两种病人常用的致死性药物要么是突然买不到了,要么就贵得让人望而却步。不少医生都试过某种替代品,但有少部分病人反映称效果不太好。
这群在西雅图开会的医生们希望能找到一种不同的药物。但助死的实际操作过程——该政策饱受争议,且在美国大多数州仍是非法的——与其它的医学领域迥然不同。“帮助人们延年益寿的经验和方法很多,但怎么帮他们死却没有什么先例可循。”与会者、美国助死医生的热门人选之一特里·罗(Terry Law)说道。
目前有7个州——包括夏威夷在内,相关法律已于1月1日生效——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允许医生为合格的、精神正常且患有不治之症的病人开具致死性处方。2014年,一个名叫布里塔尼·梅纳德(Brittany Maynard)的癌症患者曾专程前往法律允许助死的俄勒冈州并成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此事旋即获得了广泛的舆论关注,助死实践也就此在全国层面上获得了新一波舆论支持。
但公众对相关法律依旧有着深刻的争论,医学共同体内部亦复如是。目前没有监管助死的医学界团体,也没有资助相关研究的政府委员会。在助死合法的州里,州政府会就哪类病人才算是合格提供一些导引,但具体开什么药则没有规定。“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具体如何实施相关的流程,也没有人来监管其是否能以安全的方式进行,更别说年报或者字面意义上的年度听证之类的东西了。”反对助死合法化的姑息治疗(palliative-care)医生劳拉·佩屈罗(Laura Petrillo)说。
参与2016年聚会的这群人所发起的研究,在后来得出了美国使用范围最为广泛的助死药物的配方。但这群医生的工作乃是在传统科学领域的边缘地带展开的。尽管他们在出发点上是坚持操守的,但此类药物的研发及运用目前仍是一个灰色领域。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专精于助死的医生朗尼·沙沃森(Lonny Shavelson)认为,从表面上看,草拟一份加速死亡的流程表并不算复杂。他还说,当他向病人解释说帮助他们赴死需要花上一个小时乃至更长的时间时,病人们通常会很震惊。他们向他表示,“我杀掉自己的狗才只花10分钟而已。”沙沃森回忆道。

但兽医是可以对宠物施行致死注射的。在美国,助死药物则需要病人亲自服下。华盛顿州的第一部助死法草案曾允许医生以注射方式给药,但未获通过。2008年,经过修正后的助死法通过了投票,其中有一项补充规定,要求病人必须自行服下药物,以免出现家人强迫等意外情况。
多年来,有两种巴比妥类药物(barbiturates)被视为是加速绝症病人死亡的最好药物:司可巴比妥(secobarbital)以及戊巴比妥(pentobarbital)。这些药物痛苦少、见效快且价格相对低廉。但2015年以来,它们基本上就很难买到了。美国许多药厂不再生产获准专供人使用的戊巴比妥,在威朗制药(Valeant Pharmaceuticals,亦即如今的博士健康[Bausch Health])买下可巴比妥的生产制造权之后,其价格也翻倍了,几乎达到历史新高。好些年前,一份达到致命剂量的药物仅需200至300美元,如今其价格涨到了3500美元乃至于更高。
为帮助此后买不起药的病人,助死团队想了不少办法。在华盛顿,支持助死的组织“生命的终结·华盛顿”(End of Life Washington)曾向70余名病人开具过一种药物合剂,其中含有起镇静作用的水合氯醛(chloral hydrate)。“我们知道这会让你陷入昏睡,我们非常确定它可以让你们死掉。”该组织的医药总监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称,他们就是这样告知病人的。它确实有效,但偶尔也会遭逢不测:在极少数案例中,水合氯醛对病人的喉咙造成了严重的烧灼,反而在病人一心寻求解脱的时间点上引发了剧烈的疼痛。
“生命的终结”组织的成立,源自于探寻一种更佳解决方案的努力。伍德列举了另外3位跟该组织紧密相关的人物:主席特里·罗、前任医药总监汤姆·普雷斯顿(Tom Preston),最后是卡罗尔·帕罗特(Carol Parrot)。与罗类似,帕罗特是一名退休的麻醉学家,也是参与西雅图聚会及此后电话会议的、在美国称得上经验最为丰富的助死医生。另外三人分别为来自艾奥瓦州的毒理学家、兽医及药理学家。帕罗特说,这支团队秉持三大标准,他们希望能找到“一种药物:首先,能让病人入睡并保持其昏睡状态;其次,确保过程中没有痛苦;最后,保证病人一定能死去,且死亡时间最好能相对短一些”。另外,药物还必须便宜。他们设法把价位保持在每剂500美元。

医生们想起了一种治疟疾的药,此药在大剂量下有致命效果,但在某些病人身上会引发严重的肌肉抽搐。他们讨论到了复合型鸦片类药物芬太尼(fentanyl),但因此药刚上市不久、在安全性方面风评不佳而作罢。这样一来,团队决定使用复方制剂,最终敲定了高剂量的以下三类药物:吗啡、地西泮(diazepam)——其早期品名“安定”为人们所熟知——和普萘洛尔(propranolol),它是一种可以减缓心跳的受体阻断剂。这种复方制剂被冠以DMP这一代号。
接下来,该团队必须对药物进行测试,但他们仍然没法遵循标准的流程:没有政府批准的临床药物实验,当他们向病人开具混合型药物时,也没有伦理委员会的监管。医生们只能设法最大限度地保持小心谨慎。病人可以自行决定参加与否,在最开始的10次助死当中,帕罗特或罗将一直守在病床边,随时记录病人及其家人的反应。
头两例助死进行得较为平顺。但帕罗特称,第三位患有前列腺癌的病人花了18个小时才死去。在俄勒冈州,助死在20年前就已经合法化了,从服药到死亡所花费的平均时间是25分钟。帕罗特、伍德和罗均强调说,病人们一般会在5至10分钟之内进入无意识状态,因此不会被时间的拖延影响。但漫长的等待时间对家人和其它照料者而言是非常“扎心”的,在某些持续时间超过一天乃至更长的特例当中尤其如此。
帕罗特和罗终止了DMP方案的实验。这支非正式的研究团队再度碰头,但这次是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罗挖掘了一些文献,发现有一篇论文谈到了刻意过量服用心脏病药物地高辛(digoxin)的人群。团队将其加入了药方,以DDMP为之命名。
起先,帕罗特将服用这种新型药物合剂时应当遵循的规范一一告知病人。“有个人一口气吃掉了半杯百利牌爱尔兰冰淇淋,这是他的最爱,以这种方式服下了药,”她说,“他可能要过5到6个小时才会死去。”她怀疑是百利冰淇淋里的脂肪微粒阻碍了病人胃的清空。为此,研究者反复测试了许多遍,最后决定将剂量提高到帕罗特所称的“蓝鲸级别的剂量(blue-whale-sized doses)”,他们将这份修正过的药方取名为DDMP2。
药物不是助死的完美解决方案。伍德表示,司可巴比妥见效快,且是如今的病人依旧可以买得起的。与巴比妥类药物的情况相似,少数运用DDMP2的异常病例的死亡时间也会延长数小时乃至更多,而且这种合剂的口味极其苦涩。“你可以想象一下,感觉就好比把两大瓶阿司匹林碾碎了之后再往里面兑小半杯水或者橙汁。”帕罗特说。
但即便如此,DDMP2也仍是西雅图聚会中的医生们梦寐以求的低成本解决方案。2017年,司可巴比妥依旧是华盛顿州和俄勒冈州最常开具的助死药物,但科罗拉多州则更倾向于推荐DDMP2方案。这些药物一贯都能达到加速死亡的预期目的,帕罗特说:“它总是起作用的。百试百灵,效果显著。”
帕罗特和伍德追踪了病人的数据,且后来又有不少新发现。他们研究了那些花费较长时间才死去的病人的病史,找出了导致较长赴死时间的一系列风险因子:曾使用过极高剂量的止痛药,如芬太尼或吗啡;体格极为健壮;有消化道免疫力低下的症状。面对那些风险极大的病人,帕罗特或伍德有时会问他们是否要改用水合氯醛,某些病人服用该药之后喉咙会有强烈的灼烧感,不过他俩也称自己已与病人及其家人认真地就一系列潜在问题进行了讨论。
帕罗特和罗这些年来总共开具了大约300个致死性处方,并观察了药物在诸多病人身上的效果。他们俩都不是一开始就鼓吹助死的,而是在亲眼目睹了许多病人临终时的痛苦后才决定加入“生命的终结”这一组织的。罗回忆称,大约在8年前,曾经有人问她是否要为某位临终的女性开具致命性药物,一般的医生都会拒绝。她同意去看一看这名女性,去了之后才意识到:寻求助死的病人要找到合适的医生实在是太困难了。帕罗特说,她深受两位密友之死的影响,这两人都曾要求她加速其死亡,但却因为助死在其所居住的州违法而被迫作罢。她痛感对朋友爱莫能助,于退休后不久自愿成为了一名助死医生。
绝大部分医疗界专业人士都未曾参与过助死。一些医生的关切点在于,“希波克拉底誓言”禁止刻意助人赴死,或有时助死的要求源自某些原本可以治好的痛苦或抑郁症。另一些人则担心,允许以医学手段帮助绝症病人赴死,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对社会将会有不好的影响。美国医学会(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仍以官方名义对助死表示反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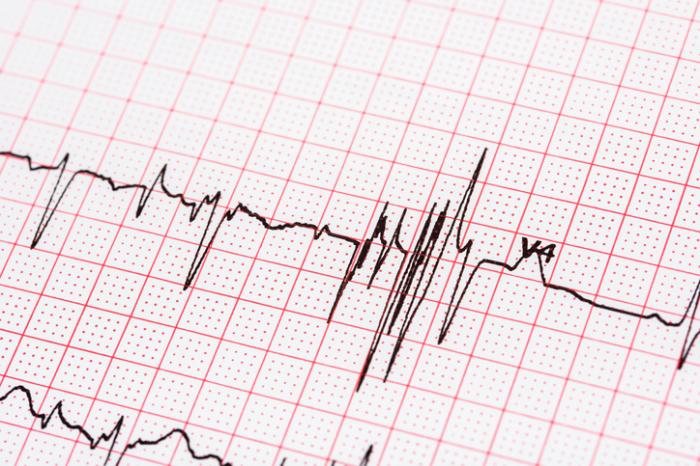
科罗拉多大学“生命伦理学与人文研究中心”负责人马修·怀尼亚(Matthew Wynia)表示,在缺乏来自专业共同体中的其它同行及社会上大部分人的支持的情况下,助死研究方法并不符合好的医学研究的标准。没有标准流程可言,没有标准化的数据收集渠道,也没有独立的团体来监督数据和安全性——这一切都旨在保护病人以及确保研究的品质。
贝尔蒙特报告(Belmont Report)包含了联邦对以人类为主题的研究的一系列建议,怀尼亚指出,这份报告也认识到:有时对某些病人而言并不存在令人满意的选项。在这些罕见案例里,一名医生或许想要尝试创新性的治疗手段,而其中某些手段又缺乏得到许可的研究流程。他进一步表示,即便这种操作是合法的,医生一般来说也应当避免贸然地将创新手段引入既有的实践,或对数量较多的病人做未获许可的研究。医用大麻也面临着一些类似的问题,它在好些州是合法的,但在联邦层面上仍是非法的。“在个体层面上找不到相应的解决办法,”怀尼亚说,“没有现成的答案可言。”
这就令诸如罗和帕罗特这样的研究者们陷入了困境。他们没有好的渠道来做研究以及交流研究中的心得。但他们曾亲眼目睹过一些将死之人的痛苦经验,且这些经验与选择助死的病人们的安然离世构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这样死去是毫不突兀的,”来自加州的医生沙沃森说道,“这些死法本身很可爱。”
沙沃森表示,在由自己助死的病人去世的那一天,他全天都呆在病床边。“气氛比你想象的要轻松一些。”他说。沙沃森将药物分为几个不同的部分,病人首先服下第一份药,接下来沙沃森会坐在病床边,大声朗读州法律所要求的报告里的那些问题。大约30分钟后,他会提问:“你是否准备好服用药物了?”他将药物混入鸡尾酒,病人一饮而尽。
“一般来说,他们在接受药物处理之前就变得一言不发了,”他说,“他们已经说完了他们想要在那时说的一切。”几分钟之内,病人通常就会一声不响地躺下来,两眼保持睁开。“接下来,他们会慢慢地、慢慢地闭上自己的眼睛。”
沙沃森每隔一小段时间就发问,“你还能听见吗?”起初,病人一直回答是,或者点头。在5到10分钟之内,他们就不再对提问有反应了。接着,沙沃森会小心翼翼地触摸一下病人的眼皮。“当人们尚未进入深度无意识状态时,他们的眼皮是会跳的。”他解释道。在10到15分钟之内,跳动反应也消失了,病人进入了深度昏迷状态。
透过心脏监视器,沙沃森将病人脉搏减弱、氧气水平降低等变化一一告诉照料者。“我们稍微等了一阵子,接下来我就说,‘啊,病人现在去世了。’”
沙沃森说,这群人乃是第一代有意识地凭借药物来加速自身死亡的病人。他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先驱者。“能坦然讲出‘我就在今天死’这样的话,不能不说是一项突破。”
(翻译:林达)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