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造就
人类的特殊之处在哪儿?
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说,有些人可能会拿对生的拇指和喉咙说事,但在很大程度上,人类的特殊之处在于创造力和产生新思路的能力。
身为斯坦福大学教授兼作家,伊格曼携手莱斯大学教授、作曲家安东尼·勃兰特(Anthony Brandt),撰写了《失控物种:人类创造力如何重塑世界》(The Runaway Species: How Human Creativity Remakes the World)。书中归纳并阐释了创造力的三个主要类别:变更(如建筑师弗兰克·盖里的建筑)、调和(如互联网混搭)以及打破(如毕加索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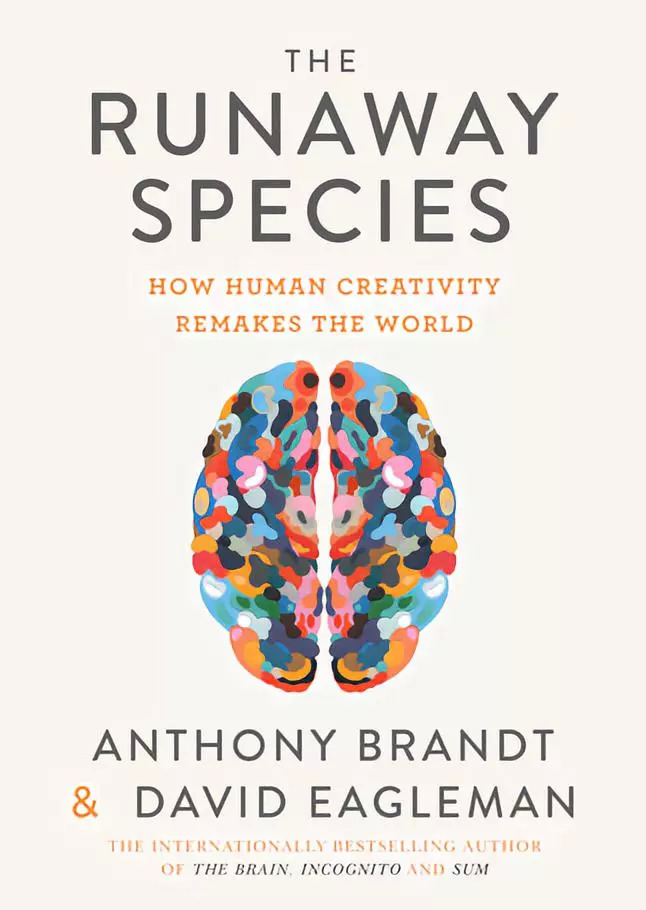
笔者于近日采访了伊格曼与勃兰特,探讨了这些过程的运作原理、创造力与创作质量的关系,以及他们个人最喜欢的创造力典范。
你们一位是神经科学家,一位是作曲家,是怎么开始合作的?
勃兰特:我和大卫相识于十多年前。我们成了朋友,过了几年,大卫在一场有关“音乐与心灵”的会议上发表演讲,主题是《创始之母》,从自己的母亲一直追溯到人类历史的发端,我据此创作了一首曲子。我们在医学中心的美食广场碰面,探讨跟曲子有关的思路。那顿午饭吃了三个小时,我们发现,我俩99%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最后,大卫说,我们应该一起写本书。
伊格曼:很不可思议的是,我们的视角完全不同,勃兰特感兴趣的是人脑,我感兴趣的是艺术,我们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之中,但我们的观点竟然不谋而合。我们不想写什么“实现创造力的几点建议”之类,因为人与人差异很大,对这个人管用的,对那个人未必管用。让我们感兴趣的是:创造力的根本是什么?是什么促使我们吸收观念,并催生出各种新的版本?
你们的论点是,我们在不断地“变更、调和与打破”。这三个手段是如何总结出来的?总结出这一结果的研究过程是怎样的?

作曲家安东尼·勃兰特(左一)
勃兰特:就是放眼各个不同的学科,总结我们已有的知识。这三项策略还是挺包罗万象的。比较振奋人心的是,在我们的演讲中,还没有人站出来说,“那XXX呢?”还没有人能提出这三项策略未能涵盖的点。在音乐中,“变更”就是变奏曲的中心思想之一,即对原作进行某种重构。“打破”的是音乐的主题,即作曲动机。“调和”可以是演奏多段旋律时的对位。我们发现,这些基本原则可以重新想象、重新应用,并无限制地自我实现。
大卫,这三项操作有没有神经学基础?
伊格曼:眼下,我们还不清楚人脑是如何做到这些的。当前未知的东西太多了。它不属于“输入信息是如何储存的”这类基本问题。它还有待更加完善的技术,以及未来的发现。
明白了。这三种手段可以分离吗?
勃兰特:我们的观点是,这三个策略始终交织在一起。它们并没有以单独的形式存在,但针对某一特定事物,你可以着重强调其中某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将它们分离出来。
伊格曼:这就像是在后台运行的基本认知“软件”。我们看重计算机的一点是,你扔一个文件进去,两年后再拿出来,它的0、1组合丝毫不差。但人脑的奇妙之处是,你把信息放进去,它就跟其他信息水乳交融、打破界限,这就使我们的创意之流源源不断。
这是人类的与众不同之处。当然,对生拇指和喉咙这些生理上的优势也不能忽略,但最根本的还是这种大规模的观念融合。我们不断地形成新想法。大部分的创意都不怎么样,但偶尔总有一个是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那品味呢?对很多东西,比如表演艺术,人们都会评价说,它“有创造力”但很烂。我们该如何评估?创造力的度该如何把握?有没有创造力“太过”的可能性?
勃兰特:我们将创造力描述为个人冲动与受众群体之间的对话。群体的判断会比较反复无常。因此判断之时切忌武断,尤其是针对孩子们,比如基于某项测试,对五岁孩子进行选拔这样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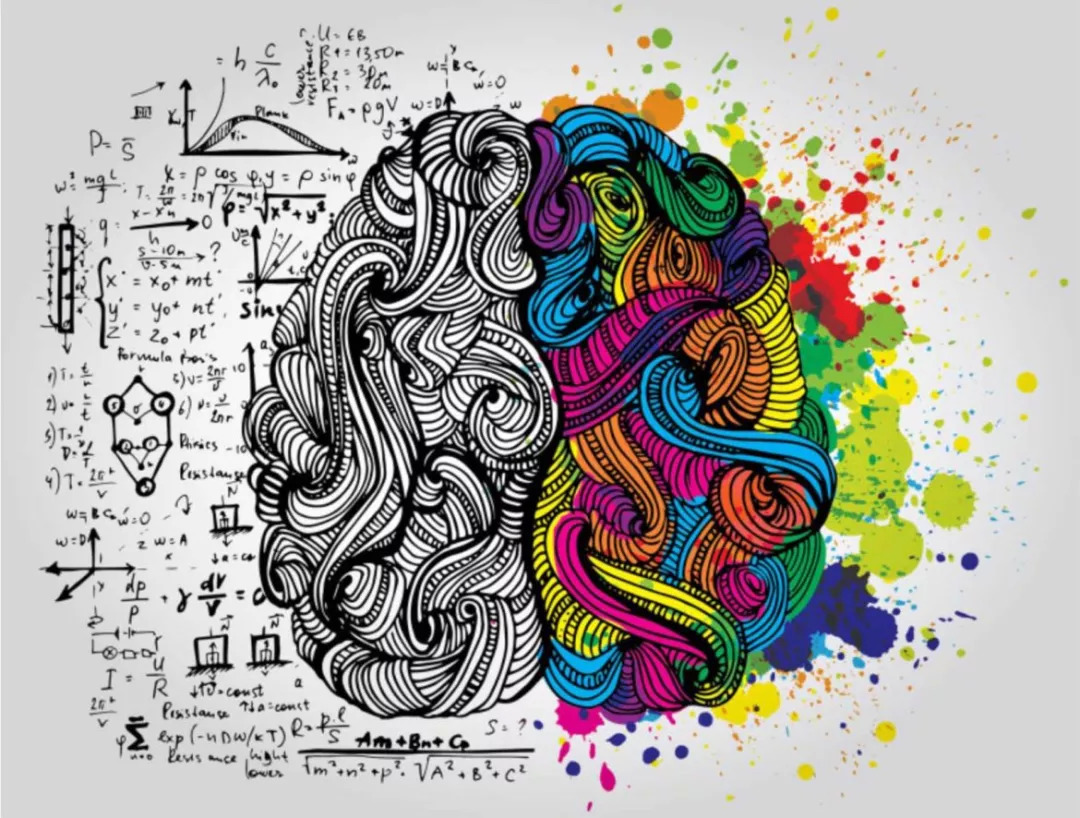
伊格曼:至于创造力究竟该到何种程度,我们无从得知。我们追寻的主题是:对个人和公司等而言,真正重要的是囊括各种选项——你创造的东西中,有一些要贴近社群标准,有一些要天马行空。汽车厂商的概念车型都超级怪诞,它们并不是真想建造这样的车型,这是为未来树立标杆的一种方式。服装厂商既生产普通服装,也设计高级时装,否则你就不知道自己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脱离社群标准。你要感觉到自己迈出了“可能性”的疆域,这一点非常重要。
你们也探讨了“孤独天才”之谜——尽管研究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人类是社会动物,创造力是在社会环境下培育出来的。这种认识误区为何如此普遍?
伊格曼:所有领域都存在这种现象。我认为,就整个社会而言,将一项发现归功于某个特定的面孔或名字,人们会更容易理解一些。但重要的一点是,有了大量想法的融会贯通,才会有新的发现。
勃兰特:若要培养创造力,尤其是孩子们的创造力,就得更加准确地把握所涉及的因素。孤独天才的迷思从来只讲“新奇”,不讲“新奇”与“熟悉”之间的张力,也不去管天时、地利与人和之间的交互。这种迷思误导了人们,导致人们在思索“怎么做才能更具创造力?”时找错了方向。我们认为:你要做的是借鉴周围的世界,设立对自己有意义的挑战,不断拿出新的解决方案,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相对于那些迷思,这是一种更可持续、更易于施行的创造力实现方式。
教育呢?我们能否跨领域培养创造力?
伊格曼:艺术和科学的教学都有一个奇异之处:一不小心,你就会把握不好。即便学校有艺术课,这也不等于孩子们就在学习创造力。他们可以了解历史上的大师,学着像他们一样作画,但那不过是模仿。而反过来,数学课却可以催生惊人的创造力。因此,教育的关键是教授创造力,确保学生打好基础,作为进入未来的跳板。

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
让我欣慰的是,这种做法在科学领域日益普遍。打好基础,然后做一个项目,编写出自己的东西。我恰好住在硅谷。在那里,这种现象遍地开花,我想,孩子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访问互联网上的世界知识,并将其作为跳板,创造出全新的东西。
你们个人最喜欢的创造力典范是什么?
勃兰特:我最喜欢的是贝多芬的《大赋格》。我们常讲的故事是,贝多芬为他的弦乐四重奏谱写了这首终曲,但对首演和听众反响忐忑不安,根本无法在听众席内坐定。他走出音乐厅,来到街对面的酒吧。最后有人告诉他,曲子并不受观众喜欢。但对我来说,它却是教科书级别的创造力典范,在给定材料的情况下,人类头脑所能想到的一切他都想到了,所以,我给他的分数是A+。
伊格曼:我认识一个人,他因为工伤失去了一条胳膊,于是装了假肢。很了不起的是,设计假肢的工程师们意识到,假肢没必要把人手的局限也照搬过来。于是,他可以让假肢无限制地旋转。因为没有筋腱的固定,它可以360度、720度地转下去。见到他后,我就想,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自然中攫取灵感,然后加以变更、改进。这就好比飞机:起初,我们想造出和鸟一样的机翼,但我们在自然的基础之上加以更改,抓住核心原则,做出了更好的东西。
翻译 | 雁行;校对 | 其奇;来源 |The Verge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