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编辑 | 朱洁树
“以往,我们把五四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或者仅仅把它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我觉得都不够。”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杨念群称,人们要么是接受了服从民族主义救亡目标的五四政治解释,要么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个人解放”看作是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价值诉求。4月26日,在《五四的另一面》的新书发布会上,杨念群指出这种“纪念史学”存在很大的问题,他认为,今天的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放在长线历史脉络里,展示出它不同的面相。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认为,杨念群不愿意把五四运动看作短暂的政治事件,而是把它放在从晚清科举废除的后科举时代,到现代中国社会慢慢形成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的长时段中理解。《五四的另一面》这本著作则“挖掘了社会组织建设这一面,解释了为什么中国革命某种意义上不是单纯的政治革命,而是长时段的、糅合了社会革命的二元革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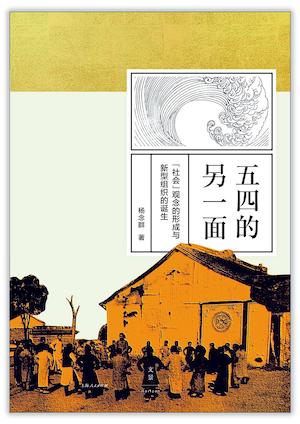
杨念群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4
五四的主题:从政治事件、文化觉醒到社会改造
杨念群说,谈到五四,一般有两种解释。其中一种是把五四看做一场政治运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诱发了各个阶层的激烈反应,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五四运动由此爆发,这一瞬间看起来是一个标准的政治事件。另外,五四运动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年轻一代的激进活动家。因此,正统史观把五四看做是民族主义的抗议和表现或者是中国共产党争取合法化地位的前奏和开端。
除此之外,关于五四运动的另外一种解释则秉持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解释传统,把个人的觉醒看作是五四最珍贵的历史遗产。杨念群看到,这种解释和上个世纪80年代的“胡适热”有关。胡适把五四定位为一场文艺复兴运动,这种“自由主义”式的思想关怀经从台湾地区被引入进大陆史学界,对那些刚从极左意识形态的压抑当中解放出来的研究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种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五四和政治的角度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被反复言说。杨念群想要指出的是,这种自由主义式的“五四解释学”把五四的解释缩挤到了个人主义的发现这一单一主题,逼窄了五四的精神含义。他认为,五四不仅是一场思想运动,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社会改造运动。
因此,我们不应该仅仅了解五四作为政治运动瞬间发生的事件含义,也应不局限于揭示心灵自我重新发现过程中爆发出的内在紧张状态,而是应当“把五四扩展到与清末变革和民初社会革命的前后长线关联中予以定位”。杨念群指出,五四之后掀起的“社会改造”运动不但成为了历史的主调,而且由此生发出的各种变革理念也深刻支配着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五四的另一面》中,最重要的关键词之一便是“社会”。杨念群指出,19世纪70年代,日本人把“society”这个单词翻译成了“社会”。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把“社会”引进到了中国,使之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与“国家”相对立。五四之后,社会改造运动变成了一个主流。“人们不是从顶层设计,不是从政党政治来讨论中国的命运和改革,而是从社会基层改造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把中国当作一个新的改革的对象,这是从五四以后慢慢形成的共识。”杨念群说。

个人主义:最值得哀悼和致敬的思潮
“五四除了‘德先生’和‘赛先生’之外,还有一个‘莫小姐’(英文moral,道德、伦理)。她一直被民主和科学这两个非常耀眼的概念压抑和遮蔽。”杨念群看到,在五四思想界,“莫拉尔小姐”即“道德伦理革命”的热门程度堪与“民主”“科学”比肩,但是,由于关于五四的记忆不断经过筛选和修正,构成“纪念史学”的一环,“莫小姐”被慢慢遗忘了。杨念群曾经在《五四前后“个人主义”兴衰史》一文中指出,“莫小姐”开启了冲破传统道德伦理束缚,追求个人幸福和个性解放的风潮。五四新青年反复讨论个人主义、人本主义等话题。但是,个人主义思潮在五四以后却慢慢边缘化,越来越多的人投身到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当中。
杨念群指出,自从个人主义被输入中国,就和各种“主义”不断竞争,争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舆论主导权,它的主要论战对手是团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在《五四的另一面》中,杨念群认为,之所以团体主义和社会主义能够后来居上,关键就在于其核心理念和中国传统思维有很多对应吻合之处。在活动现场他也告诉听众,一方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把个人作为独立价值判断的基础。在中国古代的经典中,只有庄子《逍遥游》等少数作品偶尔会提及个人自由,在以儒家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中,个人必须服从于家庭的网络和更大的社会秩序。个人只是出发点,但不可独立于任何的家国体系。另一方面,中国的公私之间的界限非常不分明。从《礼记》到孙中山,都提倡“天下为公”,“公”的合理性理所应当。但是,鲁迅、胡适等人最早在五四时期提倡个人主义时,他们试图探究个人能不能跟“天下”“公”形成对立、平行的甚至不兼容的关系,但他们的尝试以失败告终。杨念群认为,最终失败的原因就是“公私之间的界限在中国的体系脉络里无法区分” 。
时代因素也是个人主义在后五四时期陨落的重要原因。杨念群指出,个人的位置往往是在跟家国天下的互动中来确立的。在中国不断受到西方侵略的过程当中,如果把个人放在国家抵抗外来侵略的利益之上,就没有合法性。因此,在拯救民族危亡的特殊时刻,团体主义、集体主义逐步升格到了支配地位,而“个人”欲望和尊严退居其次。“个人”逐渐变成了肮脏、自私自利、带有很强烈负面价值的导向性的评价。这个趋势在日本侵略中国之后越发明显。个人主义逐渐被压抑到十分狭小的范围内,慢慢趋于消失。“这可能是五四时期最值得惋惜的因素,值得我们把它重新挖掘出来,加以哀悼和致敬。”
虽然值得惋惜,但是杨念群也看到,在中国语境下,强调个人主义,人会变得非常孤独,无所皈依。他指出,中国文化根本的意义是依靠人际关系网络和伦理网络来支撑个体,放弃了家庭,必然要找到新的组织,否则人会产生一种孤独感。因此,虽然五四时期有像鲁迅这样的个人主义者,坚持个人无所皈依的漂泊状态,但是,大多数人还是像朱谦之(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那样,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状态下的个人。
无政府主义:为新国家提供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人们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造在建立一个现代国家之后就能够找到出路。辛亥革命的一举成功曾经一度给知识界带来希望,可是民国初建的混乱局面很快打破了这种幻想。此后,不少人希望通过“莫拉尔小姐”(伦理革命)解决原来希望通过政治解决的问题。在这一过程中,无政府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杨念群看来,宣判“国家”作为偶像的倒塌乃至把变革失败归罪于“民国”的看法,逐渐演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倡导新型社会革命的前提。
李猛指出,西方无政府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反对现代国家。但是,按照杨念群的叙事,共和革命的挫折经过无政府主义,通过社会改造,最终却为1949年以后的新国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在整个建设现代中国的过程中,无政府主义的理念与后来的社会主义思想之间的关联引人思考。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应星也指出,我们应该思考无政府主义、乡村建设运动和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的关联。

杨念群认为,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翻译过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人关于劳工互助和城市里发生的无政府主义的理论,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却是对托尔斯泰那种乡村无政府主义抱有特别的兴趣。无政府主义来到中国之后,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其中包含了相当程度的非无政府主义的成分。虽然无政府主义想要绕过国家的控制,但是它依然讲究组织的严密性,讲究个人必须要服从集体的逻辑,“恰恰用另外一种方式复制了他们所反对的那套家庭的伦理”,这是中国无政府主义的一个特殊的形态,和西方的无政府主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了”。
“虽然表面上打的旗号是吸收西方无政府主义的资源,但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本身是传统的复归。”这种复归并非是乡村建设运动中使用政教关系,例如使用乡约来整合地方社会的努力。在杨念群看来,无政府主义完全是空想,没有一个完整的形态;乡村建设运动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梁漱溟等人更多考虑的是社会组织复原的问题,但是,完全地复原和现代国家的政治运作是脱节的。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更具有影响力,是因为执行力更强。他通过新民学会(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长沙发起成立的革命团体),提高团体内部的执行力,再从新民学会发展出政党政治,把湖湘地方资源和无政府主义当中对组织的重新规训整合到政党政治的框架,将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政党政治的执行力要远远高于无政府主义那种空洞想象的形态,也比乡村建设运动那种复古的、草根式的,以儒家式的道德秩序作为中心含义的政教体制的简单复原更有力量。”
……………………
| ᐕ)⁾⁾ 更多精彩内容与互动分享,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和界面文化新浪微博。



评论